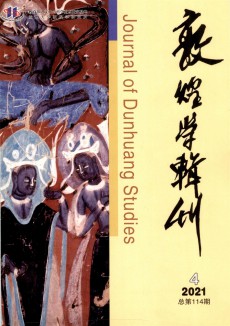敦煌文化論文大全11篇
時間:2023-03-21 17:08:27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敦煌文化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二、創作形式的轉化
20世紀末出現的動畫短片適逢民族藝術與動畫藝術融合至頂峰的時段,制作形式上自然根植于傳統二維動畫創作,同時與其他民族繪畫藝術進行融合。如《九色鹿》《鹿女》中的動畫場景均用到水彩與水墨的暈染效果,畫面場景設計也多跟隨壁畫中消除透視的方式呈現。21世紀以來,在全球化背景下,古老敦煌文化和各種社會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一種對古代文化的深層次探索,并在此基礎上對其做出現代化的闡釋。《敦煌》《飛天》《夜伴敦煌》這些動畫短片首先在創作形式上均以新時代背景下的數字方式完成,從畫面效果來看,大部分短片由于短片劇本的情節關系,短片中絕大多數借用了原有敦煌壁畫的畫面造型與色彩搭配,現代與原創造型較少,這與動畫前期的劇本設定有很大的關系。無論是哪一個時間段的有關敦煌的動畫作品,都能在將古代藝術向現代藝術轉化的過程中,除了動畫劇本的再構思,還表現在造型元素的處理上,并且從創作效果來看,體現出明顯的時代差別。所有造型簡潔靈動,人物角色占據畫面絕大部分區域,另配以山石樹木,紅色背景上襯以黃色、綠色等山水造型,裝飾風味濃厚。以此改編的動畫作品需要將人物角色、動物角色、事件發生的不同場景按照壁畫呈現出的時代畫風設計出來。從圖2和圖3的一系列圖片中可見人物、山脈、樹木造型以及畫面場景元素的位置安排均與原壁畫有神似之處。此外,敦煌壁畫中故事連續畫的一大特點就是透視感弱,在動畫《九色鹿》中,對于空間的表現同樣是缺乏透視的,組圖場景中前后山脈的空間關系、山與水的坐落位置常給人處在同一空間維度的感覺。敦煌壁畫的透視采用動點、散點透視,視主體是運動的,視點不唯一,每個視點都有所觀察的情節與局部,那么就形成了多個視覺觀察點即流動的多眼視場,觀者通過眼睛觀察不同位置環境情節下的既獨立又相互聯系的畫面。對于透視的表現,《九色鹿》就像壁畫中那樣用大小來表示遠近關系,也正是由于缺乏透視感,所以為了更好地表現空間感,也加入了少量的虛實手法表現空間透視,如遠處山脈的虛化處理和空間的霧化效果,讓人感到山脈在空間位置上漸遠。敦煌壁畫對中國古代繪畫造型中線條變化的應用游刃有余,并且線條的使用也成為敦煌壁畫的一大主要造型方式。《九色鹿》中人物的設計充分體現敦煌壁畫的造型特點,角色線條簡潔明了,多以流暢舒緩的長線條勾勒角色,而主要角色身體和面部的線條勾勒更是體現出敦煌壁畫抽象化與符號化的特點,抽象裝飾風味濃厚。20世紀的敦煌動畫作品,是在領略了敦煌壁畫造型特色基礎上,從造型和場景風格上狠下功夫的結果。近年來創作的敦煌動畫作品中,一些傳統的創作表現形式基本消失,制作手段上從傳統的二維動畫創作轉向多元化的創作手段。圖4中分別是四部動畫短片的靜幀畫面,無紙數字化二維方式、三維CG技術,抑或兩者的結合。這些先進的制作技術在短片中被高頻利用,充分呈現敦煌元素動畫的藝術形式從傳統動畫向數字動畫轉化的趨勢。具體來看這些創作形式所匹配的文本,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故事型與氣質型。故事型敦煌動畫旨在傳達現代人如何看待敦煌藝術,創作形式上通常以傳統手繪二維動畫或數字化二維方式進行,創作畫風突破以往敦煌動畫對敦煌壁畫面貌特點重現的表現手法,以現代動畫風格為主,同時恢復對空間的透視表達,人物角色的形象設計也更趨于現代化。從這一點來看,現代動畫形象的參與拉近了與年輕一代受眾的心理距離,使得這一類人群具有更多的參與感,也使其加強了對敦煌動畫的理解和認同。氣質型敦煌動畫旨在體現敦煌文化的人文情懷,從人的抽象思維層面傳達對敦煌文化的體會,對壁畫形象的贊嘆,向受眾傳遞創作者的精神感悟。這類敦煌動畫文本大多沒有故事的起承轉合,通過對敦煌壁畫中形象的精細繪制和場景再現,展現敦煌壁畫的精妙之美。從某種角度來說,氣質型敦煌動畫創作技法的難度系數有所降低,它的創作意旨決定了它創作形式的多樣化,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三維數字技術以及數字二維合成技術形式在此類型中均有所參與。創作畫風則是在無透視基礎上體現角色和場景的精細。如果說《九色鹿》動畫風格是一種抽象的符號化演示,那么這一類形式則是用超寫實的敦煌壁畫形象來呈現一種精致的敦煌氣質。概括這一時段短片劇本的整體特點是基于對古代敦煌壁畫文化的展示這一題材,隨即展開的劇本創作。也正是由于劇本涉及內容的高度一致性,這些短片中更多的是現代造型設計風格、規整的透視和對壁畫形象的細致還原,表現對象主要集中在“佛陀說法”或“伎樂飛天”兩種形象上。對壁畫形象進行創新性還原,短片多表現虛空中飛舞的天人,她們相互逐戲,身姿曼妙,衣袂飄舉,或散播天花,或彈琴奏樂,畫面豐富活潑,線條如行云流水,一氣呵成,動感強烈,暢快之極。
篇(2)
中圖分類號:K87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2)03-0027-05
Confuc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tertainment
Culture in Medieval Dunhuang
CONG Zhen1 LI Chongshen2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2. Institute of Silk Road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Gansu 730050)
Abstract: By interpreting the materials about entertainment recorded in the Dunhuang documents from the Library Cav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ntertainment culture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 theory of "ritualism" as proved by the hierarchies and paradigms revealed in these activities. Local people had to consider whether their behavior was in accordance with Confucian rites when trying to relax and entertain themselves. Limited by ritual guidelines and ethical morality, the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reveal an almost total lack of vitality and passion.
Keywords: Dunhuang;Entertainment culture;Confucian feature;Interpretation
游藝,顧名思義,就是游戲的藝術,是各種娛樂活動的總稱,是人們以娛懷取樂、消閑遣興為主要目的的一種精神文化活動。中國古代游藝活動深受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從本質上說,它沒有獨立的地位,而是依附于歲時節日、勾欄瓦肆、集會宴飲等活動中,并且始終受到禮的制約,以禮為本。敦煌莫高窟壁畫和藏經洞出土文獻中記載有較為豐富和相對完備的游藝活動資料,通過對這些資料的研讀,發現其同樣帶有鮮明的儒家思想特征。這種特征在敦煌游藝活動中表現為活動程式的規范性、活動功能的象征性以及活動內涵的人文性。對這些特征的理解,有助于對古代敦煌人民的游藝生活面貌進行儒家精神層面的解讀。
一 儒家經典對游藝的闡釋
中國歷代儒家經典著作中,有較多內容涉及對游藝的闡釋,通過這些闡釋可以比較清晰地把握所謂的儒家正統對游藝的認識。“游藝”一詞,最早見于《論語·述而》:“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1]《說文》把“游”引申為“出游、嬉游。俗作遊。”[2]朱熹《四書集注》云:“游者,適情之謂。”[3]“藝”字,據何晏《論語集解注》解釋為“禮、樂、射、御、書、數六藝。”[4]朱熹進一步解釋為:“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不可闕者也。”[3]107對于游藝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朱熹曾論證道:“志道,則心存于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則德行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3]107清人周象明亦云:“格物謂窮乎物之理,游藝謂玩適乎藝之事,窮極其理講學之先務,玩適其事德盛之余功,二者有初學成德之分。蓋此是德盛仁熟之后,等閑玩戲之中,無非滋心養德之助,如孔子釣弋是也,從心所欲不逾矩,乃其境界歟!”[5]由此可見,在儒家的傳統觀念中游藝是以道德仁義為優先,亦即只有等到德盛仁熟之后,才能從事等閑玩戲的游藝活動。
正是基于上述儒家正統對游藝的闡釋,致使歷朝歷代的封建大儒們對游藝活動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但事實上,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游藝作為人們休閑娛樂的重要內容,是無論如何也控制不住的。游藝活動不僅受到統治者的垂青,而且在民間也相當普及,成為中國人經常而又普遍的生活要素之一。因此,中國古代游藝活動的發展呈現出非常有趣的現象,一方面是正統思想的壓制或不提倡,另一方面卻是統治階級、平民百姓甚至是儒家知識分子本身的身體力行。這使得游藝活動中人們既想放松身心、盡情娛樂,又不得不時刻考慮自己的行為是否合乎禮的規范,從而導致了游藝的雙重屬性和自身矛盾性。
二 敦煌游藝中所蘊含的儒家思想特征
篇(3)
*基金項目:甘肅省高等學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成果“敦煌文化藝術遺產資源的產品化研究 ”,蘭州商學院教改研究資助項目(20110221)。
季羨林先生曾指出:“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會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 ①敦煌文化藝術享譽世界,是絲綢之路華夏文明傳承與創新的重點,敦煌旅游產業投資與開發成為旅游產業密切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敦煌旅游文化產品正從傳統的手工生產向專業化轉化,作坊生產也逐漸向企業集約化過渡,繼而在開發的內容與層次、品牌建設、管理、市場營運等方面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如何在繼承傳統、合理利用文化遺產資源、打造敦煌品牌的同時,進行可持續的生態開發,專業化發展成為良性發展的必然選擇。所謂專業化過程,就是產業部門或學業領域中根據產品生產或學界層面的不同過程而分成的各業務部分,②而旅游文化開發專業化的實質,筆者認為應該是建立在當代文化教育背景下以傳統繼承為基礎、以人才為支撐、以文化知識為動力、以信息為溝通、以旅游市場為導向的創造行為與生態發展模式。
一、 敦煌文化藝術遺產資源開發人才的主導性
文化產業專業人才的培養與吸納是敦煌工藝品開發走向規范化、專業化的前提,對于提高設計質量、創意水平、調節生產、預測市場動向,提高研發的深度與層次起著關鍵作用。知識經濟的核心是創新,創新的主體是人才問題。敦煌旅游工藝品開發對于人才的要求是,首先,具備一定專業技能技巧,以滿足工藝品開發技術需要。第二,具備設計創新能力。創新人才是產品更新換代與深入開發的主體,是產品質量創新的動力源泉,是專業知識掌握程度的綜合體現。第三,敦煌文化知識的積累與熟識程度,作為專業設計人才應關注設計的對象、理解文化的背景,產品開發的深度與層次,在傳承中進行保護性的生態開發。因此,人才具備以下專業優勢:
(一)熟悉相關的材料、科技與工藝
首先,創新人才的價值體現在對工藝材料的創造方面。不同的材料具有不同的工藝性、實踐性,實踐創造的過程必然是對材料性質及裝飾語言的探索、工藝技術手段的嘗試與方法的改造與研究,實驗實踐為材料工藝的開拓、創意產品的生發提供了動力支持,將作者的思維與創意物化為現實,設計者創意思維的更新首先是對材料屬性的認識與理解,創意產品的形成也實現于材料化學物理特性與工藝的把握,在材料、設備、技術、創意思維及市場環境條件下進行創造與生產。正如我國古代工藝著作《考工記》所提出的工藝觀:“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為良。”③敦煌文化產品開發尊重材料的屬性及藝術設計的客觀規律是旅游工藝產品創意的先決條件之一。其次,在保證花色品種豐富的同時,可提高生產力。傳統的作坊設備落后、創造力薄弱、生產能力低下,創意產業則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第三,便于合理安排產品開發的層次。有些公司眼光盯在中高檔產品的開發上,卻忽略了銷售量較大、價格適中的產品開發市場。那些價格適宜、體積較小,富有特色、便于攜帶旅游品還不多。不難看出后者遠比前者更具有市場潛力,那些體積較小、價格適中的產品銷售量較大,訂單也較多,為更多的普通游客所鐘愛。
(二) 創新人才的實踐能力與創造素質
創新思維既來自于設計實踐,又來自于當代新設計教育。當代設計教育在傳授設計知識與技法的同時,更重要的是信息的傳遞與積累,現代科技媒介下孵化的是知識的環境和效率的提升,它擴大了人們的視野,把傳統遙不可及的信息通過視頻、攝影、展演生動鮮活地傳達給我們,促進了國內國際的信息交流與溝通。設計師在較短時間內既能夠掌握藝術設計的基礎知識,又可以獲得產品設計的專業知識,又能夠擴大視野、改變設計觀念,對傳統與現代產品、國內與國際產品、手工創意與機械復制產品進行比較與分析,探索并依據產品市場的運行規律進行設計創意,創意思維的突破帶動創意產品能夠靈活根據市場的需求進行設計。
從造型到裝飾,運用創新觀念密切聯系時代生活成為創意產品設計的重要特點,藝術設計專業的分工使設計服務走向專業化、人性化,設計服務傾向精細、靈活、具體,在競爭基礎上前所未有地關注細節與質量。如何符合現代人的審美習慣,甄別現代審美的普遍性與個性,使設計融入現代生活,讓生活更富有藝術品位與質量,追求設計與時尚為一體的精神,蘊含知識與思想的文化設計成為創新設計的普遍趨勢。知識的更新與傳遞來自于教育與信息交流,當代設計教育成為產品設計創意創新的重要方式,學校教育一方面通過各種實踐活動傳授技法技巧,另一方面通過各種校內外展覽活動與教學培養更新學生的設計觀念。例如近年以絲綢之路為背景的敦煌舞蹈劇《絲路花雨》,是敦煌舞蹈的代表作。自1979年以來在國內外演出1000多場次,曾獲創作獎、演出獎一等獎。1994年獲得中華民族20世紀舞蹈經典作品“金像獎”。舞劇《大夢敦煌》以莫高、月牙的愛情故事為主線,準確地呈現了敦煌文化的精髓, 2001年獲得中國舞蹈“荷花獎”舞蹈劇銀獎,及“五個一工程獎”,2002年獲得文化新劇目獎,是國家舞臺精品工程劇目。④
創意產品的原創性具有唯一性的特點,它通過作者的創造實踐和勞動研究獲得,在一定階段具有產權專有和壟斷性。其次是產品要以商品的形式推廣于市場,從市場反饋信息來判斷產品市場的接受程度。
(三) 以文化知識支持的智力要素
創意經濟最大特點是通過文化知識來支撐經濟體系,工藝品創意也不例外,文化知識成為當代教育推動創意經濟的發展重要智力支持。文化創意產業是新經濟的一種表現形式, 1998年阿特金森和科特明確指出,新經濟就是知識經濟,而創意經濟則是知識經濟的的核心和動力⑤。文化創意產品一般是以文化、創意理念為核心,是人的知識、智慧和靈感在特定行業的物化表現。文化創意產業與信息技術、傳播技術和自動化技術等的廣泛應用密切相關,呈現出高知識性、智能化的特征。其次,文化創意產業具有高附加值特征。文化創意產業處于技術創新和研發等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是一種高附加值的產業。知識型的產品創意設計不但來自于知識的積累、實踐與拓展,而且其創造能力還來自于對知識的把握、凝練、靈活運用與轉化,知識的能力轉化程度決定了創意作品質量的高度,而作者文化知識的素養則是創意能力產生的根源,是設計師創造與創新的重要動力,也是別于匠人的主要原因。
文化設計是當代產品的一種主流現象,旅游產品經常借助于旅游文化元素與符號進行形式創新,反映和表達一種設計主旨。例如敦煌大乘藝術有限公司以敦煌文化藝術為題材,傳統文化元素的巧妙利用使現代旅游產品富有文化內涵與藝術生命力。
(四)文化資源開發的信息條件
信息資源是企業生產及管理過程中涉及的一切文件、資料、圖表和數據等信息的總稱。它涉及企業生產和經營活動過程中所產生、獲取、處理、存儲、傳輸和使用的一切信息資源,貫穿于企業管理的全過程。譬如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大膽構想建立“數字敦煌”,利用浙江大學信息科技水平,與其聯合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多媒體與智能技術集成及藝術復原”課題,屬于資源信息共享的范例。信息具有共享、時效、流動等特點。創新人才善于搜集、調動信息要素,善于信息資源化,在旅游文化產品創意領域,通過信息傳遞將多種知識和資料整合轉化為創意設計源泉;信息溝通將新材料新工藝進行合理的引入,將知識與人才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將創意市場的需求與消費聯系起來,開發市場的空白,疏通銷售渠道;通過科學的管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在生產中體現效益、效率與質量,充分利用現代信息科技的成果,將信息資源化成為創意產業開拓與發展關鍵因素和總體特征。
二、創新人才在敦煌文化藝術資源開發過程中的時代特點
柳冠中在《蘋果集?設計文化論》說道:“設計觀念是一種創造,是組織,是文化,是方法論。設計觀念昨天相對于今天是傳統,今天相對于明天,今天是傳統。”⑥創新人才既是文化開發專業化創新的主體,也是產業科學管理的有力構成,把握當代藝術設計的主流與方向,旅游消費心理的審美需求,將以人文為本的“人性化設計”、“設計與時尚于一體”的內涵靈活地運用于創意設計是時代的選擇,主要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科技為支撐的營運模式日益顯著
以科技為支撐的旅游工藝品創意與生產成為發展的普遍現象和趨勢,科技、信息、知識、智力在產業運作中的作用不斷加強,成為創意發展的必要環節。譬如在生產工藝和新材料利用方面,以蘭州文化創意產業園的創意產品為例,傳統工藝產品壟斷局面被打破,多材料、多工藝及配飾的產品爭奇斗艷、異彩紛呈、個性十足,能夠滿足當代人多樣的審美需求。這是設計生產者借助現代科技、材料與工藝研究制作的結果。
在市場分析方面,設計師開始關注既滿足大眾普遍性的審美需求,又尊重少數人個性審美特點,既能夠繼承和創新傳統文化進行創意設計,又能夠另辟蹊徑開發市場空白領域。如成立于1999年的敦煌大乘藝術有限公司,他們以敦煌藝術為目標開發工藝品,超過9個系列800多個品種,基本上涵蓋了敦煌石窟藝術最具有代表性的壁畫、雕塑造型。大乘公司在工藝品研發之余,不忘宣傳與推廣,積極打造品牌,通過作品展覽的形式擴大社會影響力。一些作品造型優美,技藝精湛,在2001年度曾有3個品種獲得國家工藝美術百花獎銅獎,他們設計的金銀幣在中國銀行中招標的有5個品種中標,其中1個品種在新加坡國際錢幣博覽會中獲得金獎。在商品推廣、網絡宣傳、品牌打造、反饋方面通過智力策劃,能夠迅速地跟蹤市場、適應需求、調整決策。
(二)設計服務意識不斷提高
設計服務是現代工藝創意產業管理規范化的要求,也是創意產業持續發展的有力保障,首先體現在質量方面。質量分為設計質量、產品質量、服務質量,質量是產業信譽的基礎條件,高端的創意產品必須具備一定水平的設計質量,創意特色、個性與商業推廣依賴于設計質量的水平,是產業鏈的首要環節。其次是產品的質量,產品生產是設計的實現環節,高質量的旅游產品生產必須在材料選擇、制作加工與裝飾過程中保持產品的品相與特色。隨著現代管理理念的引入與市場競爭壓力增大,人性化設計在設計領域越來越趨向細膩和健全,設計服務質量體現在產品的業務溝通、銷售、包裝、物流、反饋等方面,集中反映了產業的管理水平、業務素質,服務的質量與水平體現了管理人員的層次與素養,進而影響業務拓展和產業信譽。
(三)傳承、保護、可持續的生態開發意識
專業人才不但擁有一技之長,而且對產業的發展具有宏觀的視野和預見性,能夠對文化遺產資源利用提出有效的措施,實現行之有效的良性保護開發。例如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在數字與影視技術的影響下提出用數字化保護文物的新思路。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開始籌建莫高窟游客服務中心。建成后,游客服務中心可以讓游客在未進入洞窟之前,先通過影視畫面、虛擬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風貌、歷史背景、洞窟構成等,然后再由專業導游帶入洞窟做進一步的實地參觀。此外還大膽構想建立“數字敦煌”,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多媒體與智能技術集成及藝術復原”課題,將洞窟、壁畫、彩塑及與敦煌相關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數字圖像,同時也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研究成果以及相關資料匯集成電子檔案,用“數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壁畫這個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可持續的生態開發已得到專業人士及相關學者的高度重視,繼而也得到相關政府及部門的關注與支持。
(四)開放、交流、合作意識的加強
隨著現代通訊信息的快速發展,網絡、電信、媒體等相關設備設施成為現代企業的必備條件,信息時代為產業的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效率。旅游工藝品創意設計也不例外,他們意識到傳統工藝行業閉關自守、缺乏交流、逃避競爭的經營模式已不適合當展的節奏與環境。從產業開發的內容來看,許多門類是傳統工藝未涉及的領域,也是現代經濟生活的重要構成。例如旅游品、紀念品、陳設品等層次豐富,種類多樣。其次通過科技學習、專業積累,開發新的材料、技術工藝、裝飾手段和方法,創造市場前所未有的新穎特色產品。再就是通過管理培訓、技術培訓、展銷活動學習國內外的成功經驗。最后通過市場觀察、市場調研、消費反饋,及時調整生產計劃,制定新的方案與對策。另外,在開放、交流過程中,業務內的合作、互助、共贏成為創意產業的一個新的現象。
通過影視推廣和宣傳敦煌文化,例如紀錄片《敦煌》、《千年莫高》、《印象樊錦詩》 等,使觀眾更好地認識敦煌文化和敦煌人的奉獻精神。再如集歌、舞、樂為一體樂舞《敦煌韻》,以明確的市場定位和旅游演出營銷,在廣東連續演出100多場次,創造了新創劇目連續演出的記錄。另外,以敦煌為主題的藝術創作則是以弘揚敦煌文化、促進敦煌藝術發展的創作活動,中國美術家協會舉辦的“朝圣敦煌”展覽活動,和敦煌畫派以敦煌為主題的展覽活動多屬于學術研究與交流活動,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應。
三、結語
甘肅是文化大省,卻是文化產業小省,敦煌文化資源化的過程也是文化產業發展的過程,是伴隨著敦煌研究、敦煌旅游而發展起來的新興產業類型,既是現代教育視野下文化知識的創造產物,又是時代市場選擇與發展的必然結果。正如劉勰所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6]創新人才要素成為創意產業振興的核心部分與動力要素,人才的培養與吸納問題成為關鍵環節,尤其是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從市場選擇角度來看,它反映當代人們審美意識的變化和提高,多樣的審美需求制約著文化開發產品的供求關系變化與發展,同時創意產業也遵循著市場的選擇,在淘汰舊產品同時不斷更新,創造出特色產品,以個性、特色、靈活地探索市場的規律,同時也對設計者的創意提出更高的要求,在信息時代要求設計者不斷用文化知識更新武裝自己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節奏與變化。
【注釋】 ① 季羨林:《敦煌學、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紅旗》,1986年第3期。
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 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 2011年 版。
田自秉:《中國工藝美術史》,東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頁。
篇(4)
1983年,《敦煌研究》正式創刊。《敦煌研究》從創辦之初,就立足敦煌,放眼世界。一方面集中本所的研究力量,發表新成果和高質量的論文;一方面通過各種渠道,征集國內外一些著名的專家學者的成果,使本刊發表的成果保持較高的學術水準,成為敦煌學界的重要參考。
為了適應《敦煌研究》編輯工作的需要,敦煌文物研究所于1982年成立了編輯室。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原編輯室也改為編輯部,并陸續增加編輯人員,1986年已有編輯六七人,編輯部初具模。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編輯部大體上有10人左右的規模。編輯部的工作人員雖然可以說是專職編輯,但大多同時進行著敦煌學研究工作,學者兼編輯正是本編輯部成員的最大特色。從歷年就職于編輯部的工作人員來看,研究范圍涉及敦煌石窟藝術、石窟考古、敦煌歷史與文化、敦煌文獻(文學、宗教、書法、回鶻語言)等,涵蓋了敦煌學的大部分專業。本刊的編輯人員在從事繁重編輯工作的同時,仍孜孜不倦地從事學術研究,不斷地發表學術論文,出版學術著作。由于對敦煌學有著深入的研究,使編輯人員能夠從較高的視點來進行刊物的編輯工作,同時也有利于跟各學科的學者們進行交流,從而使《敦煌研究》的編輯質量能保持在一個較高的層次。
《敦煌研究》于1981年和1982年出版了試刊第一期和第二期,1983年出版創刊號。1986年起為季刊,2002年起改為雙月刊至今,截至2016年12月,共出版正刊160期,此外還出版紀念特刊8期。刊發文章(除特刊外)約5000余篇,內容涉及敦煌藝術與考古、歷史文獻研究、文化遺產的保護科學等等與敦煌學相關的所有專業,除了在敦煌文獻研究方面不斷刊發最新成果外,在敦煌石窟及全國各地石窟考古和藝術研究、石窟保護科學研究等方面的論文成為本刊最具特色的學科領域。本刊登載的論文每年都有不少被轉載被引用,或被翻譯成外文在國外發表。還有相當一部分論文為國家級或省部級課題項目的成果,有的還在全國以及各地的社科成果評獎中獲獎。《敦煌研究》不僅在世界敦煌學術界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而且對于相關的學科也產生著不容忽視的影響。
《敦煌研究》自創辦以來,得到了國內外敦煌學界的廣大學者的大力支持和關懷,包括在座的一些老師,也給我們以持續不斷的支持和鼓勵,也得到了上級主管部門的鼎力支持和幫助,使我們的工作不斷取得進步。但是在今天學術發展的形勢下,《敦煌研究》也面臨著種種挑戰,我們不能停留在以往的成績上,而是要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近年來我們在如下幾個方面做了努力:
1. 始終保持在國際敦煌學界的影響力
隨著敦煌學的發展,我們依托敦煌研究院在海內外的影響力,不斷約請世界知名學者為我們投稿。近年來,我們得到了日本、法國、英國、美國等國以及臺灣、香港等地知名學者的來稿,如日本著名學者宮治昭、高田時雄、英國學者韋陀、魏泓、美國學者王靜芬以及臺灣著名敦煌學專家鄭阿財、王三慶等都先后給本刊投稿,國內著名敦煌學專家榮新江、郝春文、柴劍虹、方廣、張涌泉等學者也不斷給本刊投稿,使本刊所刊發論文保持在較高的水準,持續在國際敦煌學界產生較大影響力。今后我們還將繼續努力,聯系國內外敦煌學專家,刊發最新學術成果。
2. 從嚴審稿,質量第一
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范圍內的敦煌學研究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國內學術界與海外的交流與合作呈現空前活躍的狀態。而國內不少大學相關專業博士、碩士研究生都在敦煌學領域選擇其論文的重點,歷史、藝術、語言文學、宗教等學科的專家們也開始關注敦煌文獻或敦煌石窟,從中找到有價值的研究項目。因此,《敦煌研究》期刊的投稿量不斷上升。與此同時,來稿質量也參差不齊,精粗雜糅。面對新的形勢,本刊編輯部首先在審稿上下功夫,所有刊發稿件均由相關專家審稿,嚴格把關。2012年起,在原有10多名專家組成編委會的基礎上,又聘請院內外7名專家學者為特邀編委,協助本刊審稿。編委和特邀編委的學科涵蓋了敦煌學相關的各學科,此外,對一些特殊專業的來稿,我們還專門請該學科的權威專家進行審稿,以保證用稿質量。
由于《敦煌研究》是敦煌學專業學術刊物,涉及較廣泛的學術領域,對編輯的要求就比較高,我刊編輯人員在從事編輯工作的同時,也從事敦煌學研究,發表敦煌學專業學術論文或出版學術專著。為提高編輯人員的編校能力,還輪流派編輯人員參加由國家新聞廣電總局下屬相關部門舉辦的編輯培訓班,以提高編輯人員的素質。
篇(5)
其一,它為我們全面、深入、系統地考察中古時期的一個地區提供了相對充足的研究資料。與甲骨文和漢晉簡牘等其他出土文獻相比,敦煌文獻具有以下特點。首先,它涉及的學科和方面較多。僅對歷史學而言,就涉及政治、軍事、經濟、宗教、文化等各個領域的諸多方面。其次,每件文獻所包含的內容也相對比較豐富。再次,它涉及的時間較長,自5世紀初至11世紀初將近6個世紀。即使文獻年代比較集中的8 世紀中至11世紀初,亦達200多年。最后, 全部文獻都與敦煌地區有不同程度的關系或聯系。就世界范圍來看,具備以上條件的出土文獻似也為數不多。如果我們依據這些資料對中古時期敦煌社會的各個角度、各個層面作全方位的考察,其成果將為學術界認識中古社會的具體面貌提供一個模型或參照系。這當然有助于推進人們對中古時期社會的進一步認識。顯然,對歷史學而言,解剖敦煌這樣一個麻雀,其意義會超出敦煌地區。而敦煌文獻為解剖這個麻雀提供了必要條件。
本文的簡略回顧表明,數十年來,我國學者在這一方面已做了許多重要準備工作。如對歸義軍政治史的研究、對敦煌歷史地理的研究等都已經相當深入,并有總結性論著問世。有的相關類別文書如碑銘贊類文書和契券文書的整理和研究也已達到較高水平。但仍有許多方面需要加強,不少方面有待展開。如歸義軍時期的經濟史、佛教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等方面都值得投入更多的力量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有些方面甚至需要較長時間的準備以后才能進行總結。如敦煌佛教史需要對相關文獻進行系統整理和研究,完成“敦煌佛寺志”、“敦煌的佛教與社會”等系列專題研究以后,才有可能在這方面進行總結性研究。敦煌社會史也要在完成“敦煌氏族志”等系列專題研究后才有可能進行總結性研究。至于敦煌文化史,我們以前做的工作就更有限,大量的工作有待展開。可見,在本世紀的最后幾年和下一個世紀,專題研究應進一步加強。因為只有在深入的專題研究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寫出有分量的專史,而各方面專史的完成又是全面綜合研究的必要準備工作。在從事專題研究過程中,需要完成大量艱苦的微觀考察。不少工作表面看來十分細碎甚至繁瑣,無關大局,如過去我們對歸義軍政治史許多小問題的探索就容易使人產生這樣的印象,但這些微觀探索又是我們全面、深入、系統地考察敦煌地區必不可少的工作。當我們將這些具體的探討整合為對整個敦煌地區的微觀透視時,就會發現在敦煌文獻研究領域,微觀考察的意義不同一般。
當然,要完成對敦煌地區的全方位考察,僅靠專題研究還遠遠不夠。必須同時積極開展綜合研究與宏觀研究。在第一、二階段,我國學者因受到資料的限制,往往只能就所見少量文書或一件文書進行闡發,研究是點式的,很難做專題或綜合研究。到第三階段,我們能見到的材料日益增多,對敦煌文獻做分類整理或專題研究的學者也逐漸增多。但對各類文書、各個專題、各個學科進行的綜合研究還很薄弱,將敦煌地區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的工作也有待展開。就目前而言,首先應注意從整體上把握敦煌文獻。敦煌文獻雖然分屬各個學科,可以分為許多類別,但同時又是一個整體,各類文獻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如人們利用有關10世紀的一大批文書研究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宗教和社會,已取得了很大成績,若在此基礎上將這一時期的各類文書打通,相信對這一時期整個社會的了解將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其它如對歷史資料與文學史資料等各學科之間聯系的研究,漢文歷史文獻與藏文歷史文獻等各文種之間聯系的研究,也都是具有很大潛力的研究領域。在下一個世紀,當各個專題和綜合研究都達到較高水平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考慮撰寫貫通中古時期敦煌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文化等領域的《敦煌中古史》了。
其二,敦煌文獻為我們進一步研究9世紀中葉至11 世紀初西北地區的民族史提供了提供了大量原始資料。9世紀中葉至11世紀, 是我國西北地區民族發生大變動的時期。但傳世史籍有關這方面的記載較少,很難據之進行深入系統的考察。敦煌文獻中保存了一批反映這一時期民族情況的漢文、藏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公私文書,為我們探討西北地區民族變遷、各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與相互間的交往提供了可能。本文的回顧表明,我國學者在利用這些資料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績。特別是第三階段,我們不僅在利用敦煌漢文文獻研究西北地區民族問題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在對少數民族文字歷史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也有較大進步。同時應該承認,我們這方面的工作做得還很不夠,與國外同行相比還存在不少差距。在少數民族文字文獻研究方面,一些文種與國外的研究水平差距還比較大,取得的成果仍以第二次譯釋居多,能直接解讀少數民族文字文書的學者亦嫌太少。所以今后應進一步加強對少數民族文字文書的整理和研究。特別是藏文文獻,數量很大,值得投入更多的力量進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另一方面,在研究西北地區民族問題時,應提倡在全面搜集各方面資料的基礎上將敦煌漢文文獻、各民族文種文獻與傳世文獻融會貫通。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得出比較合乎實際的結論。以往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所以分歧較多,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些研究者有時僅據部分材料就勿忙做出了結論。
其三,敦煌文獻還為解決中國古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提供了材料。古代的敦煌是中國的一個地區。所以,敦煌文獻不僅對了解敦煌地區具有重要意義,其中的許多材料還反映了中原地區的一般情況。我國學者在利用這些材料方面也做了許多工作。如均田制即屬中國古代史的重大問題,但在敦煌文獻發現以前,對其實施情況的研究始終無法深入。我國學者主要依據對敦煌文獻中有關材料的具體探討,才為均田制實施與否的爭論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并對均田制的實質形成了新的認識。又如本文所述我國學者對敦煌法律文書的持續探索,不僅解決了許多有關唐律和唐代歷史的具體問題,還使學術界對久已亡佚的唐代令、格、式等法律文獻的形式、內容、性質有了具體而形象的了解,并為令、格、式的輯佚提供了樣式。再如本文所述我國學者對唐代勾官的研究,也是在具體探討敦煌、吐魯番文獻中有關勾官進行勾檢的記錄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唐代勾官和勾檢制度的整體認識。對敦煌文獻中反映中原地區一般情況的材料作微觀考察,容易使人產生細碎繁瑣的感覺,但從中獲得的知識不僅有助于認識同期中原地區的情況,有時對認識某一事物或社會現象在整個中國古代的發展脈絡亦有助益。如前述我國學者對中國古代社邑發展情況的探討和對中國古代書儀源流的考察,都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了從相關敦煌文獻研究中獲得的認識。
我國學者在利用敦煌文獻解決中國古代史上的問題方面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在這方面仍有許多工作有待完成。如有關佛教史和社會史方面的資料就利用得很不夠。在今后的研究中應提倡將敦煌文獻放到更大的背景下進行考察,在對敦煌文獻和傳世文獻、石刻文字中的相關資料作徹底調查的基礎上,將敦煌文獻中有關某一專題的資料放到唐宋時期甚至中古時期的歷史背景下進行考察。
其四,古代的敦煌是中國和世界接觸的窗口。所以,敦煌文獻中保存了不少反映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資料。我國學者利用這些資料探索中國與印度、中國與波斯等地的經濟文化交流,探索絲綢之路的貿易等課題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但與敦煌文獻中保存的這方面材料相比,還有許多工作可做。特別是在唐代,敦煌匯聚了中國、希臘、印度、中亞、西亞等不同系統的文化,這些在敦煌文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站在中古時期世界文化交流的高度,全面系統地發掘敦煌文獻中有關這方面的信息,將是21世紀的一項重大課題。
以上分析表明,我國學者在20世紀雖然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但尚未解決的問題和有待開展的工作更多。所以我們有必要認真總結過去的經驗,力爭在21世紀取得更大的成績。回顧20世紀我國學者利用敦煌文獻研究歷史的歷程,似有以下一些因素對研究的進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較大影響。
第一是資料的限制。對我國一般史學工作者而言,在前兩個階段能見到的敦煌文獻數量有限。雖然在第二階段我國已有英藏敦煌文獻主體部分的縮微膠卷,由于種種原因,能直接利用的人很少。多數史學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獻仍主要依靠少量很不完善的敦煌文獻錄校本。到第三階段,我國學者終于可在國內看到英、法和北圖所藏敦煌文獻的主體部分。但有關敦煌文獻的縮微膠卷和影印圖集實際上只有少數高校和科研單位有條件購置,對多數史學工作者來說,查閱敦煌文獻仍有諸多不便。另一方面,由于敦煌文獻多為寫本,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唐宋時期的俗體字和異體字,還有不少寫本使用河西方音。這就要求閱讀某件文書的學者不僅要掌握該文書有關學科的專門知識,還應當對敦煌的歷史、敦煌俗字及河西方音等整理敦煌文獻所需的專門知識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否則,即使有條件直接查閱敦煌文獻,在閱讀過程中也會遇到重重困難。正是由于這一原因,使得擁有縮微膠卷和圖集的單位,其資料使用率并不高,查閱者多為專門或主要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一般史學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獻仍主要依靠錄校本。可見,資料方面的限制,一直是影響我國史學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獻的重要原因。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應是21世紀的首要任務。因采用先進技術重排、精印敦煌文獻圖版是正確釋錄文字的前提,所以應在現有基礎上加快敦煌文獻圖版的編輯、出版步伐,力爭在下一世紀初葉完成這項工作。同時加快對敦煌文獻的整理、錄校工作,這既包括分類對敦煌文獻進行錄校,也包括按號對敦煌文獻作全面錄校。目前,分類錄校正在有計劃地進行,全面錄校的工程也已啟動。這項工作是將敦煌文獻推向學術界的基礎工程,是為史學工作者解除資料方面限制的關鍵步驟,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重視和支持,爭取在下一世紀的前20年完成此項工作。當然,錄校工作一定要保證質量。近年出版的一些錄校本即因質量不佳受到學術界批評。
第二是史學觀念的影響。在第一階段前一時期,用傳統方法治學的羅振玉等人對歷史典籍和有關政治史的資料比較感興趣。后一時期陶希圣利用《食貨》出版《唐戶籍簿叢輯》,顯然是其社會史史觀使然。第二階段我國學者對社會經濟資料關注較多,也明顯受到用史觀研究社會經濟史風氣的影響。在第三階段,隨著各種新的史學觀念和新方法的流行,利用敦煌文獻研究歷史各方面問題得以全面展開,其中尤以社會史觀念的重新流行影響最為顯著。數十年的敦煌文獻研究史表明,新的史學觀念和新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發掘敦煌文獻的史料信息,應該大力提倡。
篇(6)
4 榮新江:《于闐花氈與粟特銀盤---九、十世紀敦煌寺院的外來供養》, 胡素馨編:《佛教物質文化:寺院財富與世俗供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3年, 第246頁。
5 Hou Ching-lang, Trsors du m onastre Long-hingTouen-houang:unetude sur le m anuscrit P.3432, dans M.Soym i (dir.) , Nouvelles contributions auxtudes de Touen-houang (Genve:Droz, 1981) :149-168.中譯文侯錦郎:《敦煌龍興寺的器物歷》, 謝和耐、蘇遠鳴等著, 耿昇譯:《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 北京:中華書局, 1993年, 第77~95頁。
6 唐耕耦等:《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3輯, 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1990年, 第1~109頁。
7 姜伯勤先生曾討論敦煌與發自波斯的香藥之路、珠寶之路、琉璃之路, 其中琉璃之路的提法頗具新意, 但未能展開論述。參看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4年, 第64~69頁。安家瑤對此有所申論, 參看氏撰:《玻璃之路---從漢到唐的玻璃藝術》, 《走向盛唐:文化交流與融合》, 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05年, 第21~27頁。
8 (7) 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外來商品輯考》, 《中華文史論叢》第63輯, 2003年, 第72~76、73、74頁。
9 榮新江:《于闐花氈與粟特銀盤---九、十世紀敦煌寺院的外來供養》, 胡素馨編:《佛教物質文化:寺院財富與世俗供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246~260頁。
10 參看柯嘉豪:《少欲知足、一切皆空及莊嚴具足:中國佛教的物質觀》, 胡素馨編:《佛教物質文化:寺院財富與世俗供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36~37頁;John H.Kieschnick (柯嘉豪) ,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14.
11 嚴耀中:《佛教戒律與中國社會》,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第194~206、449~468頁。
12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年, 第2~4頁。
13 參看定方晟:《七寶について》,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4卷第1號, 1975年, 第84~91頁。
14 《大正藏》卷54, 第1105頁上欄。
15 《大正藏》卷12, 第346頁下欄~347頁上欄。
16 《大正藏》卷1, 第310頁下欄。
17 小野田伸:《古代ガラスを意味する「琉璃と「0) 璃について》, 《Glass:ガラス工藝研究會志》第43號, 1999年, 第27~30頁。
18 Berthold Laufer, 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Chicago: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2) 110-112.羅佛的看法代表當時學界的主流觀點, 現在看來需要根據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重新檢證。
19 羅佛在當時佛教和印度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 Berthold Laufer, 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p.111.這一觀點為薛愛華所承襲, 參見《唐代的外來文明》, 第537頁。
20 魏收:《魏書》, 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 第2270頁。余太山認為《魏書》所載波斯物產之文出自《周書》, 《魏書》原文雖然亦有這類物產的記錄, 只是由于并未超出《周書》范圍, 因而被《北史》編者用《周書》的記錄取代。換言之, 《魏書》原始記錄已不可得知。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 2003年, 第86頁。
21 例如在波斯珠寶商內沙不里 (Nayshābūrī) 寫成的第一部波斯語《珍寶書》中, 水精和玻璃就是同一個詞。Muh.m m ad ibn Abīal-Barakāt JuharīNayshābūrī, Javāhir-nāma-yi Niz.āmī, ed.Iraj Afshār (Tehran:Mīrās.-i Maktūb, 2004) .此材料承邱軼皓博士提示, 謹致謝忱。
22 宮嶋純子:《漢譯佛典における翻譯語頗梨の成立》, 《東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創刊號, 2008年, 第365~380頁。
23 孫望:《韋應物詩集系年校箋》, 北京:中華書局, 2002年, 第515頁。
24 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3年, 第120、5045頁。
25 (4) (5) 陜西歷史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著:《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年, 第214~215、101、97頁。
26 奈良國立博物館:《正倉院展 (平成五年) 》, 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 1993年, 圖49。
27 考古報告和研究論著中或稱琉璃、或稱玻璃的情形, 據引時依舊。
28 《大正藏》卷45, 第405頁上欄。按, 藥師琉璃光如來的名號, 在南北朝時期譯出的《佛名經》中即有出現, 之后在《藥師琉璃光如來本愿功德經》中更直接展示了東方琉璃世界之莊嚴光明, 所體現的佛性之凈真。
29 趙永:《論魏晉至宋元時期佛教遺存中的玻璃器》,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年第10期。
30 (11) 黃征、吳偉:《敦煌愿文集》, 長沙:岳麓書社, 1995年, 第213、215頁。
31 黃征、吳偉:《敦煌愿文集》, 第148頁。以上愿文錄文均據IDP圖版有所改正。
32 陳藏器撰, 尚志鈞輯釋:《本草拾遺》, 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2年, 第24頁。
33 徐堅等著:《初學記》, 北京:中華書局, 1962年, 第646頁。
34 王炳華:《瑯玕考》, 《西域考古文存》, 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 2010年, 第225~237頁。
35 中國歷史博物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編輯:《天山古道東西風》,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年, 第279、282頁。
36 大廣編集:《中國:美の十字路展》, 大阪:大廣, 2005年, 第134頁。
37 安家瑤:《北周李賢墓出土的玻璃碗---薩珊玻璃器的發現與研究》, 《考古》1986年第2期。
38 筱原典生:《脫庫孜薩來佛寺伽藍布置及分期研究》, 《石窟寺研究》第1輯,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0年, 第197~206頁。
39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定縣出土北魏石函》, 《考古》1966年第5期;夏鼐:《河北定縣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薩珊朝銀幣》, 《考古》1966年第5期。
40 安家瑤:《中國的早期玻璃器皿》, 《考古學報》1984年第4期。
41 安家瑤:《談涇川玻璃舍利瓶》, 《2015絲綢之路與涇川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287~292頁。
42 浙江省博物館、定州市博物館編:《心放俗外:定州靜志凈眾佛塔地宮文物》, 北京:中國書店, 2014年, 第62~63頁。
43 趙永:《論魏晉至宋元時期佛教遺存中的玻璃器》,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年第10期。
44 2017年浙江省博物館特展僅陳列四件, 且未加說明。見浙江省博物館、西安市臨潼區博物館編:《佛影湛然:西安臨潼唐代造像七寶》, 第201頁。
45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金銀玻璃琺瑯器》,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9年, 圖228。
46 陜西省考古研究所:《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7年, 第248、228頁, 彩版232。
47 吳立民、韓金科:《法門寺地宮唐密曼荼羅之研究》, 香港:中國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8年。
48 其中七件玻璃花圖版, 見寧夏固原博物館編:《固原文物精品圖集》 (下冊) , 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2013年, 第33頁。
49 羅豐編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6年, 第61、82、235~239頁。
50 王炳華:《吐魯番新出土的唐代絹花》, 《文物》1975年第7期。圖版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新疆出土文物》,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5年, 圖一八三。
51 之前對于絹花只有簡單報道, 前揭王炳華文認為隨葬的絹花只是墓主奢侈生活的一個側面反映, 未能從信仰層面對其性質和功能有所討論。
52 陳海濤:《唐代入華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及其原因》, 《華林》第2卷, 2002年, 第87~94頁;畢波:《信仰空間的萬花筒---粟特人的東漸與宗教信仰的轉換》, 榮新江主編:《從撒馬爾干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跡》,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年, 第49~56頁。
53 錄文參唐耕耦等:《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三輯, 北京:全國圖書館縮微復制中心, 1990年, 第99頁。
54 張廣達、榮新江:《于闐史叢考》 (修訂本)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年, 第89頁。
55 譚蟬雪:《敦煌民俗---絲路明珠傳風情》, 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2006年, 第244~246頁;榮新江:《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年, 第279~281頁;郭俊葉:《敦煌壁畫、文獻中的摩睺羅與婦女乞子風俗》, 《敦煌研究》2013年第6期。郭俊葉認為, 七夕與七月十五相距不遠, 佛教中七月十五日為盂蘭盆節, 此時有盂蘭盆會、放焰口等一些佛事活動。于闐公主于此時施舍磨睺羅, 有可能是七夕之物, 節后施舍于寺院供養。按, 此說過于牽強, 于闐公主所施舍之物, 應當是專為盂蘭盆節而造, 與七夕無涉。
56 黎毓馨考證靜志寺佛塔地宮為隋代初建、晚唐改造、北宋沿用, 見《心放俗外:定州靜志凈眾佛塔地宮文物》, 第8~23頁。可惜的是, 圖錄中沒有專門收錄玻璃器。
57 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 《文物》1972年第8期。
58 《文物探源》, 《文史月刊》2008年第12期, 封三。
59 宿白:《定州工藝與靜志、靜眾兩塔地宮文物》, 《文物》1997年第10期。
60 唐耕耦等:《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3輯, 第10、71、15、117頁。
61 干福熹:《中國古代玻璃的起源和發展》, 《自然雜志》2006年第4期。
62 關于漢唐間來自龜茲的異物, 參見余欣:《中古異相:寫本時代的學術、信仰與社會》,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 第294~322頁。
63 榮新江:《于闐花氈與粟特銀盤---九、十世紀敦煌寺院的外來供養》, 《綿綾家家總滿---談十世紀敦煌與于闐間的絲織品交流》, 以上兩文均已收入其《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 第263~277、278~294頁。
64 干福熹等著:《中國古代玻璃技術的發展》, 第128~140頁。
65 大英博物館監修, Roderick Whitfield編集、解說:《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ヨン》, 東京:講談社, 1982年, 圖55~1、55~2、56~2。相關研究參看安家瑤:《莫高窟壁畫上的玻璃器皿》,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研究論集》, 北京:中華書局, 1982年, 第425~464頁。
66 彩色圖版見大廣編集:《中國:美の十字路展》, 第136頁。
67 安家瑤、劉俊喜:《大同地區的北魏玻璃器》, 張慶捷、李書吉、李鋼主編:《4-6世紀的北中國與歐亞大陸》,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6年, 第38頁。
68 深井晉司:《圓形切子裝飾0) 璃碗---正倉院寶物白0) 璃碗源流問題について》, 氏著:《ペルシア古美術研究:ガテス器金屬器》, 東京:吉川弘文館, 1968年, 第7~46頁。
69 王銀田、王雁卿:《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7發掘報告》, 《北朝研究》第一輯,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年, 第143頁;王銀田:《北朝時期絲綢之路輸入的西方器物》, 張慶捷、李書吉、李鋼主編:《4-6世紀的北中國與歐亞大陸》, 第75頁。
70 馬艷:《大同出土北魏磨花琉璃碗源流》, 《中原文物》2014年第1期。
71 李昉等撰:《太平御覽》, 北京:中華書局, 1960年, 第3592頁。《舊唐書高宗本紀》作龜茲王白素稽獻銀頗羅。吳玉貴疑《太平御覽》所引《唐書》金下有奪文 (吳玉貴:《唐書輯校》, 北京:中華書局, 2008年, 第1069頁) 。唐雯主張《御覽》所引唐書并不是某一部書的專名, 而是包括劉昫《唐書》、吳兢等所編一百三十卷本《唐書》及唐代歷朝實錄在內的唐代各類史料文獻的總名。編修者將這一系列史料統一引錄作唐書, 正體現了唐至宋初的士人對于唐書這一概念的認識 (唐雯:《〈太平御覽〉引唐書再檢討》, 《史林》2010年第4期) 。因此, 本條史料雖有異文, 或別有所本, 未必為銀叵羅之誤, 且從下文考證來看, 金頗梨確實存在, 故仍其舊文。
72 魏收:《魏書》, 第2275頁。
7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陽永寧寺1979~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6年, 第136頁。
74 Hofkunst van de Sassanieden:het Perzische rijk tussen Rome en China (224-642) (Brussel:Koninklijke Musea voor Kunst en Geschiedenis) 266.
75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財政干部培訓中心漢、后趙墓發掘簡報》, 《文博》1997年第6期。
76 分型、成分及功能分析, 參看張全民:《西安M33漢代玻璃研究》, 《文博》2004年第1期。
77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幕府山東晉墓》, 《文物》1990年第8期。
78 關善明:《中國古代玻璃》,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2001年, 第70頁。
79 頗梨作為七寶之一, 在唐宋時期敦煌佛寺中的功用及其與密教供養觀念的關系, 拙文《敦煌佛寺所藏珍寶與密教寶物供養觀念》 (《敦煌學輯刊》2010年第4期) 曾作初步討論, 敬請參看。
80 《大正藏》卷17, 第345頁下欄。
81 《大正藏》卷49, 第306頁中欄~下欄。
82 《大正藏》卷51, 第87頁中欄。
83 魏征等撰:《隋書》, 北京:中華書局, 1973年, 第908頁。
84 《舊唐書》卷四七《經籍下》, 第2082頁。《唐六典》集賢殿書院條注略同 (李林甫等撰, 陳仲夫點校:《唐六典》, 北京:中華書局, 1992年, 第280頁) 。據下引韋述《集賢注記》, 史書庫縹帶之前缺字可補為青。
85 孫逢吉撰:《職官分紀》卷一五引《集賢注記》,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北:商務印書館, 1983~1986年, 葉八七背。陶敏輯校:《景龍文館記集賢注記》, 北京:中華書局, 2015年, 第222頁。文字和標點參考陶校而有所改易。
86 池田溫:《盛唐之集賢院》, 《唐研究論文選集》,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年, 第190~242頁。
87 拙文《〈唐六典〉修纂考》, 朱鳳玉、汪娟編:《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2010年, 第1161~1200頁。
88 王婕等:《一件戰國時期八棱柱狀鉛鋇玻璃器的風化研究》, 《玻璃與搪瓷》2014年第2期。
89 磯部彰編集:《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中卷 (文部科學省科學研究費特定領域研究「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研究成果) , 東京:二玄社, 2005年, 第67頁。
90 林世田、薩仁高娃:《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金光明最勝王經〉古代修復簡論》, 《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
91 林玉、董華鋒:《四川博物院藏敦煌吐魯番寫經敘錄》, 《敦煌研究》2013年第2期。
92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1年, 第47~48頁。
93 Yu X in, Material Culture, Reading Perform ance, and Catalogue System:Sutra Wrapper and Sutra Kerchief in Chinese Buddhist Rituals and the Form ation of the Canon, special lecture at Colum bia University Buddhist Studies Sem inarthe Center for Buddhism and East Asian Religion, January 29, 2016.
94 《大正藏》卷19, 第522頁上欄~中欄。
篇(7)
2007年1月3日,劉永明的博士后論文《唐五代宋初敦煌道教的世俗化研究》順利通過了由知名專家學者組成的評議委員會的評議,他也成為我國首位出站的敦煌學博士后。
熱愛歷史,結緣敦煌學
劉永明出身于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的一個農民家庭,這里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劉姓卻是當地難得的書香門第,所以,家族中有一種久遠的文化傳承。劉永明從小在爺爺的歷史故事熏陶下長大,高考時,他毫不猶豫地填報了蘭州大學歷史系,從此得以學習和研究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并與敦煌學結緣。
劉永明大學畢業時,敦煌學被重新重視起來還時間不久。地處大西北,蘭州大學在敦煌學研究方面可謂近水樓臺,所以在全國率先成立了敦煌學研究機構,形成了正規的敦煌學研究氛圍,也匯集了一些卓有成績的敦煌學研究學者。留校從事圖書資料工作的劉永明終日與古籍相伴,打下了比較堅實的文獻功底,并在與師長的溝通影響下,對敦煌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94年,劉永明在齊陳駿先生和樓勁先生的指導下,開始攻讀歷史系歷史文獻學(敦煌學)碩士學位。“是碩士研究生階段使我進入了研究之門。”時至今日,劉永明仍舊感激這段歲月,感激自己的導師。
2003年,從南京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劉永明難舍鄉土之情,回到母校工作,恰逢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學(敦煌學)博士后流動站成立,劉永明正式歸隊,成為第一位獲準進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員。
人一輩子,總要選擇一項畢生的事業。因為熱愛,劉永明選擇了敦煌學,而現在又成為率先進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員,從而促使自己在學業上的長足發展,劉永明深深地感到:“結緣敦煌學是我的幸運。”
甘坐冷板凳,愿啃硬骨頭
敦煌作為古代絲綢之路的咽喉,自古就是古代中國、古代印度、古代希臘和波斯(現阿拉伯地區)文化的交匯地。“敦煌”一詞,通常解釋為“大而盛”,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志》中進一步解釋道:“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
上個世紀初,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轟動了世界,藏經洞中發現的敦煌遺書包容了儒、佛、道、摩尼、祆教等多種宗教文獻,也保留了多種文字,是名副其實的世界文化寶藏,其文化價值不言而喻。但是,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絕大部分被列強劫奪而去,散落世界各地。現在資料雖然大多公布,但由于散亂、殘缺、損壞、真偽混雜,以及年代久遠等原因,資料的整理辨析十分不易。敦煌學研究之艱辛,可想而知。
在敦煌文獻中,道教文獻的數量僅次于佛教文獻,所以敦煌道教的研究是敦煌學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博士后階段,劉永明以敦煌道教這一學術研究的薄弱環節為主攻方向,一方面考察唐五代宋初敦煌道教的曲折發展,一方面深入探討道教向民間宗教、社會生活、民俗文化以及佛教等方面的滲透,將道教的世俗化問題落到實處。在研究中,劉永明在學界關于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掘出了一批敦煌道教文獻以及與道教密切相關的文獻,為敦煌道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內容;同時將道教放到了更為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進行研究。
敦煌道教文獻由于出自佛教藏經洞等局限性,反映本地區道教歷史的資料缺乏而且矛盾重重。但劉永明心甘情愿地去啃這塊硬骨頭,因為他認定,作研究就應該去選擇有難度又有意義的課題。
正是這樣,劉永明從敦煌的故紙堆中一點一點尋找道教存在的蛛絲馬跡,再根據自己的考察、分析,判斷出最終的結論。有一件事情劉永明記憶猶新,神泉觀是敦煌史料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一處道觀名,但是文獻記載的神泉觀詳細位置居然有三處:分別位于沙洲敦煌縣城的不同方向,而且描述都十分詳細。“神泉觀到底在哪里?”對此,學界未作深究。但劉永明一定要找出一個答案來。通過一段時間埋頭研究《道藏》,劉永明終于從行文格式中觀察出道觀地理位置描述有誤差的原因:根據教義規定,道士描述自己身份的時候,姓名前的地名為該道士的籍貫,而道觀名被夾在籍貫與姓名中間,意為強調,與道觀實際地址無關。由此他不但解決了敦煌道觀地址方面的一些問題,而且進一步認識到了道教的發展變化和道教教義方面的一些矛盾,對道教的歷史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實際上,每一次選擇,劉永明都會給自己一個挑戰,以挑戰促動新的進步。他認為,人原本是有惰性的,應該想辦法克服它。
2000年,劉永明到南京大學讀歷史學博士學位,出人意料的是,他沒有繼續自己原來的研究方向,而是選擇了道教醫學這一全新的研究領域。道教醫學需要將“道教”和“中醫學”跨學科交匯到一起,研究難度很大。劉永明這樣解釋他的選擇,“如果我繼續敦煌道教研究,成績得來更加容易,卻失去了當初選擇到南京大學讀博士的初衷。我的意圖就是要在新的環境中需求新的收獲。所以,我強迫自己在博士期間進行全新的研究,我沒有太多的功利心,只希望自己的視野更加開闊。”2003年,劉永明最終以《道教煉養學的醫學理論創造――腦學說和身神系統》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事后,劉永明回想起來認為,如果沒有當時的機會和勇氣,這篇論文就不可能產生。
《道教煉養學的醫學理論創造――腦學說與身神系統》的出籠,不僅讓劉永明順利獲得博士學位,而且拓展了他日后的研究方向。道教醫學的研究還讓劉永明體會到:“中國人應該懂些中醫知識。”醫學書看多了,劉永明已粗通醫理。現在他能從大夫開出來的方子里判斷出治療思路,家人有個頭疼腦熱,他也能自己開出方子,他笑稱父親吃他的方子最靈了。
劉永明現在是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副教授,他常教導學生,做學問必須不怕艱深,學術研究課題應該選擇難度大的做;只有深入其中,才能發現被忽視的內容,做出新意來,“只要下功夫做事,時間長了一定會有收獲。”
“學問需板凳甘坐十年冷,敦煌學研究面對如此繁復的歷史資料,更要格外吃苦。”劉永明說敦煌學研究其實比人們想象中的還要枯燥、艱苦。記不清多少個夜晚孤燈相伴;記不得多少個假日于敦煌遺書、敦煌道藏對面而坐;記不清多少次苦心拼湊殘片,使研究得以繼續;在敦煌的實地考察,也遠非旅游觀光那般悠閑自得,“但是,作為敦煌學研究者,就是窮盡
畢生精力,也要還敦煌文化以真實面貌,這是敦煌研究者的責任和義務。”十幾年的研究生涯,劉永明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關,在敦煌道教這個較為冷僻的領域里艱難跋涉,又樂在其中。他說,做學問最痛苦是在鉆進去的階段,過了那個階段會眼前一亮。好比陶淵明《桃花源記》里所說:“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為敦煌的明天而堅守
“敦煌學者,今日國際學術之新潮流也。”學者陳寅恪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對敦煌學的評價,時至今日也不為過。“敦煌所藏的資料多是唐五代以前的書卷,內容豐富,而且作者多為普通人。閱讀這些書卷,就像直接傾聽古人的聲音。這是經過文人雅士加工過的傳世文獻中所沒有的。這也是敦煌文獻的獨特價值所在。”
篇(8)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于8月18—20日在首都師范大學舉行。來自英、法、美、俄、日等國及中國大陸、臺灣的130多位敦煌學研究者歡聚一堂,共同回顧30年來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發展歷程,深入探討敦煌學的相關問題。本次學術研討會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敦煌研究院和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四家單位主辦,北京大學東方研究院、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敦煌學研究中心、吐魯番學研究院、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和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協辦。承辦單位是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還提供了贊助。
本次會議是近年來敦煌學研究領域規模最大的一次學術盛會,共收到論文100多篇。會議分兩個小組,進行了19場共105個學術報告,研討內容既有對敦煌吐魯番學研究工作與成果的總結,也有對敦煌吐魯番學前沿問題的關注,還有大量針對敦煌文獻和石窟藝術的個案研究,內容涉及古代歷史(包括法律、典章制度、社會民俗等)、文學、藝術、語言學、民族學、宗教學、古代科技(如醫學、天文等)等領域的問題。開幕式上,老一輩學者(80歲以上者)馮其庸、金維諾、寧可、沙知、王克芬、唐耕耦、白化文、陳國燦等在主席臺就坐。參會的學者既有中老年一大批知名學者,也有相當多的青年才俊,充分展示了當今國際敦煌吐魯番學的研究水平和學術陣容。本次學術會上,敦煌研究院12位學者參加了會議,包括樊錦詩、馬德、張先堂、趙聲良、王惠民、楊富學、楊秀清、張元林、陳菊霞、張小剛、張景峰、趙曉星。他們分別發表了在敦煌石窟、敦煌文獻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一些年輕學者的論文,顯示了新思路、新成果,引起了與會學者的關注。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于1983年,正值改革開放、文化振興的時代。中國學者們意氣風發,努力鉆研,極大地推動了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發展,30年來,不僅在相關的各領域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果,而且在國內許多重點大學開設了敦煌吐魯番學課程,有的學校還設立了敦煌學博士點,培養了大批青年敦煌學研究人才。30年間,國外收藏的敦煌學資料中最主要的部分如法、俄、英等國的文獻都逐步由中國學者整理,并在中國系統刊布,而國內各單位收藏的敦煌文獻也大部分整理出版。敦煌石窟方面也出版了《敦煌石窟藝術》、《敦煌石窟全集》等大型圖錄。與此同時,英國的IDP、法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及敦煌研究院等單位通過網絡建設,構成了極為便利的學術資源網站,這些工作極大地推動了敦煌學的全面發展。到21世紀初,中國敦煌吐魯番學的發展已經在很多方面產生了集成性成果。近年,榮新江、柴劍虹先生主編的30多卷本《敦煌講座》叢書(即將出版),正是中國敦煌學成果的集中體現,敦煌吐魯番學越來越展現其勃勃生機。
篇(9)
中圖分類號:I207文獻標識碼:A
敦煌變相與變文的關系,是藝術學界與文學界共同關心的一個重要課題。敦煌變相與變文的最初出現都與佛教直接相關,唐代以后,二者共同發展到比較成熟的階段,并且對其后的通俗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無論從文學史還是從藝術史角度來看,敦煌變相與變文的關系都具有比較重要的研究價值。
敦煌變相與變文之間有著比較緊密的聯系,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第一,變相、變文作為佛教的化俗手段,它們都可以稱為“變”;第二,講唱敦煌變文時,通常都配合使用了變相畫;第三,隨著敦煌變文的盛行,石窟中也出現直接根據變文創作的變相。由于藝術學與文學在研究視角、方法與目的等方面,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差異,從而導致敦煌變相與變文的關系這一課題,進入它們研究領域的緣起也不一樣。
一、研究的緣起
藝術學界對于此課題的研究,是伴隨著對敦煌變相研究的逐步深入而展開的。
初盛唐時期,敦煌變相已經發展到十分成熟的階段,這表現在如下方面:在構圖方面,它打破了傳統格局,采用鳥瞰式透視描繪出氣勢磅礴的場面;在形象塑造方面,人物面容、身姿、神態與衣飾等得到了很好的刻畫,創作者成功地表現出人物的身份、性格、年齡等特征;在線描與色彩運用方面,蘭葉描普遍得到運用,線條筆力較強,并且注意到了疏密、濃淡的關系;由于使用了絢麗奪目的色彩,畫面形成了比較熱烈的色調。西方凈土變、藥師經變、維摩詰經變等是此期常見的變相。
從吐蕃時期到其后的歸義軍時期,敦煌佛教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敦煌變相也發展到一個全新階段。變相從構圖、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較多沿襲了初盛唐,與此同時,這一階段的變相(尤其是歸義軍時期)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特點。其一,大型變相主體畫面的表現形式相互套用,缺乏創新精神,導致這一階段變相的形式,總體上具有比較明顯的“程式化”特點。與此同時,這些變相中的小故事題材明顯增多,盡管它們處于比較次要的位置,卻不乏創新之處。其中世俗生活里的人物、場景隨處可見,這在彌勒經變、維摩詰經變等中表現得尤其突出。其二,吐蕃時期以后,屏風式變相日益盛行,尤其是歸義軍時期出現了聯屏變相,為充分表現佛教故事創造了有利條件,聯屏賢愚經變、佛傳故相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作。其三,歸義軍時期,出現了直接根據變文等描繪的大型變相。如根據《降魔變文》創作的勞度叉斗圣變,根據《目連變文》創作的目連變相等。此外還有受因緣講唱風氣的影響而產生的作品,如莫高窟第72窟的劉薩訶因緣變相等。概而言之,吐蕃時期與歸義軍時期,敦煌變相的總體特點是題材的故事化、形式的程式化及內容的世俗化。
導致上述特點形成的原因是多種的,來自佛教“俗講”、“轉變”風氣的影響,就是其中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此,敦煌變相與變文的關系也受到了藝術史家的關注,從而逐步進入他們的研究視野。從藝術史的角度看,這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相比藝術學界而言,文學界更早關注到這一課題,并且展開了持久的探討工作。一些藝術史家最初也是在文學界的影響下,才開始研究這一課題的。下面就從文學研究的角度,討論一下問題的緣起。對于文學史研究而言,變文的發現具有深遠意義。在敦煌變文發現以前,宋元以來通俗文學史中一些重要的問題一直懸而未決,誠如鄭振鐸先生所說:
在“變文”沒有發現以前,我們簡直不知道“平話”怎么會突然在宋代產生出來?“諸宮調”的來歷是怎樣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寶卷、彈詞及鼓詞,到底是近代的產物呢?還是“古已有之”的?許多文學史上的重要問題,都成為疑案而難于有確定的回答。但自從三十年前史坦因把敦煌寶庫打開了而發現了變文的一種文體之后,一切的疑問,我們才漸漸的可以得到解決了。①
由此可見,敦煌變文發現的意義非同一般。學者們很快認識到了變文的研究價值,但是在其后的研究過程中,卻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其中首要的難題就是變文到底是什么。由于古代文獻中關于變文的記載十分有限,如此重要的問題在20世紀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答。
研究敦煌變文的過程中,一些學者逐步認識到借助于對變相的研究,可以有助于解決上述難題。相比變文而言,敦煌文書以及其他古代文獻中,關于變相的記載比較豐富,這就為兩者的比較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學者們在給變文下定義時,大多提到了變相之“變”。如鄭振鐸先生認為:“像‘變相’一樣,所謂‘變文’之‘變’,當是指‘變更’了佛經的本文而成為‘俗講’之意。(變相是變‘佛經’為圖相之意。)后來‘變文’成了一個‘專稱’,便不限定是敷演佛經之故事了。(或簡稱為‘變’)”②最有代表性的當是孫子書先生的觀點,他說:“蓋人物事跡(按:此指奇異的或變異的事跡)以文字描寫則謂之‘變文’,省稱曰‘變’;以圖像描寫則謂之‘變相’,省稱亦曰‘變’。其義一也。”③孫氏的觀點得到較多學者的認同。此外,關于變相的定義,還有其他不同的說法。
除了變相之“變”與變文有著密切關系外,變文講唱時還配合使用了圖畫(包括變相畫)。通過研究變文卷子以及其他文獻史料,學者們發現講唱變文時使用圖畫不是偶然的。大多數變文卷子中都帶有關于圖畫的提示語,如“××處”及“××時”等,這些常見提示語的作用是提醒聽眾觀看相關畫面。由此看來,從探討變文定義到變文講唱,都有必要研究變相與變文的關系。
古代畫史文獻中不乏變相的記載,但文獻提及的那些實物幾乎沒有保存下來,敦煌石窟中卻集中保存了大量的變相圖像資料。像歸義軍時期勞度叉斗圣變這樣的變相,不僅畫面的內容可以與敦煌變文比較研究,而且其中部分榜題與變文中的文字基本一致,從而可以與變文卷子進行比較研究。對于探討變相與變文的關系而言,這類敦煌變相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敦煌變相與變文的關系,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進入了文學研究的視野。隨著兩個不同領域的學者參與,使得多角度、多層面探討這一課題成為可能。
二、敦煌變相與變文研究的簡史
自20世紀初期敦煌變文發現以來,學術界對于敦煌變文校勘、整理以及研究的工作一直沒有中斷,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果。就研究而言,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主要成果,集中體現在周紹良、白化文先生所編的《敦煌變文論文錄》內,④其后的研究成果更加豐富,不勝枚舉。
就研究敦煌變相與變文的關系而言,值得重視的是敦煌變文校勘、整理以及匯輯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與一般的歷史文獻資料不同,藏經洞出土的敦煌變文文書殘損比較嚴重,其中存有大量俗體別字,訛、衍、脫的情況屢見不鮮,且因分散保存于不同國家的博物館中,由此凸顯校勘、整理以及匯輯工作的繁重。這一領域的主要成果有周紹良先生編《敦煌變文匯錄》(1954年)⑤、王重民等人所編《敦煌變文集》(1957年)⑥、潘重規先生的《敦煌變文集新書》(1984年)⑦以及黃征、張涌泉先生所編的《敦煌變文校注》(1997年)⑧。其中,《敦煌變文校注》收羅宏富,體例嚴謹,考證詳實,對于研究敦煌變相與變文關系等學術課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敦煌變相是敦煌藝術十分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敦煌變相與變文的關系的研究,隨著敦煌變相研究的深入逐步引起學者們的重視。
敦煌變相可以說是敦煌藝術中的精華,它不僅內容豐富,而且數量很大。僅就其中的“經變”而言,就有30余種(包括藏經洞出土的紙畫、絹畫在內),1300多幅。敦煌變相研究從收集整理圖像資料開始,經過畫面內容解讀、考證,最終發展到專題研究、綜合研究。
1937年,日本學者松本榮一先生發表了《敦煌畫的研究》(1985年再版)。此書根據藏經洞絹畫等藝術品與敦煌壁畫照片,對照佛教經文考釋了不少變相的畫面內容,為后來的研究奠定了較好的基礎。
20世紀50、60年代,中國一些學者開始運用圖像學方法研究敦煌變相,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果。周一良先生的《敦煌壁畫與佛教》⑨、金維諾先生的《敦煌壁畫〈園記圖〉考》及《〈園記圖〉與變文》⑩、潘茲先生的《敦煌莫高窟藝術》B11,可以看作此期的代表作。他們不僅探討了變相內容與佛經的關系,而且還注意到了敦煌變相與變文之間的聯系。此外,宿白、金維諾先生等還對佛教史跡故相進行了探討。
20世紀80年代以后,敦煌變相研究進入了全盛時期。一些大型經變分別按專題得到了系統研究,譬如法華經變、維摩詰經變、涅經變、彌勒經變、西方凈土變等等。此期敦煌變相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對照石窟榜題、佛經、敦煌文書及其他歷史文獻,考釋變相每一品的內容情節,與此同時,探討同一題材的變相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背景。在此背景下,敦煌變相與變文關系的研究也步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出現了一批研究成果。
史葦湘先生較早對聯屏賢愚經變與變文講唱的關系進行了探討B12。李永寧、蔡偉堂先生的《〈降魔變文〉與敦煌壁畫中的勞度叉斗圣變》B13,則充分結合變文、畫面內容與榜題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創見的觀點。樊錦詩、梅林先生《榆林窟第19窟目連變相考釋》一文,詳細考釋了榆林窟第19窟前室甬道北壁描繪的目連變相內容,指出這一目連變相直接取材于《目連變文》,并進而探討了它與《佛說十王經》插圖的聯系B14。榆林窟第19窟目連變相的發現,為研究敦煌變相與變文的關系提供了新的重要個案。筆者所寫《榆林窟第19窟目連變相與〈目連變文〉》一文,探討了該鋪變相創作的目的與背景等問題。B15
巫鴻先生的《何為變相?――兼論敦煌藝術與敦煌文學的關系》一文,則從畫面構圖的內在邏輯角度,對敦煌變相與變文的關系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提出關于敦煌變相與變文關系的新見解。根據敦煌變相的“奉獻式”創作目的以及其表現形式特征,他特別提出觀察敦煌變相與變文的關系的兩個原則:
我們需要從一個新的角度進行觀察。我希望在這里提出進行這種觀察的兩個原則:一、奉獻式藝術本質上是一種“圖像的制作”(image-making)而非“圖像的觀看”(image-viewing);二、圖像制作的過程與寫作和說唱不同,應有其自身的邏輯。根據這兩點原則,我將在下文中對描繪“降魔變”故事一大批壁畫做詳細的研究。B16
巫鴻先生對于奉獻式藝術本質的看法很有道理,這對于從圖像學角度研究宗教藝術具有重要的意義。他提出的這兩個觀察原則,有助于我們深入探討敦煌變相與變文的關系。巫鴻先生對敦煌“降魔變”題材繪畫等研究的結論是,“敦煌石窟的變相壁畫不是用于口頭說唱的‘視覺輔助’。但是這些繪畫與文學有聯系,并且這種聯系十分密切……敦煌藝術與文學的交互影響持續到以后的幾個世紀,在這一過程中,二者互相配合,共同發展,其形式日益豐富復雜。”B17在敦煌變相與變文的互動性方面,巫鴻先生所提出的觀點富有啟迪意義。
除了以上研究成果外,還有部分學者嘗試將個案研究與總體的理論分析結合起來。譬如美國學者梅維恒(Victor Mair)先生所著的《繪畫和演出――中國的看圖講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B18、日本學者秋山光和先生的《說話中的說話原文、畫面構成及問題――從〈變文〉及繪畫關系入手》就是其中的代表著作B19。筆者所著《敦煌變相與變文研究》B20,在探討敦煌變相與變文關系個案的同時,論述了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兩者之間的總體關系,提出了一些個人看法。
總體而言,本課題在個案研究與總體的理論分析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的進展。
三、敦煌變相與變文研究有待深入探討的一些問題
回顧本課題的研究歷史,可以發現中外學者已取得比較豐富的研究成果,其中,金維諾、巫鴻、秋山光和、樊錦詩、梅林等先生的成果,具有比較重要的學術價值。
在學者們的努力下,我們已基本了解敦煌變相與變文之間的一般關系。敦煌變相中,既有P.4524勞度叉斗圣變畫卷這樣可以配合變文講唱的作品,又有不少根據變文創作的壁畫,但它們很少用來配合變文講唱。敦煌變相與變文的關系具有互動性特點。相比而言,敦煌變相受變文的影響比較直接,而它對變文的影響較為間接。學術界通常以吐蕃時期為界,將敦煌變相分為前后兩期。與前期相比,后期敦煌變相的總體特點是,題材的故事化、形式的程式化及內容的世俗化。這在歸義軍時期的勞度差斗圣變等變相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上述特點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來自敦煌變文的影響值得充分關注。
由于敦煌變相與變文的關系比較復雜,跨越了藝術學與文學兩個學科,導致研究的難度較大,其中還有一些問題沒有得到很好解釋,有待于進一步深入探討。
首先,就已發現的考古資料來看,配合敦煌變文講唱的變相畫發現的數量極其有限。敦煌變文的講唱過程中,經常配合使用相關的變相畫,P.4524勞度叉斗圣變畫卷可能就是其中一個代表作。S.2614的首題是“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并圖一卷并序”,其中的“并圖”二字寫上后似又涂去,可能是抄錄者抄錄原來附圖的變文后,因為沒有臨摹該圖,所以又涂去“并圖”二字。這一題記表明,講唱此《目連變文》時,顯然配合使用了相關題材的目連變相。《全唐詩》收錄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一詩B21,不僅詩題中用了“看”字,而且詩中還有“畫卷開時塞外云”之句,由此可見,講唱此變文時也配合使用了畫卷。
敦煌石窟壁畫中的變相,有直接根據變文題材創作的勞度叉斗圣變、目連變相等,但是通過對這些壁畫作品進行的專題研究,學者們基本否定了它們配合變文講唱的可能性。就研究敦煌變相與變文的關系而言,直接配合變文講唱的變相多已失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本課題的深入研究。尤其是關于此類變相的創作情況等,由于存世作品太少,以至于無法展開具體的分析。
其次,關于敦煌變文的講唱儀軌以及使用變相畫的表演方式,現存的歷史文獻資料中幾乎沒有記載,它們也就成為有待于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梅維恒先生在其《繪畫與表演――中國的看圖講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一書中,曾比較詳細地考察了印度尼西亞“瓦揚•貝貝爾”等的講唱表演方式,并進而推測了敦煌變文的配圖講唱的方式B22。譚蟬雪先生的《河西的寶卷》一文,論述了河西地區宣卷活動中的配圖講唱方式,并進一步推論了其與敦煌變文講唱的關聯B23。傅蕓子先生還依據“立鋪”推測了圖畫的使用方式,他說:
但是這種畫卷既然說是“立鋪”,大概是將畫卷立起,便于給聽眾觀看,好似“看劇”一般,這圖幅是和講唱純佛教的變文輔助用的變相圖是同一作用的。可見講唱變文需要用圖像來作說明,佛教的變文是如此,非佛教的變文也是如此的。B24
學者們的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了解使用敦煌變相配合變文講唱的方式,但是由于缺乏歷史文獻記載等直接依據,這種配圖講唱的表演方式仍有待于進一步研究。筆者認為,關于此問題的研究應該注意如下兩個方面。其一,使用變相配合敦煌變文講唱的表演方式不會一成不變,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也可能不斷發生變化。早期的佛教變文講唱由于受到佛教俗講的影響,可能會出現“講者”、“唱者”合作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其中一人就可能兼有展示變相的職責。其后隨著變文在民間的不斷普及,它的講唱儀軌與表演方式可能不斷簡化,到了后期或許通常由一人承擔講唱與展示圖畫的所有職責。其二,根據現有的資料來看,配合變文講唱的變相主要有橫卷與立鋪兩種形式。這兩種形式的圖畫在創作構圖等方面有很大的區別,因而導致在配合講唱過程中的使用方式也不盡相同。橫卷便于手持展示,而立鋪更適合懸掛在固定的地方向聽眾展現。
以圖畫配合講唱的表演方式,在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藝術傳統中都采用過,因此,敦煌變文講唱的表演方式可以與世界各地的相關藝術形式做更充分的比較研究。這種比較研究,有助于深入揭示各自的藝術特點,與此同時,可以豐富我們對于世界各地配圖講唱藝術發展演變規律的認識。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對于當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與保護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再次,作為佛教藝術的兩種形式,敦煌變相與變文不可避免地會對后世的其他藝術門類產生影響。敦煌變文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隨著“化俗”功能不斷增強,自身也漸漸“俗化”了。“俗化”加快了變文的消亡,進而導致了敦煌變相與變文關系的瓦解。敦煌變文雖然消失了,但是它的題材內容、藝術形式乃至配圖講唱的方式,都可能對后世的其他藝術門類產生過重要影響。迄今為止,學者們大多從文本的角度探討敦煌變文對評話、寶卷、彈詞等的影響,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就配圖講唱方式的影響方面而言,則沒有得到充分關注。筆者所著《敦煌變相與變文研究》的下編“變文講唱藝術的影響”中,即對敦煌變文配圖講唱方式的影響進行了一些探討。皮影戲表演、寶卷的宣唱等,就可能受到變文配圖講唱方式的一些影響,與此同時,元、明以來小說話本等中插圖的淵源,也可能與配合變文講唱的變相圖等有著一定的關聯。敦煌變相與變文的影響問題,對于探討敦煌變相與變文的關系這一課題而言,雖然屬于邊緣問題,但是這一領域卻為本課題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間,在今后的研究中,此領域中有望獲得更多的突破。
最后,敦煌變相與變文可以視為佛教弘法的兩種通俗藝術方式,它們的產生及其發展演變與其承擔的宗教教化功能密切相關,換言之,其發展演變規律不同于非宗教藝術。在現代的佛教弘法活動中,變相與變文已經不再扮演重要的角色(變文早已退出了歷史舞臺),但是它們在唐代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以及其后的發展命運,對于現代的佛教弘法活動而言,仍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迄今為止,對于敦煌變相與變文的研究,主要限于文學、藝術學領域,佛學界沒有過多介入。就本課題領域的研究前景來看,佛學界可能會越來越關注本課題的研究,而它們的研究視角、方法、目的等顯然不同于文學界、藝術學界,因此,最終可能會在本領域取得更多的新成果。
綜上所述,自敦煌變文發現以來,學術界對敦煌變相與變文的關系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工作,取得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通過對此課題研究歷史進行了回顧,在評述已有成果的同時,也指出一些有待于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尤其是在跨學科領域的綜合研究以及跨文化領域的比較研究領域,本課題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有望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責任編輯:楚小慶)
①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頁。該書根據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校訂。
② 同上,第154頁。
③ 孫子書(即孫楷第)《變文之解》,《現代佛學》,第1卷第10期。
④ 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⑤ 周紹良編《敦煌變文匯錄》,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
⑥ 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⑦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1984年印。
⑧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中華書局,1997年版。
⑨ 周一良《敦煌壁畫與佛教》,《文物參考資料》,1951年第1期。
⑩ 金維諾《敦煌壁畫〈園記圖〉考》,《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10期;金維諾《〈園記圖〉與變文》,《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11期。這兩篇文章又被收入《敦煌變文論文錄》(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B11潘茲《敦煌莫高窟藝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B12參見史葦湘《關于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一文,《敦煌石窟內容總錄》,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B13李永寧、蔡偉堂《〈降魔變文〉與敦煌壁畫中的勞度叉斗圣變》,《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經變篇》,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B14樊錦詩、梅林《榆林窟第19窟目連變相考釋》,《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版。
B15于向東《榆林窟第19窟目連變相與〈目連變文〉》,《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1期。
B16巫鴻《禮儀中的美術――巫鴻中國古代美術史文編》,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366頁。
B17同上,第389頁。
B18梅維恒著,王邦維等譯《繪畫與表演――中國的看圖講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
B19秋山光和《說話中的說話原文、畫面構成及問題――從〈變文〉及繪畫關系入手》,《國際交流美術史研究會第八回:說話美術》,1989年版。
B20于向東《敦煌變相與變文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2003年,筆者完成博士學位論文《敦煌變相與變文》,本書即是在該文的基礎上寫作而成。
B21曹寅等編《全唐詩》,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8771頁。
B22梅維恒著,王邦維等譯《繪畫與表演――中國的看圖講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110頁。
B23譚嬋雪《河西的寶卷》,《敦煌語言文學研究通訊》,1986年第1期。
B24同④,第155-156頁。
Review on Dunhuang Bianxiang and Bianwen
YU Xiang-dong
篇(10)
[中圖分類號]K24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4)06-0024-03
敦煌寫卷P.2553號為《王昭君變文》孤本,學者歷來對其頗為關注,研究成果也頗豐,在此不再贅述。王昭君作為歷史人物最早記載于《漢書·元帝紀第九》和《漢書·匈奴傳下》中,但這兩者都只是單純敘史,并未對昭君本身的情感有任何描述,更不用說提到單于對昭君之寵愛了。《后漢書·南匈奴列傳》記載:“昭君字檣,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于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1}始將昭君出塞略帶故事感彩描繪出來。隨著時代變遷,王昭君已然成為一種文化象征,歷代文人對其揮毫潑墨,以自己的理解對其形象進行描繪和改造。而將昭君故事庶民化,則還是要數敦煌本《王昭君變文》。
對于昭君的命運,文人墨客多著以悲愴之色,我們比較熟悉的《西京雜記》、《昭君怨》、《昭君辭》等都是用悲劇眼光看待昭君出塞這一史實。這些加了自己主觀猜測的描繪究竟可否代替昭君本身,也要見仁見智了。在《漢書·匈奴列傳》和《后漢書·南匈奴列傳》中對昭君出塞后的生活有比較清楚的介紹,昭君于竟寧元年(前33)嫁于呼韓邪單于,但呼韓邪在建始二年(前31)死去,于是昭君又嫁給了呼韓邪單于的繼承人,成為新單于的閼氏,新單于又于鴻嘉元年(前20年)死去。{2}這以后對昭君再無任何記載,所以昭君的生卒年至今仍是一個謎,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昭君最少歷經二夫,并沒有很快死去。但是《王昭君變文》中昭君雖得到了可汗百般恩寵,但她還是逐漸羸弱,郁郁而終。為何變文給昭君的命運加注了死亡這么濃厚的悲彩呢?這得從《王昭君變文》的創作時代及其背景說起。
那么,《王昭君變文》到底為何時所作,這在學術界并未有定論,究其考證過程,我國學者有主要有以下十種觀點:高國藩認為是在“初唐至盛唐之時,也即唐代的上半期”; {3}容肇祖認為其作于公元767~857年{4},俞曉紅也持此觀點{5};邵文實認為在781~848年,也即吐蕃占領河西地區之時;{6}張壽林認為在850年左右;{7}陸永峰認為其應在848年左右;{8}鄭文認為其創作時間“必然在大中之前,甚至遠在大中之前,也就是遠在847年之前”;{9}張輝將時間縮至780~830年,或者稍晚一點的時間里;{10}程毅中認為其創作于8、9世紀之間;{11}張文德認為應該在817年前;{12}王偉琴認為其創作于786~816年。{13}對于國內學者考辨的內容,大家一般都比較熟悉,在此不再贅述。
下面說說日本學者根本誠主張的創作時限。其認為《王昭君變文》創作上限“不應該追溯到元和三年(808)以前”,{14}也就是說最早不能早于元和三年(808)。有以下兩個原因:
其一,在《王昭君變文》中明確涉及其創作年代的只有一句:“故知生有地,死有處,可惜明妃,奄從風燭,八百余年,墳今(上)尚在。”{15}根本誠認為這“八百余年”的起時應該是從漢哀帝在位年間算起,因為書中提到了漢哀帝,“后至孝哀皇帝,然發使(使)和番。遂差漢使楊少徵扙節和來吊”。漢哀帝的在位時間為綏和二年(前7)到元壽二年(前1),{16}昭君于元帝時出嫁匈奴,元帝之后是成帝即位,但是變文中沒有提到成帝,直接是由哀帝派使祭吊,那么可以推測昭君很可能是死于哀帝之時,也就是公元前7至前1年,那么文中的“八百余年”也應該為公元800年左右了。
其二,推算到其不早于元和三年(808)創立的第二個原因是咸安公主于這一年死去,可能是借由王昭君之故事來緬懷有著同樣命運的咸安公主。{17}筆者認同此觀點。因《新唐書·諸帝公主列傳》記載:
燕國襄穆公主,始封咸安,回鶻武義成功可汗,置府。薨元和時,追封及謚。{18}
《新唐書·回鶻列傳》(上)記載:
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湩酪,可汗常與共國者也。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為奸。三年,來告咸安公主喪。主歷四可汗,居回鶻凡二十一歲。{19}
由上可知,咸安公主為唐德宗第八女,是遠嫁到回鶻的一位公主,其在回鶻21年歷任四位丈夫,最終未能返回長安。《王昭君變文》很可能是由這件事情為契機而創作,以隱喻咸安公主之死,同時怨嘆敦煌陷蕃時間已久。這個理由似乎有些牽強,但根本誠先生沒有提及的第三個原因筆者想在此做一陳述。
據王偉琴《敦煌〈王昭君變文〉河西地域特征探析》對變文主人公最終去向地“紫塞”、“玉塞”等地名的考辨,皆指向敦煌。{20}敦煌在這一時期正處于吐蕃統治之下(吐蕃占領敦煌時期為公元786~848年),這應該是《王昭君變文》創作的大時代背景。而且,每一部文學作品的創立都必然有其創作契機,不能憑空而出。陷入吐蕃統治,民眾有過反抗,而且有史料記載河西民眾的反吐蕃情緒是非常激烈的。敦煌陷落吐蕃,敦煌庶民悲憤而惶惶度日,敢怒不敢言,只能付諸于筆端,借助于講唱舞臺宣泄悲憤之情。而咸安公主和親又和昭君出塞故事相似,出于當時敦煌陷落蕃邦和周邊的環境,便假借昭君之名來感懷咸安公主之死,同時也通過變文來悲嘆敦煌民眾的命運。
另外,變文中有“澣海上山鳴戛戛,陰山的是搌危危”,而在《新唐書·回鶻列傳》中有“明年(730)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為瀚海”。筆者認為,“澣海”即為“瀚海”,在變文殘缺部開始“搜骨利幹,邊草叱沙紇羅分”中的“骨利幹”應為回紇部落。《新唐書·回鶻列傳》記載: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為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奚結、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21}
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為瀚海,多覽葛部為燕然,僕骨部為金微,拔野古部為幽陵……其西北結骨部為堅昆府,北骨利幹為玄闕州,東北俱羅勃為燭龍州……{22}
由此可知,“骨利幹”為回紇的一個部落,而回紇在貞元四年(788)迎娶咸安之后請求改回紇為回鶻,意思是說其兇猛敏捷如同鶻一樣。變文中“衙官坐位刀離(剺)面,九姓行哀截耳珰”的“九姓”在《新唐書·回鶻列傳》中亦有“九姓者,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啒羅勿,曰貊歌息訖,曰阿勿嘀,曰葛薩,曰斛嗢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23}可見,變文中的主人公所嫁的地方是以回鶻的統治環境為背景的,而回鶻與唐朝和親始于肅宗干元元年(758),肅宗將寧國公主嫁于回鶻可汗,且派榮王之女陪嫁,后來寧國公主回國,而榮王之女留在回鶻,稱少寧國公主。少寧國公主“歷配英武、英義二可汗。至天親可汗時,始居外。其配英義生二子,皆為天親所殺”。{24}其死于貞元七年(791),雖然這時敦煌已經被吐蕃侵占,但是就其悲慘的命運來說,已經被視為“棄子”,早已淡出人們的視線之外,是無可汗恩寵可言的。相比之下,哀悼身為德宗親女的咸安公主,可能會更讓人信服。
從上述來看,將變文上限定位在808年咸安公主離世之年,筆者認為可信。
其創作下限王偉琴已經推之于816年之前,原因是李賀作過《許公子鄭姬歌》和《塞下曲》,說明李賀聽聞過《王昭君變文》相關的講唱故事。李賀死于816年,故有此推斷。據朱自清《李賀年譜》考證,李賀應生于貞元六年(790),卒于元和十一年(816)。從《許公子鄭姬歌》中“桂開客花名鄭袖,入洛聞香鼎門口”和“自從小靨來東道,曲里長眉少見人”兩句可以看出此詩的創作地點應該是洛陽,而李賀到過洛陽的時間經朱自清考證應為元和八年(813),由“元和八年癸巳(八一三)二十四歲。是年春,以病辭官,歸昌谷……冬十月,復入京,與黃浦湜別……賀之行當在十月望后,復有洛陽城外別黃浦湜詩云。”{25}可見其813年十月經洛陽,而在元和九年(814)秋天到了潞州(今山西長治),投靠張徹,寄人籬下兩年之后于元和十一年(816)回到昌谷,不久離世。筆者認為,根據其作《許公子鄭姬歌》的最晚時間應該不晚于813年十月,那么《王昭君變文》的成立時間也應該不晚于這個時候。
歸總起來筆者認為,《王昭君變文》的創作時間應該是808~813年。
變文前半部分殘缺,后半部分著力描寫昭君的思鄉情緒,而對單于也是極盡溢美之詞,將其描述為一個對昭君萬般疼愛、千般呵護的好丈夫形象。盡管昭君遠離故土,但是丈夫對自己如此費盡心思,親情的離失感應該會從愛情的滋潤中有所補償,但是昭君卻“既登高嶺,愁思便生……一度登千山,千回下淚……乃可恨積如山,愁盈若海……因此得病,漸加羸瘦”。{26}金岡照光認為,《王昭君變文》反映了悲劇性的女性像,{27}單于(可汗)越是對自己好,自己越是消受不起,越是顯示出了思念故土的無奈與痛楚。筆者認為變文作者越是極致描寫昭君所受的恩寵,就越是反襯出她迫切歸故土的赤子之心,其不僅反映出了當時悲劇性的女性像,更反映出了當時悲劇性的庶民面貌。用這種故事與現實的極大反差,映襯出當時敦煌民眾在吐蕃統治下積怨已久,百般呵護尚且還得不到人心,更何況吐蕃對敦煌是一種侵略霸占。
因此,通過《王昭君變文》可以窺探到敦煌庶民的一般心理狀態,身體是在吐蕃的統 治之下,但是心卻依然系著大唐,在吐蕃統治之下的生活如同“喪孝之家”、“敗兵之將”。身陷蕃里,透露著民眾的無奈,因為“不嫁昭君,紫塞難為運策定”,不把敦煌讓于吐蕃統治,敦煌將無法生存和暫時穩定,人民生活只會更加困苦。
綜上所述,變文通過對柔弱女子王昭君故事的改編,揭示出敦煌庶民階層身陷囹圄但寧死不愿屈從吐蕃的一般群體像。也正因為有著這樣的暗流涌動,所以才會有最終的張議潮揭竿吐蕃統治,將敦煌再次納入大唐領土,進入歸義軍繁盛時期的壯舉。
[注 釋]
{1}劉宋·范曄:《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941頁。
{2}{16}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809頁。
{3}高國藩:《敦煌本王昭君故事研究》,《敦煌學輯刊》,1989年第2期,第53頁。
{4}容肇祖:《迷信與傳說》,見《敦煌變文論文集》,第605~606頁。
{5}俞曉紅:《佛教與唐五代白話小說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頁。
{6}邵文實:《敦煌邊塞文學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頁。
{7}張壽林:《王昭君故事演變之點點滴滴》,《文學年報》,1932年第1期。見《敦煌變文論文集》,第631頁。
{8}陸永峰:《敦煌變文研究》,巴蜀書社2000年版,第174頁。
{9}鄭文:《〈王昭君變文〉創作時間臆測》,《西北師院學報》,1983年第4期,第29~30頁。
{10}張輝:《〈王昭君變文〉創作時間考探》,《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8月增刊,第161~162頁。
{11}季羨林:《敦煌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577頁。
{12}張文德:《王昭君故事傳承與嬗變》(博士學位論文),南京師范大學,2004年。
{13}王偉琴:《敦煌變文作時作者考論》(博士學位論文),西北師范大學,2004年。
{14}{17}〔日〕根本誠:《王昭君變文の成立年代考》,《東洋文學研究》,1961年第9期,第57頁、第64~65頁。
{15}{26}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啟功、曾毅公:《敦煌變文集》(上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頁、第124頁、第100~102頁。
{18}{19}{21}{22}{23}{24}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665頁、第6126頁、第6101頁、第6111頁、第6112頁、第6114頁、第6125頁。
篇(11)
據文獻記載,我國簡帛的發現、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漢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經,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學方法進行有目的有計劃地發掘、整理和研究,則開端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迄今將近一個世紀。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簡帛的發現可謂層出不窮,共出現了兩次大發現的:一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簡帛的年代涵蓋戰國、秦、漢、三國及魏晉。
戰國簡包括五里牌楚簡37枚、仰天湖楚簡43枚、楊家灣楚簡72枚、長臺關楚簡229枚、望山楚簡22枚、藤店楚簡24枚、天星觀楚簡70枚、九店楚簡344枚、隨縣楚簡240多枚、臨澧楚簡數十枚、包山楚簡448枚、秦家咀楚簡41枚、石板村楚簡4371片、郭店楚簡804枚、新蔡楚簡1300余枚等。
秦簡包括云夢秦簡1155枚(另有80枚殘片)、天水秦簡460枚、龍崗秦簡283枚、木牘1方、楊家山秦簡75枚、關沮秦漢簡500枚、王家臺秦簡800余枚、周家臺秦簡389枚、木牘1枚、青川秦牘1枚等。
漢簡包括敦煌漢簡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漢簡3500余枚、羅布淖爾漢簡71枚、武威漢簡600余枚、甘谷漢簡23枚、銀雀山漢簡4974枚、武威醫簡78枚、木牘14方、馬王堆漢簡900余枚、木49枚、定縣漢簡一批、鳳凰山漢簡428枚、木牘9方、居延新簡近兩萬枚、羅泊灣漢簡十余枚、木牘5枚、阜陽漢簡一批、大通漢簡400枚、張家山漢簡2787枚、胥浦漢簡17枚、木牘2方、清水溝漢簡一冊(27枚)、散簡14枚、懸泉置漢簡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書10件、紙文書10件、墻壁題記1件、尹灣漢簡133枚、木櫝24方、虎溪山漢簡1000余枚、孔家坡漢簡785枚等。
三國兩晉簡包括尼雅、樓蘭簡牘400余枚、紙文書728件、吐魯番阿斯塔那晉木簡1枚、南昌永外正街晉墓出土木刺5枚、木牘1枚、南昌陽明路三國吳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牘2枚、鄂城出土三國吳木刺6枚、馬鞍山出土三國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灘坡出土東晉木牘5枚、高臺晉墓出土木牘1枚、長沙走馬樓出土三國吳簡10萬多枚等。
帛書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漢代烽燧遺址中發現的幾件帛書、長沙子彈庫楚墓發現的“楚繒書”、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出土的帛書1件、長沙馬王堆3號墓出土的一大批帛書、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帛書10件等。
簡帛的整理與研究碩果累累
隨著大宗簡帛的相繼出土和陸續公布,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極大興趣和高度重視。據粗略統計,近百年來,經過海峽兩岸和國外學者幾代人的共同努力,已發表有關簡帛研究的論著數千種。這些論著大體上可分為簡帛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兩個方面。所謂基礎研究主要包括發掘報告、圖版、釋文、注釋、語譯、索引、字編、參考文獻和論著目錄等。而應用研究主要是應用新發現的簡帛資料(包括簡帛文字記載、實物以及器物、遺址、墓葬等),結合傳世典籍研究當時的政治、法律、經濟、軍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關系、中外關系、語言、文字、書法等各個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歸宿,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正如張政先生為《簡帛研究》題詞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義,璣珠重聯,審系篇題,終成圖籍,補史之逸。”簡帛的整理和研究,大體上是沿著這樣的軌跡進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漢簡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漢簡雖然首先由法國漢學家沙畹率先進行整理和考釋,但作出最大貢獻的應該首推我國學者羅振玉和王國維。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墜簡》一書以及王國維后來發表的系列論文,不僅對每枚簡文分類詳加考釋,而且應用新發現的簡牘資料,撰寫出許多研究漢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論文,尤其重視把敦煌漢簡所記載的內容和漢代烽燧遺址的情況聯系起來,力圖盡可能恢復漢代烽燧組織系統的原貌。《流沙墜簡》一書的精辟考釋和王國維研究敦煌漢簡的系列論文,不僅為當時的東西方學者所望塵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為近代簡帛學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漢簡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漢簡的整理和考釋,一開始便是由中國學者負責的。起初參加的學者有馬衡、向達、賀昌群、余遜和勞干等人,因為爆發,整理工作中輟。后由勞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釋,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和《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與此同時,勞干還發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漢簡的論文。《釋文之部》在變通《流沙墜簡》一書的基礎上,將居延漢簡分為文書、簿錄、簿籍、信札、經籍、雜類等六大類。《考證之部》和研究論文則沿用王國維所創立的“二重證據法”,進一步拓寬了研究領域,在居延漢簡和漢代歷史研究兩個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貢獻。1949年以前,重要的論著還有《漢晉西陲木簡匯編》、《羅布淖爾考古記》、《新獲之敦煌漢簡》、朝鮮古跡研究會《樂浪彩篋冢》、賀昌群《〈流沙墜簡〉補正》、《烽燧考》、陳盤《漢晉遺簡偶述》、《漢晉遺簡偶述續稿》和勞干《敦煌漢簡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別是隨著七十年代居延新簡和馬圈灣等敦煌漢簡的相繼出土,居延和敦煌漢簡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興未艾之勢,在應用簡牘來研究歷史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概括地說,在下列六個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和1957年《居延漢簡·圖版之部》的出版,使人們第一次得知貝格曼田野發掘工作的詳情,并能見到居延漢簡的全部圖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漢簡甲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灣、地灣、瓦因托尼、查科爾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漢簡所屬的出土地點。1980年出版的《居延漢簡甲乙編》發表了首批居延漢簡的全部出土地點,這對居延漢簡的斷簡綴合、冊書復原以及古文書學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義。(三)、早在《甲編》出版以后,就有學者曾撰文對《甲編》的釋文進行補正,如陳直《〈居延漢簡甲編〉釋文校正》、陳邦懷《〈居延漢簡甲編〉校語》、于豪亮《〈居延漢簡甲編〉補釋》等。當1980年《甲乙編》問世前后,又有許多學者接連不斷發表有關補正釋文的論著,如裘錫圭《漢簡零拾》、于豪亮《居延漢簡釋叢》、謝桂華、李均明《〈居延漢簡甲乙編〉補正舉隅》等。從1979年起,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漢簡,謝桂華、李均明曾反復審讀居延漢簡各種版本的圖版和釋文,又得有機會見到尚未公開發表的居延新簡的簡影,于是將以往諸家釋文逐一進行校訂,最后編撰成《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一書,在釋文的準確性上有顯著的提高。(四)、眾所周知,首批發現的一萬余枚居延漢簡,完整的冊書僅保留下來兩種,即由77枚簡(其中2簡無字)編聯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簡編聯成的“永光二年候長鄭赦予寧書”僅由此兩種簡冊可知,居延漢簡絕大多數原本都是用細麻繩編聯的冊書,出土以后,因為麻繩腐爛斷絕,原來的冊書都變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簡和斷片。為此,森鹿三以為將已散亂的簡牘恢復到冊書的本來狀態,至少恢復到接近原來的冊書的狀態,這是居延漢簡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礎工作。當1957年勞干《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將全部精力傾注到了“通澤第二亭食簿”(簿書)、卒家屬廩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復原上,率先開了復原居延漢簡簿籍冊書的先河。魯惟一繼承和發展了森鹿三的這種研究方法,出版了專著《漢代行政記錄》,從居延漢簡中復原出多種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冊書。對居延漢簡的斷簡進行綴合和冊書進行復原,其意義正如永田英正在《漢簡的古文書學研究》一文中所總結的:(1)在居延漢簡中,從全體上來看,簿籍簡牘占絕大多數;(2)簿籍簡牘和它們所記載的內容相應,各自具有固定的書寫格式;(3)所有的簿籍簡牘并不是孤立的個別記錄,而是被編聯成冊書的;(4)以簡牘的書寫格式為標準,有可能將大量的簡牘歸類集成;(5)隨著簿籍簡牘的移送和傳遞,就有可能形成文書。這就開啟了通往對簡牘進行古文書學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臺北出版了《居延漢簡補編》。《補編》彌補了以往歷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漢簡的圖版和釋文均未能核對原簡的根本缺陷。為了盡可能為字跡日漸褪色的原簡保留最好的簡影資料,而采用紅外線設備等先進科學技術,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鏡無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跡,清晰呈現,從而對以往諸家的釋文多有補正,在釋文的準確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華書局出版《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全書分為上、下兩冊,上冊為簡牘釋文,下冊為簡牘圖版,除收錄居延都尉所轄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與甲渠候官所轄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這兩處遺址所獲的全部簡牘外,還收錄了如下五宗簡牘:(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簡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簡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東燧所獲簡173枚;(4)1972年居延地區采集的散簡7枚;(5)1972年居延地區采集的地點不明的散簡14枚,合計8409枚。《居延新簡—甲渠候官》的出版標志著居延漢簡從此進入新簡和舊簡結合,進行綜合研究的新階段。
與此相應,在1949年以后,中外學者研究居延漢簡的論著不斷出版問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舉。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大庭修《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和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漢簡》上、下冊,則是研究敦煌漢簡的重要論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發現的簡帛,諸如云夢秦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尹灣漢墓簡牘、郭店楚簡等的研究也緊跟而上。(一)云夢秦簡的釋文公布伊始,便有許多學者撰寫論文。據臺灣東海大學吳福助教授統計,截至1995年止,已發表論著近千種。(二)馬王堆漢墓帛書和竹木簡,雖然還有三冊沒有發表,但經過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業已取得豐碩的科研成果。其中,帛書《老子》、《黃帝書》既是整理發表最早的,也是海內外學術界特別關注和研究論著最豐富的兩種帛書。《周易》和《易傳》盡管發表時間較晚,但由于其在中國哲學思想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決定,故一經發表,便成為研究熱點。經過研究,《周易》經傳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為止,已發表的帛書研究成果數以百計。(三)尹灣漢墓簡牘,僅就其數量而言,既無法與多達數萬枚的居延和懸泉置漢簡相比,也遠不如云夢秦簡、敦煌漢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和竹木簡,但因為它們出自生前曾任東海郡功曹史的師饒墓中,不僅內涵異常豐富,而且特殊珍貴。自1993年春尹灣漢墓簡牘發掘出土以后,連云港市博物館為了將這批珍貴的簡牘及早公諸于世,便迅速組織有關專家進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簡牘圖版、釋文以及文物、發掘報告、簡牘尺寸索引等在內的《尹灣漢墓簡牘》一書。此外,還發表了廖伯源《簡牘與制度——尹灣漢墓官文書考證》等專著、論文集、書法集以及論文近百種。(四)郭店楚墓竹簡的發現,引起海內外學者的極大關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簡》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學界的高度重視,迅速形成國際性的研究熱潮。專著、論文層出不窮,學術會議接連不斷,研究成果豐碩可喜。(五)《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館收購的楚簡和期盼已久的張家山漢簡也將出版。我們深信這些簡牘定會成為學者們密切關注的新熱點。
簡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來,簡帛學不論在出土、整理還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與此同時,簡帛研究中也存在諸多有待改進的地方,比如資料公布不及時、研究條件滯后、基礎研究工作不扎實等。整理、研究簡牘帛書資料,利用簡牘帛書資料促進古代史研究,現在只是開始,可以說是方興未艾,其深入發展還有待于將來。今后,這一領域發展的主要趨勢是:
第一、加快簡帛文獻資料的整理和出版,縮短從簡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間的周期。目前,許多重要的簡帛資料已出土很長時間,有的長達二十年,卻由于種種原因,遲遲不見公布,嚴重影響了簡帛研究的進程。希望各方人員通力協作,克服孤軍奮戰的局面,使出土簡帛資料早日公諸于眾。為了使大多數學者都能接觸到簡帛資料并應用于研究,每一批簡帛資料除了出版包括圖版、釋文的精裝本外,也應出版只有釋文的簡裝本。另外,如同編纂《甲骨文合集》與《殷周金文集成》,簡帛學界應考慮編纂包括秦漢簡帛在內的《簡帛集成》這樣的大型資料匯編,為人們對分散的簡帛資料進行比照和綜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現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條件。其一,采用紅外線設備,提高簡帛文字釋讀的準確率。其二,加快簡帛資料數據庫建設,使所有簡帛資料都能上網進行圖版檢索和全文檢索。這種方式比起手工翻檢來,無論檢索速度還是檢索效果,都要優越得多。
第三、加強簡帛資料研究的基礎工作。主要包括發掘報告的撰寫、簡帛文字辨釋、殘碎帛片的拼接、斷簡綴合、簡冊復原、簡帛內容考訂、資料索引等。這方面的工作細微、瑣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礎。有了翔實的發掘報告,有助于綜合研究的開展。文字釋讀準確,內容理解無誤,研究的結論才可靠。而殘簡碎帛的拼合與簡冊的復原,可以化腐朽為神奇,使無法利用的片言只語成為一句或一段有價值的資料。完備的資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個課題的研究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