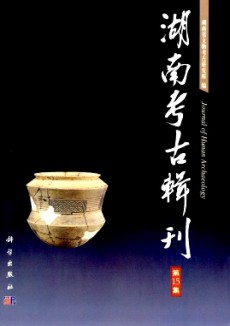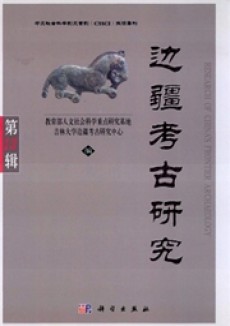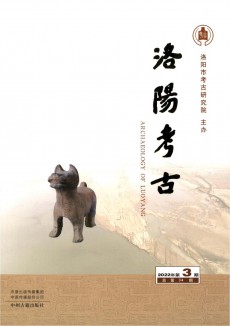考古學的概念大全11篇
時間:2023-11-20 09:53:36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考古學的概念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一、廣西改革開放30年會計實踐性教學的回顧
會計是一門技能性強和特別注重經驗積累的學科,會計教育的一項重要手段就是進行實踐性教學。會計實踐性教學包括在課堂教學中的案例教學,也包括到企業進行會計實踐和在校內的會計實驗室進行的會計模擬實驗。這一發展過程,可以通過會計實驗室的建設階段得到反映。
(一)無校內會計實驗室的階段
計劃經濟的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廣西會計教育的校內實踐教學是一片空白,實踐教學都是由學校提出計劃,再由自治區財政廳(當時叫自治區財政局)下發紅頭文件,指派各地市縣財政部門和一些國有企業的財務部門給予安排落實的。應該說,當時各地市縣財政部門和國有企業的財務部門對學校學生的實習是非常熱心和高度重視的,都專門派出了業務熟練的干部擔當指導教師,毫無保留地、手把手地指導學生實習,不但傳技術,而且還教如何為人處事;而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也是非常高的,不怕苦和累,事情搶著干。正因為老師教得歡,學生學得勤,學生都能夠在短時間內掌握會計工作的要領,并且為今后的成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時的學生很多都成為了單位的業務骨干或者走上了領導崗位。
(二)會計實驗室建設的探索階段
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企業作為最重要的市場主體,作為以營利為目的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向社會提供商品或服務的經濟組織,有它的獨立性,其正常的經營活動已經不再受政府行政部門的干預,會計專業學生的實習由學校提出計劃,再由自治區財政廳下發紅頭文件,指派各地市縣財政部門和一些國有企業的財務部門給予安排落實的做法已經行不通了。學生的實習只能由學校自己聯系、自己安排。80年代中期起,由于三方面原因導致了會計專業的學生到企業實習越來越難:一是到企業實習不再是免費的了,一些企業收取不算少的實習費用,學校和學生都承受不了;二是市場經濟下企業要講求效益,財務部門不再有冗員,會計崗位一個蘿卜一個坑,工作繁忙,生怕生手插入,使其忙中出錯、忙中添忙、忙中添亂,不再樂意當實習生的指導老師;三是市場經濟競爭激烈,企業的會計資料屬于重要的商業秘密,會計部門已經被視為企業的機密部門,一般不再歡迎外人介入。因為有后面兩種原因,致使實習生就是到了企業,安排到了財務部門實習,所能接觸到的經濟業務也極為有限,動手機會不多,甚至出現坐冷板凳,無事可做的情況,實習效果并不理想。面對會計實踐教學的困境,當時廣西會計教育工作者們開始思考建立會計模擬實驗室,使學生不出校門,也可以進行會計實踐教學。當時的廣西財經學校、廣西財政高等專科學校、廣西商業高等專科學校組織了部分老師深入企業調研,搜集資料,整理加工,分別編制出了《會計學原理》、《工業會計》、《商業會計》模擬實習資料,于1988年建立了廣西財經學校會計模擬實驗室、廣西財政高等專科學校會計實驗室、廣西商業高等專科學校會計實驗室,開了文科經濟管理類實驗室建設的先河。當時的這些會計實驗室都只是手工會計實驗室,盡管設備簡陋、資料粗放、項目單一,但是實驗資料的仿真程度都比較高,基本上解決了會計實踐教學的難題。需要說明的是,廣西財政高等專科學校會計實驗室還專門拍錄制作了工業企業生產流程和會計業務處理的錄像帶,在會計實踐教學中開始引用了現代化手段。
(三)會計實驗健全和完善階段
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幾年間,是廣西會計實驗室進一步健全、完善的年代。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手工會計實驗室相繼配置或更新了設備,有了專用的實驗桌,配置了幻燈機,放像機、憑證裝訂機等等;二是隨著企業會計準則的頒布和執行,實驗資料都及時地得到了修訂、補充和完善,實驗資料不再粗放,實驗項目也不再單一,不但有了學生畢業前必須進行的會計綜合模擬實訓,而且也有了一些主要會計課程理論教學結束后的課程實訓以及隨課進行的單項實訓;三是開始建立了會計實驗教學管理的相關制度;四是隨著計算機的普及,會計電算化的推廣,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各校紛紛投資建立了會計電算化實驗室,為會計電算化的教學和實訓提供了條件。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末,是市場經濟逼出了各校的會計實驗室。那么,2005年后,人們便開始了對會計實驗室規范建設的理性思考。2004年,廣西財政高等專科學校和廣西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合并組建廣西財經學院,由原財專會計模擬實驗室和原商專會計模擬實驗室合并整合建立了廣西財經學院會計實驗室。如何建設本科院校的會計實驗室引起了人們的思考。一些專家、教授先后主持課題對會計實踐教學和會計實驗室建設開展了研究,先后提出了“雙體系、雙平臺、多模塊”的會計本科人才培養模式、會計模擬實驗的運作方式在專業配合上,設置軍團組合式,在時間安排上采用波浪式,在選擇上采用菜單式以及會計實踐教學應采用立體實戰演練的模式等設想。2006年6月,廣西財經學院召開了實驗教學工作大會,作出了《廣西財經學院關于加強實驗教學工作的決定》,充分認識了實驗教學工作的重要意義,提出了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構建與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相適應的實驗教學體系的要求,對會計實驗室的建設給予了巨大的推動,會計實驗室建設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1.制度建設。會計實驗室隸屬于學院經濟管理實驗中心,為了保障會計實驗室實驗教學的正常運行,實驗室先后建立了實驗教學管理辦法,實驗教學工作實施細則,實驗室工作人員守則,實驗室各崗位工作責任制,實驗室開放管理辦法、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等等一系列的規章制度。如此完善而且科學規范的實驗室管理制度,應該是前所未有的。
2.會計實驗室硬件建設。經過整合,廣西財經學院會計實驗室現有手工實驗室三間、電算化實驗室四間,使用面積共計700平方米,可以同時容納640名學生進行實習實驗。會計手工實驗室均安裝有多媒體設備,方便直觀教學。會計電算化實驗室安裝有用友財務軟件、金碟財務軟件、博科審計電算化軟件、“無紙化手工會計模擬實驗”軟件(CS模式和BS模式兩種)。
3.實驗范圍和實驗項目的拓展。現在的會計實驗室不再是單純的會計實驗,已經拓展到了會計、審計、財務管理的實驗,而且各種實驗都已經具體細化為許多的實驗項目。
4.健全和規范實驗教材的建設。目前廣西財經學院會計系已經建設完成可供使用的實驗教材有會計學基礎綜合實驗教程、會計學基礎單項實驗教程、工業企業會計綜合實驗教程、崗位會計核算實驗教程、商品流通企業會計實驗教程、交通運輸企業會計實驗教程、網絡會計分步實驗案例、會計信息化仿真實驗案例、會計電算化實驗教程、財務管理綜合實驗教程、財務管理課程實驗教程、企業財務審計綜合實驗教程、審計電算化實驗教程、成本會計實驗教程、預算會計實驗教程等15種。實驗教材品種不僅達到了空前的齊全,為實現學生進行“菜單式”實習實驗選擇提供了可能,而且新編和修訂的這些實驗教材基本上達到了實驗教材的規范要求,改變了過去那種以大練習代替實驗教材的做法。由劉蓉等老師編寫的《企業財務審計綜合實驗教程》所附的自主研發的一套帶有“審計陷阱”的審計資料,目前在全國尚屬首創。
5.實驗形式多樣化。實驗形式包括手工模擬實驗、無紙化手工模擬實驗、電算化實驗和網絡實驗。手工模擬實驗有會計核算手工模擬實驗、審計手工模擬實驗和財務管理手工模擬實驗;無紙化手工模擬實驗是利用計算機實現會計核算無紙化手工模擬實驗和審計業務無紙化手工模擬實驗;電算化實驗是利用計算機、會計電算化系統軟件和審計電算化系統軟件以及ERP財務管理系統軟件實現會計電算化模擬實驗、審計電算化模擬實驗和財務管理模擬實驗,財務管理實驗還可以在學院的ERP實驗室模擬進行實戰演練;網絡實驗是指利用網絡服務器,將“無紙化手工會計模擬實驗”軟件和資料(BS模式)掛到網上,學生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通過網絡登陸服務器便可進行無紙化手工會計模擬實驗。
6.走產學研相結合的道路,開放式地建設會計實驗室。目前廣西財經學院已經與15家企業、會計師事務所簽訂了實習基地協議,與100多家企業、會計師事務所建立了密切聯系,學生可以到這些單位實習,老師也可以到這些單位進行業務實踐和科學研究。老師們可以通過對企業的調研,獲取第一手資料對實驗教材和實驗資料進行更新、修訂和補充。廣西財經學院與上海博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聯合開發可以穿透原始憑證的“審計之星”教育版教學軟件,擁有部分產權,是實驗室走產學研結合成功的一個例子。目前該軟件已開始向全國大專院校轉讓,也實現了實驗研究成果向社會生產力的轉化。2007年1月廣西財經學院制定了《廣西財經學院實驗室流動編制管理辦法(試行)》,為走產學研結合的道路,開放式地建設會計實驗室給予了制度保障。按照該辦法,實驗室根據其實際工作需要設置流動編制,有關人員帶著建設實驗室的任務或有關科研項目,經申請批準后以流動編制形式進入實驗室工作,其原人事關系不變,期滿后再回到原工作崗位。進入實驗室流動編制的老師可以到企業調研,結合實際地編寫、修訂實驗教材和實驗資料、完成科研項目。一年多的實踐證明,該辦法確實有效地推動了會計實驗室的建設。
(四)會計實驗室尚待解決的問題
經過20多年的建設,廣西的會計實驗室建設雖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在許多方面仍然存在著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現在:
1.實驗教材的建設尚不夠全面,尚不能開出足夠多的實驗項目供學生選擇,因此,會計模擬實驗的運作方式在選擇上,采用菜單式的設想目前尚無法實現。
2.會計業務不是獨立發生的,對會計專業學生的訓練也不能孤立地進行,但是,現在的會計實驗室對于如何將會計專業的模擬實驗置于全院財經類各專業(包括金融證券、財政稅務等)的綜合實驗之中,實現融資、申報納稅、供、產、銷全過程的,計劃、組織、協調各職能部門,通過生產經營的運作,與假設對手競爭的全仿真環境下的綜合實驗還沒有一個成熟的方案,因此會計模擬實驗的運作方式在專業配合上,設置軍團組合式的設想以及會計實踐教學應采用立體實戰演練模式的設想也暫時未能實現。
3.與其他文科經濟管理類實驗室一樣,現在的會計實驗室所能開出的實驗項目中,基礎操作性實驗居多,綜合應用性實驗較少,創新設計性實驗幾乎為零。
會計實驗室存在的以上三方面的不足,應該是今后會計實驗室建設努力改進的方向。
二、對未來會計實踐性教學的思考
縱觀會計實踐性教學的發展演變過程和會計實驗室建設的情況,要進一步改進會計實踐性教學,完善會計實驗室建設,必須從以下四方面進行思考和努力:
(一)進一步完善實驗教材建設
會計實驗教材應該符合以下要求:
1.規范性。會計實驗教材既不能是會計理論教材的翻版,也不能以大練習代替,應該嚴格按照實驗的要求規范地編寫。要認真地分析各門專業課程的知識點、技術技巧點,設計相應的實驗項目,提出每個實驗項目的實驗目的、實驗要求,提供實驗材料(資料)、實驗步驟(或者實驗路徑)。
2.仿真性。會計各門專業課程的實驗教材所提供的業務資料都應該取材于企業實際,應該置于企業的實際環境之中,符合實際情況,符合實際邏輯;所用的賬、表、憑證都應該是當前企業所實際使用的格式。
3.典型性。企業每天發生的經濟業務非常繁雜,許多業務是重復發生的,會計各門專業課程的實驗教材所提供的業務資料不能簡單地照搬企業實際,應該經過認真加工整理,擷取有代表性、典型性的經濟業務即可。
4.系統性。從會計某一門專業課程的實驗教材來說,它本身就是一個系統。它的內容、體例、應該開設哪些實驗項目統籌安排;從會計實驗室來說,會計各門專業課程的實驗教材構成了一個大系統,會計、財務、審計、金融、稅務等等相關的實驗教材如何有機地聯系應該通盤考慮。
5.全面性。從會計某一門專業課程的實驗教材來說,它所設計的實驗項目應該包括這門專業課程的教學大綱要求學生掌握的所有知識點、技術技巧點,不能有所遺漏;從會計實驗室來說,應該建設的會計、財務、審計、金融、稅務等等相關的實驗教材都應該建設起來,而且各行業的會計、財務管理的實驗教材和各種審計的實驗教材都應該建設起來。如能這樣,會計模擬實驗的運作方式在選擇上,采用菜單式的設想就可以實現了。
6.形象性。會計實驗教材不但應該是紙質的和電子文檔的,相當多的一些實驗場景、實驗對象的環境,一些具體的實驗操作需要形象地展示給學生。因此,會計實驗教材應該具有形象性,應該附以相應的音像資料。
(二)經濟管理類學生的實踐教學應該通盤考慮、統籌安排
財經院校一般除了設置有會計專業、財務管理專業、審計專業以外,還有金融專業、財政稅務專業、工商管理專業等等。在這些不同專業就讀的學生今天是同學,畢業后就是所從事職業的職業環境中的合作伙伴或者博弈競爭對手。他們所學的專業知識是互相交融,緊密聯系的。因此他們的實踐教學理所當然都應該聯系起來,通盤考慮、統籌安排、同時進行。這樣就能夠使得他們在學習期間體會到自己今后所從事的職業環境情況,如何應對自己職業環境中的合作伙伴或者博弈競爭對手。這就是會計模擬實驗的運作方式在專業配合上所采取的軍團組合式或者會計實踐教學所采用的立體實戰演練的模式的設想。
廣西財經學院已經成立了經濟管理實驗教學中心,統管了學院的經濟管理類實驗室,從形式上看已經為通盤考慮、統籌安排經濟管理類學生的實踐教學奠定了基礎和條件。現在缺乏的是能夠進行這方面考慮、安排的人才和經驗以及適合于通盤考慮、統籌安排、同時進行經濟管理類學生的實踐教學的系列實驗教材。萬事開頭難,只要經濟管理實驗中心的領導和同志們牽頭,各系配合,積極探索,大膽試驗,如何組織立體實戰演練模式的經濟管理類學生的聯合(綜合)實踐教學終會形成一個成熟的方案的。
(三)進一步完善和認真貫徹實驗室流動編制制度,使會計實驗室成為師生進行創新設計性實驗和其他研究性實驗的陣地
2007年1月,廣西財經學院制定了《廣西財經學院實驗室流動編制管理辦法(試行)》,規定教師帶著科研課題進專業實驗室工作,是一個很好的嘗試。經過一年多的實踐證明,這個辦法對促進實驗室建設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如果會計實驗室能夠引進相關企業數據庫資料,如果教師帶著科研課題進會計實驗室工作,進行科學研究(比如實證研究)的同時,能夠帶著一些比較優秀的學生一起進行研究,那么,會計實驗室就將成為師生進行創新設計性實驗和其他研究性實驗的陣地,創新設計性實驗幾乎為零的現狀必將改變。
(四)重視校外畢業實習,認真組織好校外畢業實習
校外畢業實習是學生走上社會,走上工作崗位前的一次實戰演練,是檢驗學生在校所學財會理論知識是否扎實,是否能夠運用于實際,同時也是了解社會,熟悉職業環境,學習為人處事,進一步增長才干的一次極好機會。通過校外畢業實習,可以為正式畢業后走上工作崗位時縮短不適應期,盡快拿起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應該說,校外畢業實習是會計實踐教學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培養合格會計人才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不應該以校內會計模擬實驗取代。對于校外畢業實習,學生應該重視,學校更應該重視。
學生重視校外畢業實習,就應該按照學校教學計劃的安排,在畢業實習期間,好好地到一個企業、事業單位的財務部門去虛心地拜在職會計為師,真正地進入會計角色,虛心地向師傅學習,學習他們認真細致的工作作風,誠懇熱情的服務態度,把師傅要你記的賬全部記好,把要你辦的事全部都辦好,實習結束時,讓師傅給你寫一個好的實習評語,讓實習單位給你寫一個好的實習鑒定。
學校重視校外畢業實習,就應該對每一屆的畢業生都要制定完整周密的畢業實習計劃;詳細地將學生自己落實的實習單位名稱、地址、聯系人、聯系電話記錄在案,動用學校的實訓基地單位、關系單位為不能自己落實實習單位的學生落實實習單位,不讓一個畢業生畢業實習落空。在畢業實習期間,學校應該派專業教師對學生的畢業實習進行巡回檢查指導,以便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解決,使畢業實習能夠嚴格按照計劃進行,不至于流于形式。
學生要把找工作與畢業實習結合起來,處理好兩者的關系。如果已經落實了就業單位的,而且現在又能夠接收你在那里實習,那就最好,實習階段就應該在那里好好地干,好好地表現。如果實習單位已經落實,但并非你已經落實的今后的就業單位,那就更應該安心地在實習單位好好實習。如果實習單位已經落實,但是就業單位沒有落實,為了找工作經常要外出跑一跑,要跟實習單位提前打招呼,請個假,不要不辭而別,隨便缺勤,影響實習單位的正常工作。把實習搞好,是為找工作打下好的基礎,而工作就業是學習、實習的目的。處理好二者的關系其實也是畢業實習的一個重要內容。
學校要像向用人單位推介畢業生一樣向實習單位隆重推介畢業實習生。自從有了會計實驗室,有了校內會計模擬實驗以后,會計專業的畢業生已經既具備了會計理論知識,同時也有了一定的會計技能技巧。實踐證明,現在的會計專業畢業實習生到實習單位不但不是累贅和包袱,不但不會給實習單位添忙、添亂,而且成為了實習單位業務工作的生力軍,可以幫助實習單位做很多事情。因此,不少曾經接收過會計專業畢業生實習的單位,現在每年都主動要求學校派畢業生去實習,有些單位不但不收取實習費用,而且還主動給實習生發放實習補助。因此,要使會計專業的畢業實習生能夠受到更多的實習單位歡迎,需要學校向更多的業務單位隆重推介。
【參考文獻】
[1] 唐振達,蘇藝.立體實戰演練法在高校會計實踐性教學中的應用[J].經濟與社會發展,2007,(01).
[2] 張臻,馬英華,唐振達.構建會計實驗教學體系[J].廣西財經學院學報,2006/S1.
篇(2)
中圖分類號:K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4)03-198-02
最近的十余年,中國的文化資源保護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社會對于考古學的發展也給予熱切的關注。但是,在國內公眾考古學還處于方興未艾的階段,還是一個亟待建設的系統,缺乏相應的理論體系和社會實踐經驗,公眾考古工作還很難進行。公眾考古學是一項復雜但是確實有重大社會意義的工程,不僅需要一段很長時間的探索,全民參與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環節。眾所周知,公眾考古的主體是公眾,考古發掘、博物館展示等資源對公眾起到的是引導作用,公眾對象的調查研究才是研究公眾考古學重中之重,公眾考古學的歸宿是公眾參與,如何做到“以公眾為本”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群眾,就需要我們對公眾考古中的公眾或是潛在公眾進行研究。
一、國內公眾考古學研究現狀
近十年來,國內學者主要圍繞公眾考古學的概念、理論、公眾考古學大眾化、公眾考古與傳媒、公眾考古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大討論。圍繞概念、理論的公眾考古學的定位問題一直是爭論不止,其探究主要原因是對“Public”一詞的理解。“Public”一詞在英語中可有兩種含義:一為“公共的,共同的”,一為“公眾的,與公眾有關的”。這里所謂的“公共”,即與國家、政府、公共機構相聯系,代表了社會大多數人利益的集合體,具有客觀性,共享性,整體性。由此可以看出公眾考古學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分。隨著公眾考古學的引進,國內諸多考古發掘現場已經開始對外開放并將行動付諸于實踐。國內學者則更側重對公眾考古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大討論、建言獻策。陳星燦先生在《公眾需要什么樣的考古》中從考古學的社會性質以及人民大眾的知識渴求度論述考古學與公眾存在一定的距離。所謂“公眾考古學”真正作為一種理念被介紹至中國是本世紀初以后的事情。2002年,宋豫秦發表《走向公眾的考古學》一文,指出了受傳統思維模式禁錮下的中國考古學所面臨的三個問題,即學科自身固步不前、學術成果對其他學科貢獻率低、公眾對考古學認可率認知率低等問題,呼吁考古工作者和考古學科的轉變,既面向學術又面向公眾事業方面;2003年9月,曹兵武在《中華讀書報》上發出了“中國亟須建構‘公眾考古學’”的呼吁;2005年8月,陳洪波在《中國文物報》發表《考古學和公眾的距離到底有多遠》對“公眾考古學”發展做了深入分析提出由于多種限制因素的存在,加之考古學的專業性質,考古學實際上距離大眾還是很遠,需要面對的一些問題進行進一步思考;2006年,郭立新、魏敏在《東南文化》發表《初論公眾考古學》,對西方公眾考古學理論進行了介紹,并對如何將興起于西方的公眾考古學與中國的社會現實結合起來,建立中國自己的公眾考古學進行了一些探索和思考;2007年,周暉、方輝譯校了美國公眾考古學研究者尼克?麥瑞曼在其主編的《公眾考古學》一書的序言――《公眾考古學的多樣性與非調和性》,將國外學者對公眾考古學的一系列較為成熟的認識,諸如公眾考古學的提出背景、內涵、研究目的、所需面對的問題等進行了介紹;青年考古學者范佳翎在各種場合積極宣傳推廣“公眾考古學”理念,并試圖說服一些地方考古研究機構開展向公眾開放考古現場的嘗試。同時,一些博士、碩士畢業論文開始將公共考古或公眾考古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一些大學和考古文物研究機構也陸續成立了公眾考古研究中心。
二、公眾的調查研究
為了更好地了解當今社會一般群眾對考古學的認識,2013年5月,本項目組成員5人于四川廣元市劍閣縣的聞溪鄉崖墓群周圍的居民點走訪調查。以調查問卷、訪談的形式對500名村民隨機進行采集樣本,其中有450份有效問卷。
通過初步統計與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問題。
第一個問題,人們對“考古學”的第一印象。主要集中在“古董”和“盜墓筆記等書籍”有68%的民眾。主要因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現今中國的“收藏熱”,日益高漲。這主要歸功于廣泛的媒體商業宣傳工作。如“尋寶”,“華豫之門”,“收藏馬未都”等電視節目的收拾了之日攀升,使民眾逐漸認識到“古董”等于“金錢”。而“古董”的來源大多數則來源于考古發現。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調查時選擇“盜墓筆記等書籍”選項的人群,幾乎全是青少年。他們對于考古學的第一認識全部來源于網絡小說。
當我們對第二個問題進行統計發現,民眾對于考古學家的工作主要認定為“挖墓”與“很神秘,以及“不知道”有85%的民眾。其原因通過第一的問題分析的結果,我們知道,錯誤的獲取知識的渠道是根本因素。媒體的商業宣傳,必然會涉及炒作問題,過分的推崇考古文物的經濟價值,使廣大的民眾片面的認為考古就是挖墓尋寶。還有另一部分人,受傳統思想的影響,認為考古就是挖死人的東西,總是避而遠之。對考古學感覺“很神秘,不知道”也是必然。
不過,感到慶幸的是,當地民眾的文物保護意識還是比較樂觀。通過問卷的問題的統計分析。當地民眾對于考古學家如何處理考古文物的態度,有37%的民眾認為應該交與博物館,22%的民眾認為交由考古單位做研究。還有對于考古發掘的主持者,有58%的民眾認為是考古學家,其次是政府人員。我們在與民眾交談中發現,當地文管所的文物保護宣傳工作開展的比較好。在“你知道離你最近的考古遺址嗎?”問題中有超過94%的民眾知道,他們附近正在發掘的文溪鄉崖墓群。
當問到“通過什么渠道了解考古”以及“對于你來說,你是如何了解考古學”時,59%民眾選擇了電視節目“鑒寶”和“華豫之門”,只有19%選擇了書籍,這說明現在民眾,尤其是青少年深受電視影響,閱讀能力弱化,喜歡以形象、直觀的方式接受知識。從另外一個方面,也反映出傳統的以書本獲取知識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在生活節奏逐漸加快的今天,民眾對知識的獲取也更加“快餐化”、“通俗化”和“圖像化”。更愿意把一切與經濟掛鉤。
在問到“你知道四川有哪些考古遺址嗎?”時有25%選擇金沙遺址,23%選擇三星堆遺址,45%選擇武侯祠博物館,7%是其他。這充分說明武侯祠博物館的宣傳營銷的成功。對于成都來說,武侯祠博物館已經成為了成都地標性文物單位。不僅是四川,在全國也是十分著名。
在問到“你會主動了解身邊的考古發掘和考古遺址嗎?”有95%以上的人,不會主動了解考古發掘和遺址。也有超過55%的人不愿意作考古發掘的志愿者。其原因我們了解到,普通民眾不明白考古的真正目的,他們只在意考古文物的經濟意義。但是不可否認,廣大民眾對考古學依然是興趣盎然,無論出于什么目的,經濟?好奇?探險?這是民眾了解考古學的第一步,對于未來還是充滿樂觀的。
三、公眾考古學發展的建議
(一)傳播途徑的改進和創新
眾所周知,博物館與考古學是相生相伴的機構,必然承擔考古資料的展示工作。所以加強對博物館的利用,以人為本,盡量用生動、形象的方式將各類文物系統化的展示出來。在展示過程中,增強趣味性、互動性,融入考古學的基礎知識和文物保護的理念,引導公眾形成正確觀念。其次,講座是一種非常好的普及考古學知識的方式,專業人員可通過講座向公眾傳遞正確、嚴謹的考古學知識,而且講座的舉辦相對比較容易,對于時間、空間的要求較小,且受眾面較大,所以應當努力發揮講座的集群效應,定期舉辦考古學講座,使講座內容系統化,擴大聽眾人數與范圍,以取得更廣泛的效果。為加強公眾對講座的積極性,可以考慮在不威脅文物安全、不影響工作秩序的前提下,定期開放考古發掘現場,組織公眾實地的了解考古發掘過程。還有,我們知道電視媒體是公眾了解考古學的最主要方式,是公眾考古工作中不可忽視的渠道。但在利用時應當注意:要選擇主流媒體,考慮考古節目或新聞報道的客觀性、真實性。對于如何將專業語言轉化為公眾語言,應必須有專業人士的參與,不可放任自流,任憑電視媒體以收視率為目的妄自加工考古資料。必須反對炒作,保持考古學的純潔性,要堅持嚴謹與科學,不能為了迎合公眾的喜好就放棄科學嚴謹,所有的科普釋讀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不能偏離考古學公眾化的初衷。再次,是數字化時代,網絡具有強大的傳播力,其受眾面極大,方便快捷,時效性極好,具有相當大的利用空間。我們必須加強對網絡的利用,創辦論壇、網站,考古信息與相關知識,同公眾進行互動,使公眾更廣泛的參與其中。但在利用網絡的同時要注意法律監督和道德輿論引導。最后,考古志愿者的選拔。選出一部分文化水平高、熱愛考古、樂于奉獻的公眾,以義工的形式,參與到考古工作中,了解考古工作,以其親身體驗,慢慢感染滲透其他公眾。
(二)文博學界觀念的轉變
學界掌握著最核心的資源,學界的態度決定了考古學能否公眾化。轉變觀念,學科發展與文物保護都離不開公眾。所以學界要加強考古發掘的整理和研究,把堆積如山的考古資料轉化為公眾能理解的語言和其他學科可以利用的知識,轉化為通俗易懂的普及性讀物,提高民眾的文物保護意識。學界應作為考古公眾化的主體,要發出有關公眾考古理念的更大的聲音,引起政府與社會更多的關注和重視,提供更多的政策、經濟支持和公眾的理解與參與。
篇(3)
三十年過去了,當年蘇秉琦先生基于現有資料對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探索雖具有前瞻性,然這一理論在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實踐中也日漸顯現出理論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而出現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確。“區、系、類型”理論中出現了考古學文化的“區”、考古學文化的“系”和考古學文化的“類型”,蘇秉琦先生對“區、系、類型”的定義如下:“在準確劃分文化類型的基礎上,在較大的區域內以其文化內涵的異同歸納為若干文化系統。這里,區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顯然,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與原有的“考古學文化”、“考古學文化類型”等考古學專業名詞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義不同。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定義,“區、系、類型”中的“區是塊塊”,屬于空間范疇;而考古學文化區也同樣屬于空間范疇。在蘇秉琦先生劃分的六大區系中,“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即海岱地區;盡管蘇秉琦先生認為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屬另一個文化系統,實際上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可歸屬海岱地區的一個亞區。而“長江下游地區”則包含了太湖地區的“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寧紹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寧鎮地區的“北陰陽營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學文化。
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劃分,“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大致相當于“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而長江下游地區卻包含著“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陰陽營文化”和“薛家崗文化”的分布區。因此“區、系、類型”的“區”似乎既可等同于一個考古學文化區,又可包含若干個考古學文化區。此外,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區”,或以省命名,如“陜甘晉”“、山東”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長江下游”“、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等。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學的基本標準④,而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中“區”的命名,既無統一的標準,又無規律可尋。“區、系、類型”中的“系是條條”,顯然屬于時間范疇;而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發展演進也同樣屬于時間范疇。根據蘇秉琦先生對大汶口文化發展演進為龍山文化和馬家浜文化發展演進為良渚文化的論述,“區、系、類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發展演進而不包括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文化分期屬于量變,而文化的發展演進則屬于質變,質變是由量變的積累而發生的突變。因此,“區、系、類型”中的“系”與文化分期、文化演進的相互關系的區分,“系”的時間概念與文化分期和文化演進的時間概念的區分,顯然存在著概念上的不確定性。在同一考古學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圍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異,往往又分為若干類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史家類型”、“廟底溝類型”、“秦王寨類型”、“大司空村類型”和“西王村類型”等,而龍山文化則有“城子崖類型”和“兩城鎮類型”等。在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系、類型”中,“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顯然“區、系、類型”中的“類型”與考古學文化的類型有著不同的概念。
“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與分支也同樣存在概念上的不確定性。綜上所述,“區、系、類型”的“區”不等同于考古學文化區的“區”“,區、系、類型”的“類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學文化類型”。考古學理論既須以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作為理論基礎,又須符合形式邏輯的基本原理。一個學科中用同樣文字的專業名詞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著不同的定義,似乎有悖于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同一律。考古學理論應具有普遍性,應適用于不同時期的考古學研究。“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如僅適用于新石器時代考古學,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區系的劃分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區。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蘇秉琦先生在“區、系、類型”中劃分的六大區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學文化空白區的情況下劃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區與下游地區。因此六大區系的劃分出現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東部和江淮中部地區在當時還是考古學文化的空白區,還沒有龍虬莊、侯家寨、凌家灘、雙墩等遺址的發掘,還沒有龍虬莊文化、雙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灘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據對古史傳說的研究,劃分了華夏、東夷和苗蠻民族集團的空間分布范圍。其中將渤海灣以西到錢塘江以北劃為東夷民族的分布空間⑤(圖一)。而蘇秉琦先生將我國東部沿海劃分為“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和“長江下游地區”,顯然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區,顯然強調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考古學屬性而忽略了區系劃分的民族學屬性。“‘考古學文化’是代表同一時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內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遺跡和遺物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應該屬于某一特定的社會集團的。由于這個社會集團有著共同的傳統,所以在它的遺跡和遺物上存在著這樣的共同性。#p#分頁標題#e#
與民族學的資料相結合,可以認為,新石器時代的各種‘考古學文化’類型是體現當時各個部落和部落聯盟的存在,與民族的形成有關。⑥”蘇秉琦先生提出“區、系、類型”理論是“滿天星斗說”、“多元一體模式”和“古文化、古城、古國”、“古國———方國———帝國”、“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等系列文明起源理論的基礎,目的是為了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然蘇秉琦先生在討論“區、系、類型”理論時卻認為:“目前還有這樣一種傾向:即把某種考古學文化與文獻上的某個族人為地聯系起來,把它說成××族的文化。從長遠來說,進行這樣一項工作可能是研究工作的一個方面;但是現在,在對各地的考古學文化的內涵、特征、與其他文化的關系以及上下的源流等的認識還很不充分,還不具備做這種探索或考訂的時候,似應先做些基礎性的研究,積累起必要的原始素材,以備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礎。……我們這里所作的有關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的探討,只是基于現有資料所作的探索。”因此,蘇秉琦先生在劃分六大區系時就存在著考古資料的局限性;由于受到考古資料的局限,六大區系的劃分也缺乏一定的民族屬性,或偏重了考古學屬性而忽略了民族學屬性。二、“考古學文化系統”簡介“隨著新材料的發現和新的研究成果的推出,補充、修正、完善蘇先生建立的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體系是我輩考古同仁責無旁貸的任務。⑦”由于“區、系、類型”理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與“區、系、類型”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論相一致的考古學“文化系統”理論,可能比“區、系、類型”理論更符合我國考古學的實際;考古學“文化系統”理論與原有的考古學專業名詞也不致相互混淆或產生歧義。考古學“文化系統”的概念是尹達先生提出的。1955年,尹達先生在《論我國新石器時代的研究工作》一文中指出“:在我國的廣大地區以內,由于自然環境的不同,經濟生活基礎的某種差異,在新石器時代的漫長時期里,不同的地區當然可能發展成為不同的文化系統。⑧”
1961年,曾昭燏和尹煥章先生在對青蓮崗文化的分布范圍、文化年代和文化特征進行了全面論述時,第一次區分了“考古學文化”和“考古學文化系統”兩個不同的概念,并對“青蓮崗文化”和“青蓮崗文化系統”進行了客觀闡述,并特別強調了我國東部沿海自北向南的諸多新石器時代遺址都屬于青蓮崗文化系統⑨。在曾昭燏和尹煥章先生發表對青蓮崗文化的研究之前,除尹達先生提出的文化系統外,夏鼐先生還提出了考古學文化的定名問題⑩,因此曾昭燏和尹煥章先生所提出的“青蓮崗文化”和“青蓮崗文化系統”的命名,或許受到尹達先生和夏鼐先生的影響,而“青蓮崗文化”和“青蓮崗文化系統”的提出,則是曾昭燏和尹煥章先生對“考古學文化”和“考古學文化系統”的理解和實踐。1980年,石興邦先生在對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進行廣泛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文化系統的命名,將7000~6000年之間的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系統分別命名為“仰韶文化系統”“、青蓮崗文化系統”和“北方細石器文化系統”。“青蓮崗文化系統的分布范圍是黃淮下游、東方沿海、渤海灣周圍及東南半壁。……青蓮崗文化系統根據歷史民族學,可分為三個系統:一、東方沿海一帶的稱夷;二、長江中下游及其支流為三苗后來的百淮;三、五嶺以南閩江、珠江及紅河流域為百越。”石興邦先生對“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定義如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系統即人類社會生活系統。文化系統大致包含社會結構、社會組織、社會制度、宗教禮儀、道德規范、語言系統、生活習俗、生產方式、行為能力、藝術風格、審美情趣等要素。諸多要素中,既有繼承性和保守性等延續性要素,亦有開放性和擴展性等變化性要素。……在一個文化體系中,由于地理環境的不同和人文歷史、生產技術的發展等原因,可逐漸形成不同的文化共同體,即文化共同體與文化共同體之間,或存在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而形成新的文化共同體,或相互排斥和相互爭斗而形成強勢文化共同體取代弱勢文化共同體
“考古學文化”和“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區別在于考古學文化強調的是小區域內的文化共性和大區域內的文化個性,而考古學文化系統強調的則是大區域內的文化共性。新石器時代的民族文化區往往包含若干個考古學文化區,因此,考古學文化區與民族文化區的相互關系,同樣是考古學界無法回避的課題。如何解釋考古學文化區與民族文化區的相互關系,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劃分與研究有可能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因為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定義顯然包含著考古學文化的民族屬性。考古學文化系統包括相同的文化生態和文化景觀、相同的文化地域和民族特征、相同的文化傳統和原始宗教等諸多因素。系統是由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各個要素構成的整體。文化系統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文化系統包括物質文化系統、社會文化系統和精神文化系統等要素,即文化系統由技術的、社會的和觀念的三個子系統構成,技術系統是決定其他兩者的基礎。文化系統可分為三個層次的序列:技術層為基礎,觀念層最高,社會層居中輰訛輥。因此考古學文化系統內應包含著若干個考古學文化,一個考古學文化即可獨立構成一個考古學文化系統中的子系統。考古學與民族學分屬不同的學科,考古學文化區與民族學文化區的基本概念,既有相似性,又存在差異性:考古學文化區是考古學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間。考古學文化區的劃分是根據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通過對文化遺跡、文化遺物等文化遺存的分析、比較、研究而確定的考古學文化分布的空間范疇。民族文化區是民族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間。民族文化的分布區域,即民族文化區。民族文化區是一個具有連續空間范圍、具有相對一致的自然環境和相同或近似的歷史過程、具有某種親緣關系的民族傳統和具有一定共性的文化景觀所構成的地理區域。
考古學文化區的劃分強調的是考古學文化面貌的個性,強調的是物,而民族文化區的劃分強調的是民族文化的共性,強調的是人。考古學文化區屬考古學范疇,民族文化區屬民族學范疇。考古學人群共同體與民族學人群共同體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考古學人群共同體形成考古學文化區,民族學人群共同體形成民族文化區,盡管考古學人群共同體與民族學人群共同體有著許多相同的特征。顯然,民族文化區的分布范圍要大于考古學文化區,即一個民族文化區內可分布著若干考古學文化區。因此,在建立考古學文化區和文化譜系的基礎上,考古學研究應在劃分考古學文化系統與民族文化區的基礎上,根據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基本理論進行考古學與民族學相結合的綜合研究。雖然考古學文化系統與民族文化區是兩個不同學科的不同概念,然而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系統與民族文化區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因此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地理空間大致與民族文化區相當。考古學文化系統是由同一區域內的考古學文化按一定關系構成的有機聯系的整體。考古學文化系統強調的是文化共性,即考古學文化的共性和民族歷史文化的共性。考古學文化系統的概念應包含“地理、民族、文化”三個最基本的要素,即“共同的地理單元、共同的民族集團和共同的文化傳統”構成了考古學文化系統。考古學文化系統建立在各考古學文化已充分研究和基本明了的基礎之上,在更為廣袤的空間里,宏觀地、動態地研究區域內各考古學文化發生、發展、交融、演進和衰亡的全過程,同時也可與文化系統區域外的考古學文化系統動態地進行文化系統與文化系統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考古學文化系統不是一個氏族、一個部落、一個部族或部落聯盟的文化,而是一個民族集團的文化,顯然這種大范圍的考古學文化系統具有一定的民族性,表現出一定的民族屬性。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的劃分和考古學文化譜系的建立,是考古學研究的必然歷程;而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劃分,同樣是考古學發展的必然歷程。#p#分頁標題#e#
考古學的最終目的是研究人與社會,是研究人的行為能力與行為過程的發展過程,研究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的演變過程,研究人類社會發展演進的歷程。因此考古學文化區的劃分僅僅是考古學研究中的一個階段,而不是考古學研究的終極目標。石興邦先生指出:“新石器時代是各種文化模式形成的階段,也是各個國家和民族文化的淵藪。我國原始文化的多樣性和特點,都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分布在世界各個角落的人類群體,為適應不同的生態環境而創造出不同類型的文化。新石器時代,也是各個族系的形成時期。同一人種分布在不同的地區,在不同的生態環境中形成了不同的生活習俗和文化模式,同一模式的陶冶下,形成了經濟類型、生活習俗、和地區意識的人們群體,由氏族———部落———部族而發展為民族,在文明時代,即形成國家。”輱訛輥因此,劃分文化系統的目的是為了探求民族和國家的形成過程,與“區、系、類型”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考古學文化區的劃分與研究是考古學發展的必然階段,而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劃分與研究也應是考古學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向縱深發展的必然階段。考古學文化系統與民族文化區具有相同的共性,即考古學研究應逐漸向民族共同體的研究發展,逐漸向考古學文化系統即民族文化區的研究發展。根據考古學文化定名的基本原則,遵循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以各系統中最具代表性的遺址命名考古學文化系統,我國的新石器時代可分為“仰韶文化系統”、“青蓮崗文化系統”、“屈家嶺文化系統”、“曇石山文化系統”和“昂昂溪文化系統”等考古學文化系統。
仰韶文化系統的分布范圍大致為遼、冀、蒙、京、津、晉、陜、豫、甘、寧、青的一部或全部;青蓮崗文化系統的分布范圍大致為遼、冀、豫、魯、皖、蘇、浙、滬的一部或全部;屈家嶺文化系統的分布范圍大致為豫、鄂、皖、贛、湘、渝、川、甘、黔、桂的一部或全部。其中豫西、豫北和豫東、豫南分屬華夏、東夷與苗蠻民族文化區的分布范圍,因此中原亦成為仰韶文化系統、青蓮崗文化系統與屈家嶺文化系統的交會地帶;曇石山文化系統的分布范圍大致為浙、皖、贛、閩、湘、粵、桂的一部或全部,甚至還可能包括臺、瓊等南島;昂昂溪文化系統的分布范圍大致為黑、吉、內蒙、陜、甘、寧、青的一部或大部,甚至可延伸新疆東部(圖二)。我國古代有華夏、東夷、苗蠻、百越和匈奴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等民族集團。仰韶文化系統、青蓮崗文化系統、屈家嶺文化系統、曇石山文化系統和昂昂溪文化系統的分布空間,大致相當于我國古代民族文化區的分布范圍。考古學文化系統與民族文化區的對應關系分別為:仰韶文化系統———華夏民族文化區;青蓮崗文化系統———東夷民族文化區;屈家嶺文化系統———苗蠻民族文化區;曇石山文化系統———百越民族文化區;昂昂溪文化系統———北方草原民族文化區。五個考古學文化系統與蘇秉琦先生劃分的六大區系的大致對應關系為:仰韶文化系統———陜甘晉鄰近地區,青蓮崗文化系統———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和長江下游地區,屈家嶺文化系統———湖北和鄰近地區,曇石山文化系統———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地區;昂昂溪文化系統———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劃分與六大區系的唯一區別是將“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和“長江下游地區”合并為一個文化系統。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系統的民族屬性主要表現為:一、有共同的地域和經濟生活;二、有共同的語言風俗和道德規范;三、有共同的圖騰崇拜和;四、有共同的藝術風格和審美情趣;五、有相同的生產技能和生活方式等;民族屬性在考古學文化系統層面上的主要表現為:有共同的聚落形態與建筑形態;有共同的墓地形態與埋葬習俗;有共同的裝飾習俗和宗教禮器;有共同的生產對象和生產物品;有共同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器等。因此,考古學文化系統兼有考古學與民族學的雙重特征,而且還可將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劃分為若干不同的層次結構:第一層次,考古學文化系統;第二層次,考古學文化;第三層次,考古學文化類型;第四層次,考古學文化的分期輲訛輥。
由于“青蓮崗文化系統”是唯一對“六大區系”中的兩個區系進行合并的文化系統,因此有必要對青蓮崗文化系統進行簡要的論述。青蓮崗文化是曾昭燏和尹煥章先生于1961年提出的。曾昭燏和尹煥章先生將江蘇境內的原始文化分為“青蓮崗文化、劉林文化、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和湖熟文化”。1972年,吳山菁先生發表了《略論青蓮崗文化》輳訛輥,不僅取消了劉林文化,而且以青蓮崗文化系統的概念取代考古學文化的概念,構建了一個延續時間達2000余年并縱跨五大流域、三大平原的“青蓮崗文化”,由此引發了上世紀70年代關于青蓮崗文化的討論輴訛輥。夏鼐先生認為:青蓮崗文化的定名可以取消,建議將“江南類型”和“江北類型”的青蓮崗文化分別叫做“大汶口文化”和“馬家浜文化”輵訛輥。蘇秉琦先生也認為:“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新石器諸文化,盡管它們呈現出許多相似之處,存在明顯的共性,這只能說明當時它們之間具有比較密切的聯系,而不能說它們屬于一個某種的人們共同體。”輶訛輥顯然,蘇秉琦先生已注意到“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新石器諸文化……呈現出許多相似之處,存在明顯的共性,”但由于缺乏江淮地區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資料,又囿于夏鼐先生的影響,故也“只能說明當時它們之間具有比較密切的聯系,而不能說它們屬于一個某種的人們共同體。”上世紀90年代,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建議,國家文物局設立了“蘇、魯、豫、皖地區古文化研究”重點課題。江蘇、安徽先后發掘了高郵龍虬莊輷訛輥和周邶墩訛輮輦、興化南蕩輯訛輦、阜寧陸莊輰訛輦和東園村輦輱訛、東臺開莊輲訛輦、蚌埠雙墩輳訛輦、定遠侯家寨輴訛輦和含山凌家灘輵訛輦等遺址,并先后命名了龍虬莊、雙墩、侯家寨和凌家灘等考古學文化。通過一系列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基本廓清了江淮地區古文化的序列,建立了江淮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譜系。#p#分頁標題#e#
江淮地區的考古發掘填補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空白,并由此建立了東部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譜系:海岱文化區: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江淮東部文化區:龍虬莊文化;江淮中部文化區:雙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灘文化;江淮西部文化區:薛家崗文化;寧鎮山脈文化區:丁沙地遺存→北陰陽營文化;太湖流域文化區: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由于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基本建立了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譜系,為重新討論“青蓮崗文化系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江淮東部考古學文化區的確立和龍虬莊文化的命名,填補了將海岱地區與太湖地區之間的空白,將我國東部沿海地區連為一體,可清楚地發現各考古學文化區之間存在的差異,也可清楚地考察我國東部沿海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共性。“青蓮崗文化系統”屬考古學文化系統,考古學文化系統強調的是文化的共性。曾昭燏和尹煥章先生歸納的青蓮崗文化系統的共性是:生產工具多斷面成橢圓形的石斧、扁平穿孔石斧、斷面近方形的條形石錛和長方形的兩孔或一孔石刀;骨制器具相當普遍,以骨魚鏢最為突出;使用的陶器,大多掛紅衣,尤以掛紅衣的泥質缽形器為最突出;炊器多夾砂質的鼎和釜,不見鬲形器;釜皆圜底,肩部多有突出卷沿一周;帶嘴的壺形器很多,式樣是多種多樣的,還有質料較粗而掛紅衣的鬶形器;裝飾品有玉玦、玉璜、玉環、玉管、石鐲等;當時人死后埋在公共墓地里,葬法和頭向有一定的規律,用或多或少的器物隨葬。石興邦先生歸納的青蓮崗文化系統的共性是:早期以釜形、罐形器為主,中晚期以三足和鏤孔的圈足器為主;生產工具以精致的石器和骨器為主;以種植稻谷和農業生活為主,飼養豬;普遍出現了進步的刻玉工藝;普遍流行拔牙習俗;崇尚裝飾。曾昭燏和尹煥章先生劃分的青蓮崗文化系統的分布空間主要為東夷民族文化區,而石興邦先生劃分的青蓮崗文化系統的分布空間包括東夷、苗蠻和百越民族文化區,因此,曾昭燏和尹煥章先生劃分的青蓮崗文化系統的分布空間應更接近于史實。進入21世紀,對東夷民族文化區考古學研究的結論逐漸趨向一致。2004年,王永波先生通過對齊魯史前文化與三代禮器的研究,通過對考古學文化與古代民族集團相互關系的研究,提出了“鼎———鬶文化系”的概念,認為東夷民族屬“鼎———鬶文化系”(含鼎、鬶、匜、盉、杯、尊等),而華夏民族則屬“斝———鬲文化系”。東夷民族集團的分布范圍包括桑衛、海岱、江淮、太湖諸地區,并根據對諸地區考古學文化的研究,將東夷民族集團的主要特征歸納為“鼎鬶文化”和“崇日尚鳥”輶訛輦。
2011年,韓建業先生在分析了龍虬莊文化與大汶口文化的關系后,提出東部沿海地區“鼎、豆、壺、杯、鬶(盉)文化系統”的概念“:大汶口文化的形成與龍虬莊文化的北上有關,形成后又與江淮、江浙地區文化不斷交流,加上仰韶文化同時向兩地施加影響,從而使得海岱和江淮、江浙地區的文化面貌越來越近似,逐漸在東部沿海地區形成‘鼎、豆、壺、杯、鬶(盉)文化系統’。”輷訛輦考古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發現、發掘和研究考古學遺存、命名和研究考古學文化或文化類型、在考古學實踐的基礎上歸納考古學基礎理論和基本方法的歷程。隨著學科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化,越來越多的相關學科介入了考古學領域,尤其是民族學。民族文化區的空間范疇內應包含著若干個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氏族、部落、部族或部落聯盟;考古學文化系統的空間范疇內也同樣包含著若干個考古學文化區和處于不同發展階段考古學文化。因此,考古學的考古學文化系統的時空范疇大致與民族學的民族文化區相當。而“青蓮崗文化系統”、“鼎———鬶文化系”和“鼎、豆、壺、杯、鬶(盉)文化系統”等考古學文化系統的提出,皆表現出考古學逐漸向考古學與民族學相結合的發展趨勢。根據以上學者的研究,對東夷民族文化共性進行進一步的綜合研究,兼及考古學文化和民族文化屬性,并兼及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層面,可將青蓮崗文化系統即東夷民族文化區的文化特征和構成要素歸納如下:反映原始宗教和圖騰崇拜的對象為“鳥”,即“鳥圖騰”;反映審美情趣、宗教巫術和工藝技能的物化物主要為“玉制品”;反映宗教禮儀的物化物主要為“鼎、豆、壺”,或“鼎、豆、壺、杯(觚)、鬶(盉)”;反映生產方式和生產對象可用“飯稻、羹魚”表述,尤其是“羹魚”。以上四個文化特征中,除第一個文化特征貫穿始終外,后三個特征都是在文化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根據以上文化特征,青蓮崗文化系統的空間范疇應從山東半島至太湖流域,包括海岱地區、江淮地區、寧鎮地區和太湖地區的不同空間、不同時間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膠東貝丘遺址、雙墩文化、侯家寨文化、龍虬莊文化、薛家崗文化、凌家灘文化、北陰陽營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具有上述文化特征的“淮系文化”,甚至遼東地區的貝丘遺址等也可納入青蓮崗文化系統。簡言之,青蓮崗文化系統即“東夷民族文化區”。同樣,其他考古學文化系統也可歸納出各自的文化特征和構成要素,因不屬本文的討論范疇,不贅述。
考古學文化的空間分布、文化內涵、文化特征、文化源流以及文化與文化之間相互關系等必要的原始素材的積累,是研究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基礎;而古史傳說的梳理與考證,同樣是研究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基礎。傅斯年先生根據對華夏和東夷民族的研究,認為“中國大陸土地上最早的文明發源地在渤海附近、九河故地,東夷是我國古代文明最高、最成熟之種族,山東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中心。輯訛輧”蒙文通先生根據對古代民族的研究,也同樣認為海岱(即東夷)民族是我國古代文化最發達的民族輰訛輧。俞偉超先生根據對考古學研究,認為“在4000~5000年以前的我國的文明曙光時代,以東方的龍山和東南的良渚文化的光芒最亮,同時期黃河中游的龍山階段諸文化,其發展水平還達不到這個高度。輱訛輧”徐旭生先生根據對古史傳說的研究,劃分了華夏、東夷和苗蠻民族集團的空間分布范圍。其中將渤海灣以西到錢塘江以北劃為東夷民族的分布空間,東夷集團中較早的氏族“有太皞,有少皞,有蚩尤。輲訛輧”新石器時代,隨著社會經濟和聚落規模的發展,聚落與聚落之間的相互作用也不斷地增大,社會組織更趨復雜化,于是萌生了超越聚落群的社會組織。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規模較大、作用力較強的聚落,就有可能處在優先發展和社會變革的前沿,其中聚落內部組織管理的強化是聚落獲得優先發展的重要條件,同時又是導致階層分化的主要原因。而強化管理的有效途徑就是削弱聚落內部各氏族的獨立性,強化聚落內部的統一性。聚落內部統一性的強化從而形成了考古學文化。由于社會形態發展的不平衡,在一個民族文化區內包含著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氏族、部落和部族;在一個文化系統內也同樣包含著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考古學文化。#p#分頁標題#e#
隨著聚落形態的發展和社會物質逐漸豐富,聚落之間的相互作用逐漸加劇,社會內部的分化也逐漸向聚落群乃至更大范圍擴張。聚落之間的相互作用表現為考古學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與相互融合。社會形態的發展往往通過增強聚落群的作用和削弱其他聚落的獨立性,導致聚落群內部的結構發生重大變化或進行重新調整和組合。聚落群內部結構的變化導致考古學文化發生變化,從而出現了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劃分與界定,可將考古學研究導向兩個不同的層面:可在同一考古學文化系統內部動態地研究各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如發生與衰亡、互動與消長等;可宏觀地、動態地研究考古學文化系統與考古學文化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亦可微觀地、動態地研究處于不同文化系統的相鄰考古學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東夷民族集團在我國古代文明化程度最高,所以在青蓮崗文化系統中各考古學文化表現出強烈的趨同性;根據古史傳說的研究,東夷民族文化區內有兩個文化最發達的部族———兩皞和蚩尤;根據考古學的研究,青蓮崗文化系統中也同樣有兩個文明化程度最高的考古學文化———龍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古史傳說的研究與田野考古的結論基本是一致的。社會形態的發展,即氏族向部落或部落向部族發展,首先是內部的整合和趨同;在考古學文化系統內,則表現為考古學文化與考古學文化之間的互動。其次是向外部空間的拓展,即發生史前戰爭;在考古學的層面上則表現為考古學文化系統與考古學文化系統之間的互動,即考古學文化系統擴張或“被擴張”。在“青蓮崗文化系統”即東夷民族文化區內,有北辛文化向大汶口文化與馬家浜文化向崧澤文化的發展和演進;有賈湖文化的東遷;有大汶口文化的西進和崧澤文化的西進與北擴;有良渚文化的北上與雙墩文化、侯家寨文化、龍虬莊文化、凌家灘文化、薛家崗文化的消亡;有龍山文化與良渚文化的衰亡;有王油坊龍山文化的南下和南蕩文化遺存、廣富林文化遺存的發生;還有龍山文化、良渚文化與岳石文化、馬橋文化之間的文化斷層等。可見在同一文化系統內,既有文化的擴張和文化的碰撞,也有文化的變異和文化的衰亡、消亡與乃至滅亡。
在“青蓮崗文化系統”即東夷民族文化區內,唯有海岱文化區和太湖文化區文化序列完整,唯有海岱文化區和太湖文化區的文化內涵對周邊的考古學文化區有強烈的輻射性,呈強勢文化區;而江淮東部文化區、淮河中游文化區和寧鎮山脈文化區皆呈弱勢文化區,應為亞文化區。與海岱文化區和太湖文化區相對應的民族集團應為太皞、少皞民族集團和蚩尤民族集團;海岱地區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太湖流域的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有可能反映的正是太皞、少皞部族和蚩尤部族創造的考古學文化,其中龍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成為我國新石器時代末期最發達的考古學文化。盡管東夷民族集團的文化最發達,文明化程度最高,然而我國首先誕生的是華夏民族集團的國家文明,這不能不令人深思。我國新石器時代的末期,階層分化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血緣關系的羈束,出現了地緣關系的因素,出現了王權并頻發史前戰爭,最終導致華夏國家文明的誕生。這主要表現于強勢考古學文化區域的擴大和內部強烈的同一性,表現于考古學文化的裂變、考古學文化與考古學文化之間的碰撞和弱勢考古學文化的消亡,即社會復雜化的進程。在五大文化系統即五大民族文化區中,華夏、東夷和苗蠻都與我國國家文明的起源發生過關系,而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華夏、東夷兩大民族集團之間的相互關系。考古學文化系統的確立,除了可動態地研究文化系統內部的互動之外,還可進一步動態地研究文化系統與文化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尤其是華夏民族集團與東夷民族集團之間的相互關系,猶如當年傅斯年先生提出的“夷夏東西說”,至今仍是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和華夏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課題。
在五大文化系統中,唯有青蓮崗文化系統是縱向分布的,唯有青蓮崗文化系統是縱跨江、河、淮、濟“四瀆”輳訛輧的。由于地理環境特殊性,故在東夷民族文化區內形成了既相互獨立又有聯系的兩個族群———太皞、少皞部族和蚩尤部族,而在青蓮崗文化系統中則形成了南北兩個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龍山古國”和“良渚古國”。猶如鐵木真擴張前統一蒙古各部和努爾哈赤擴張前統一女真各部一樣,華夏民族集團率先完成了文化系統內部的整合與統一,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即黃帝———夏禹;而東夷民族集團卻由于地理環境的原因形成了兩個中心,即兩皞部族與蚩尤部族———這也許是文明化程度最高的龍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未能最終完成從古國走向王國的歷程的真實原因。通過考古學文化系統的確立與研究,為探討華夏國家文明的起源即從古國———王國(方國)尋求了一條新的途徑。與“區、系、類型”理論不同的是,考古學文化系統理論不僅可用于新石器時代從古國走向王國的研究,而且還可用于夏、商、周時期從王國走向帝國的研究。我國的夏、商、周時期的文化系統可劃分為“中原(華夏)系統”和“非中原(非華夏)系統”。夏、商、周時期主要是系統內的子系統之間的碰撞、互動與整合,強勢文化不斷增強、擴展、融合、同化弱勢文化,逐漸形成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主體文化;其次是系統與系統之間的碰撞、互動與整合。“中原系統”中包含著若干“中原系統國家群”,而“非中原系統”也包含著若干“非中原系統國家群”。通過對系統內部和外部進行動態地研究,同樣可探求如何從王國走向帝國的歷程。夏、商時期是以夏、商王國為中心,以與夏、商王國有著血緣關系或地緣關系的方國群組成“中原系統方國群”,王國和方國構成“中原系統”的亞系統;而與中原王國沒有血緣關系或地緣關系的方國群組成“非中原系統方國群”,諸多方國構成“非中原系統”的亞系統。
篇(4)
首先談談對“晉文化”中的“晉”字該如何理解。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卻并非如此,而是正確理解晉文化概念的關鍵。從上述第一種觀點來看,“晉文化”中的“晉”字指晉國及三晉,而第二種觀點似乎認為“晉文化”中的“晉”是指山西(山西簡稱晉),因而將晉文化的上限追至東下馮類型。我們基本同意上述第一種觀點,認為晉文化是指兩周時期晉國及三晉的主體考古學文化,而不宜用來統稱山西境內從東下馮類型開始至秦統一期間先後存在過的若干考古學文化。
根據考古學文化的定義以及考古學文化命名的原則,考古學文化是指在一定時間、一定地域內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遺跡、遺物的總和。考古學文化通常以首次發現的地點或典型遺址來命名。毋庸置疑,以往關于考古學文化命名的原則,通常適用于史前時期的考古學文化。而對于歷史時期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則需要作特殊處理,因為此時的考古學文化已經牽涉到族屬、國別、疆域等問題。目前,學界約定俗成的是,對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先商文化、先周文化等等,由于其文化族群相對單純,人們生前聚族而居,死後聚族而葬,因此,均可視為以某族為主體所創造和使用的考古學文化。至于兩周時期分封國的考古學文化,則不宜用族屬的單一概念來命名,而不得不考慮到國別問題。值得一提的是,俞偉超先生《關于楚文化的概念問題》[3]一文對我們認識晉文化的概念有很大啟發。
關于晉文化的主創群體問題,顯然,我們不能認為晉文化是“晉族”的考古學文化。因為,歷史上并無“晉族”存在,當然也無此提法。事實上,晉國的統治者是來自關中的周人,而在晉國統治疆域內,不同的族群則共同生活于此。如除土著居民和從關中遷徙而來的周人以外,還有不少北方民族。可見,晉國社會組織的群體構成來源是復雜的。因此,只有以晉國人來界定晉文化的主創群體才是妥當的。至于三晉時期,晉文化繼續發展,其主創群體自然演變為三晉國民。
關于晉文化的時空問題,就時間而言,上起晉國始封,下至三晉滅亡。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隨著秦人勢力的不斷推進,各地晉文化被秦文化所取代的時間存在先後之差,如在侯馬地區,秦文化對晉文化的取代明顯早于三晉其它地區。因此,嚴格地講,對晉文化的下限不必一刀切,一般而言,其下限大體可以秦滅三晉為尺度,但還應注意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就地域而言,晉文化的分布范圍,隨著晉國及三晉的地域擴張而不斷變化,但并不意味著晉文化的分布范圍完全等同于晉國及三晉的政治疆域。
那么,晉國統治疆域內的考古學文化是否都是晉文化呢?非也!眾所周知,晉國由弱到強、由小變大,疆域在不斷變化、不斷擴大,晉文化的分布范圍也在相應地變化,但二者并非完全同步,或者二者不可能完全一致。一般而言,政治疆域與文化分布范圍之間,不能簡單地劃等號。西周時期,晉國乃區區小國,其地域僅限于汾澮之間的方百里之地。春秋武、獻以下,兼國多也,晉國疆域自是向南延伸至黃河北岸。但今晉東南地區當時仍為北方部族赤狄所盤踞,霍山以北也為北方部族所占據。直至春秋中期,晉滅赤狄余部;春秋晚期,趙氏苦心經營晉陽繼而滅代、智氏滅仇盂;晉文化才開始逐漸向東南、向北推進。考古學的研究表明,晉文化與北方青銅文化的分布范圍呈犬牙交錯之勢,如春秋中期以前,在晉國疆域之內,河東地區基本上為晉文化,而今晉東南、晉中乃至晉北地區則活躍著北方青銅文化。但隨著晉文化的不斷推進,有時北方青銅文化甚至處于晉文化的包圍之中。如是,晉文化的分布范圍與晉國的統治疆域之間并不能簡單地劃等號。
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晉文化與周邊考古學文化之間的互動交流,晉文化的特征也在不斷演變。也就是說,晉文化的特征有其階段性的變化。
第一階段: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如同其它分封國文化一樣,晉文化與宗周文化保持
同步發展。晉文化的面貌與宗周文化大同小異。
第二階段:春秋中期。晉文化開始孕育新的文化因素,并萌發出新的文化面貌。
第三階段: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晉文化在吸收周邊考古學文化的基礎之上,逐漸形
成自身的特色,并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同時對秦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四階段:戰國中晚期。由于秦國勢力向東擴張和秦文化的東漸,而且,三晉出于自
身的發展,各自的政治中心開始向東、向南轉移。因三晉力量分散及其它
社會原因,晉文化的發展受到遏制。至此,晉文化開始走向衰落,直至最
終被秦文化所取代。
我們認為,狹義地講,晉文化是指從晉國始封到韓、趙、魏三家分晉為止、在晉國地域范圍內、以晉國人為主體所創造和使用的考古學文化。但由于韓、趙、魏三個政治實體皆出自晉國,且三晉文化只是晉文化的自然延續和發展,其間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質變。即晉國雖亡,晉文化并未因此而終止,而是隨著三家政治勢力的不斷壯大而繼續走向繁榮。因此,根據考古學文化定義的原則,三家分晉以後所形成的三晉文化仍應納入晉文化的范疇。晉文化的年代當然應始于周初封唐而終于三晉之亡。我們認為晉文化的概念,應指從周初叔虞封唐到三晉被秦所滅這一時期內,在晉國及三晉地域范圍內,以晉國人及三晉國民為主體所創造和使用的、具有共同特征的考古遺存。
晉文化圈或晉文化系統概念的提出,也非常必要,有助于我們對兩周時期列國文化的宏觀認識。李伯謙先生在《中國青銅文化的發展階段與分區系統》[4]一文中,最早提出了東周時期周鄭晉衛、齊魯、燕、秦、楚與吳越六個文化亞區。孫華先生在其《中原青銅文化系統的幾個問題》[5]一文中,也明確提出了春秋戰國時代,中原青銅文化(即周文化)已分化為晉、秦、楚、齊、燕等幾個亞文化,并形成了既密切關聯又彼此獨立的文化區。其中,晉文化區包括晉國和由晉國分裂出的韓、趙、魏“三晉”、周王室以及鄭、衛諸小國的遺存,分布地域主要在黃河中游地區。由此看來,晉文化圈或晉文化系統不僅包括兩周時期晉國及三晉疆域之內的晉文化遺存,還包括晉國及三晉疆域之外同時期且具有與晉文化共同文化特征的考古遺存。例如,山西洪洞坊堆—永凝堡西周遺址,經研究是楊國的文化遺存[6]。由于其與天馬-曲村晉文化遺存的文化面貌幾近相似,因此,可將其納入晉文化圈或晉文化系統的范疇之內。又如,戰國中期以後的中山國遺存,其文化面貌已徹底被統領中原的晉文化所同化,鑒此,完全可將其視為晉文化圈或晉文化系統的一部分。
總之,晉文化是中原地區兩周時期一支重要的區域性考古學文化,尤其在東周時期,隨著晉文化的繁榮、壯大,晉文化對周邊考古學文化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并在中原地區形成了以晉為核心的晉文化圈(包括周鄭晉衛等國),與東齊西秦、北燕南楚、乃至吳越等考古學文化曾有過密切的文化交流,在列國文化考古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對晉文化概念的探討,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學術問題。
[1] 劉緒:《晉與晉文化的年代問題》,《文物季刊》1993年第4期。
[2] 王克林:《論晉文化的傳統性和綜合性》,《汾河灣-丁村文化與晉文化考古學術研討會文
集》,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6年。
[3] 俞偉超:《關于楚文化的概念問題》,《考古學是什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4] 李伯謙:《中國青銅文化的發展階段與分區系統》,《華夏考古》1990年第2期。後收入《中
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科學出版社,1998年。
篇(5)
根據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對“原史(Protohistory)”的定義,原史的時間段指的是一文化最早的“記錄歷史”出現的前夕(The study of a culture just before the time of its earliest recorded history)。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定義原史時代是“緊接著史前,但是又早于能以書寫文件證明的歷史(protohistory Period following prehistory but prior to the appearance of history as documented in written records)”[1]。所以,西方將“原史時代”的時間段界定于史前與歷史兩大階段的過度階段。
作為一個主要使用于考古學上的詞語,Christopher Hawkes對“原史時代”加以解釋認為,原史的概念是相對于文獻豐富的歷史,這一時期已經有一些文書記錄,但是這些記錄只是一些片斷,涉及社會非常少的方面,這些記錄可能表現于一些刻銘、硬幣等等,或是其他地區散亂的文本資料。[2] Glyn Daniel則認為“原史時期”一詞,以稱呼古代文獻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過或等于文獻材料的時期。[3]在法國《史前大辭典》一書中,認為所謂“原史”或“原始史”的涵義是,“首先具有一種方法論之意義,應用于一些為歷史文獻所不能確定的文化群體。為了研究它們,人們因而使用了此概念,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擁有文字、然而卻為同時代的其他人群所記述和提及的人群(例如征服前之高盧人,他們為希臘與拉丁作家所記述);也可以指那些通過後世的口頭傳說、記憶或者記載而保存下來其歷史的人群。在此兩種狀況下,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學資料及間接的文字記載資料兩方面。此時期在年代學體系中只具有一個很短暫的時間范圍,而且也不精確。”[4]也曾有人這么總結原史時代的特點:在最初書寫文獻還很稀少,并且很難讀懂,多數最初的記錄還沒有完全的破譯。這歷史的最初階段通常被稱之為原史時代。後世的學者也會對這個時代的歷史不斷的進行文書上的補充。這些文獻,在結合考古資料之後,也會成為值得重視的材料。好比說一個傳說中的國王的名字被發現在刻銘上,關于這個國王的記載的可靠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5]
由字面上來看,“proto-”指的是一件事物的較原始的狀態,是一種“祖”、“祖型”的概念。例如英語里的“Proto Austronesian”(原南島語)指的是南島語的一種祖型,Proto Austronesian表示了其與Austronesian 的差別,也表示了Austronesian存在的最初始狀態。同樣的,我們將先商稱為“Proto Shang”、將先周稱為“Proto Zhou”,所表示的都是商、周王朝的先族,周人或是商人在建立王朝之前已經存在,所以我們不會將先商稱為“pre-Shang”,也不會將先周稱為“pre-Zhou”。因此,在“protohistory”這個階段里,史學開始萌芽,一些記錄開始以各種形式出現,雖有文書記錄,但是仍不足以讓我們據之復原歷史,這一階段有別于史前,也有別于歷史時期,是史前向歷史時期發展的一個過度階段。在對這一階段進行研究時,也需要不同于史前及歷史時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將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文字學、器物學等等學科綜合起來的一種研究。
雖然,作為方法論的“原史”的概念還沒有被更深入的定義、討論,對于其意涵還有不太相同的認識,但是“原史時代”在西方已經是受到普遍承認的了。綜上,我們可以根據西方學者對“原史時代”的定義總結出幾條基本原則:1.原史時代是介于史前時代與歷史時代的;2.原史時代研究的對象應是一些為歷史文獻所不能確定或認識不夠充分的文化群體;3. 由于原史時代當代的文獻稀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過或等于文獻材料;4.原史時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將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文字學、器物學等多種學科綜合起來。
以下,我們可以根據西方學者對原史時代的定義來檢驗中國原史時代是否存在。
對“中國原史時代”的界定
過去我們一般將古史分為史前、歷史兩大階段或是史前、傳說、信史三大階段。這兩種分類都是由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材料出發的。在考古學引入中國之後,史料的范圍已經由文字材料擴大到包括文獻(當時的、追述的)、文物、考古材料、古文字(而古文字的主要獲取方法是考古學)。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對中國先秦史的研究(這里指的是文獻記載中的夏商周階段,下限是秦始皇帝統一中國(221B.C.))。張光直先生即曾說過,“自從二十世紀初期以來,考古學的發現越積越多,越多便出現好些以前從來沒有看過、聽過、想過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問題。用考古學建立的歷史因此更得隨時改變。考古學還發掘出新的文字材料來,加強了古文字學這一門學問。研究商周三代歷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學;近百年來使用古文字學的結果,是知道了傳統的三代古史有許多處被古文字學證實了,但還有更多處被古文字全部改觀了。”[6]
戰國以前同時期的傳世文獻材料非常少,即使是當時流傳下來的,如尚書、周易、詩經等等的文獻材料里,也有許多後人補作或是經傳抄而改變的內容。後世對這一時代追述的著作多作于東周及漢代,這其中除了保留部分夏至西周的真實情況外,大多是為了時代需要加以改編、附會而成。所以,我們在面對傳世文獻以及通過這些文獻而認識的古史時,總是要持一些保留的態度。即使是現在基本被考古材料印證的《史記.周本記》,其所能為我們提供的,也只是當時歷史發展的一個框架,還須要我們透過其他手段進行復原。
另一方面,中國的人文史學傳統肇始于西周王室覆滅「王官之學降于民,知識分子才脫離王室的束縛,逐漸由過去的“巫”史中走出來。晉《乘》、楚《檮杌》、魯史《春秋》,都成于這個時期。今日我們讀到的《左氏春秋》,開創編年記事的體例,是中國歷史學發展成熟的標志。至此,可供後世學者研究的確實的文獻史料開始豐富,文獻材料為學者提供了全方位更為豐富的論證材料,考古學成果成為歷史文獻的一種參照或是補充,而非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因素,如此才算是進入真正的「歷史階段。
王樹民先生指出,現在有些人對于古代史學和史料不加分別,以為根據古代的直接史料,便可以說明當時的史學了,正與把傳說當作史實同樣是不正確的。如甲骨文是殷代遺物,史料價值很高,在巫史不分的情況下,也可能為史官所作,但原為占卜之用,不是歷史記載。鐘鼎文多為周代之物,記載了許多重要的史實,但原為紀念性質,也不是歷史記載。[7]所以,不論是由史料或是史學史的角度來看,三代時期的研究是有其獨特性的,不同于史前及歷史時期的研究。
由現存的文獻材料來檢視中國(中原地區)先秦史,春秋以前(甚至是戰國以前)的傳世文獻里沒有比較全面的史學著作,所見可靠的文獻材料也多經後人修改。考古發現了大量的文字資料,但是這些文字表現的是歷法、卜筮、紀念,或是簡單記事文字,只表現了商周王朝片段的歷史,雖然已經極具歷史性,但仍不足以充分表現當時歷史的方方面面。雖然已經有了史官,但是當時的史官是為上層及祭祀占卜服務,其性質仍不同于後世的史職。“史”的概念還在萌芽的階段,真正為記錄歷史的歷史記錄還沒出現。這些都與西方對原史時代的定義相符,所以,我們可以將中國的商、西周時期(甚至是春秋時期)作為中國的原史時代。李學勤先生即根據Glyn Daniel對原史時代的定義認為,東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經脫離了這種“原史時期”而跨入真正意義的“歷史時期”了[8]。此外,作為歷史文獻所不能確定或認識不夠充分的(但是仍有相當的文獻材料及考古線索)夏、先商、先周也應屬於中國的原史時代重要的一部分。這牽涉的不僅是時間的概念,更是一種族及考古學文化發展的概念。因而在尋找夏的根源上,我們更應該將著眼點放在晚期龍山文化。至於繁複龐大的傳說記載,由於其涉及的時間范圍太長,似乎不宜將所有的傳說都歸入原史時代范圍;此外,多數傳說內容也很難與考古材料相結合,即使是距離夏代較近的“三皇五帝”傳說也很難落實在考古材料上,所以這里不把過去所謂的“傳說時代”等同于原史時代,其所涉及的是另一種概念及材料。
中國的原史時代,及其與傳統中國上古史的區別在于,傳統史學由文獻出發,以政治時間作為歷史分期的標準,所以一般將秦以前劃為上古史的范圍。在過去所認為無文字的史前時代以及文字發明之後的歷史時代之間加入一個“原史時代”所表現的是歷史學的一種初興狀態,以及我們對這一階段的歷史進行研究時所面對的史料的多樣性(與史前及文獻發達時期相較)。這里所指稱的“中國原史時代”是,一時代的歷史由傳說或是不充分的文獻記述,必須通過考古材料對這些傳說或文獻加以檢驗確定其正確性,并需要由大量的考古資料建立、補充文獻所缺乏的各種對當時的研究材料(即使考古材料所表現的也只是當時社會的極小的一個部分)。這一階段的研究需要由考古學、古文字學、歷史學等等一起建構出當時的歷史、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況。而這種對“原史時代”的研究,也只有在今日考古學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之下才有可能展開。
所以,原史時代概念的提出不論是對歷史學研究或是考古學研究都是有所幫助的。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原史時代的研究對象并不應該被限定在整個現代中國領土的范圍,而是著眼于族群之上,被介定為以中原華夏民族的原史時代為中心,其范圍是在中原的古文字材料、傳世文獻、考古學文化的基礎上,向外輻射至與之相關的各個地區、族群、文化(當然,如果該文化也有文字材料,也需被視為認定其族屬、文化以及認定其與中原及其他族群、文化的重要材料),希望能將中國原史時代表現為一個各種活動、族群聯系在一起的有機體。而對于現代中國境內曾經有的各個族群、文化的原史時代的研究,則應該將其分別命名(如:匈奴原史時代、女真原史時代等等),成為以其為主體的原史時代,以求與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原史時代區隔開來。
所以,中國的原史時代是:1.時間段在文獻所記載的夏至西周晚期(甚至春秋中期);2.涉及的對象是以中原為中心,兼及在各種方面與原史時代的中原有聯繫的各種族群(如羌、鬼方、蜀、淮夷等)、文化;3.主要的研究材料為當代及後世文獻,以及原史時代的古文字、考古遺跡遺物、傳世文物等等;4.中國原史時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將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文字學、器物學等多種學科綜合起來。
中國原史考古
中國原史時代的定義已如上述,而作為中國原史研究最重要的一環的中國原史考古,又有其不同於史前或歷史考古的特殊性。
首先是文獻材料對考古產生的不同影響。史前考古沒有當代的文獻材料,後世文獻材料對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話與傳說。神話為非客觀的記述,本來無法作為有效的根據。傳說的核心部分固然為古代實有,與後人因想象而虛構的不同,但是傳說有較大的不穩定性,不僅時間、地點、人物易發生錯亂,更容易混入神話成分[9]。因此史前考古與文獻的相關性很低。而歷史時期擁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獻材料,考古雖然仍能對文獻有所增補,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獻材料的基礎上進行,以文獻材料為主要依歸。原史考古與文獻之間則是一種互補的關系,文獻為考古提供線索,而考古則檢驗文獻的正確性,并在文獻所提供的框架之上進行更深一層的復原。原史考古與歷史時期考古的不同在于,考古學材料在許多模糊的歷史問題的研究上具有的決定性的影響力。
原史考古所涉及的對象是以中原原史為中心,輻及與之有關的各個族群文化。中原以外的族群沒有文字,雖然其族屬的確認主要是依據古文字、文獻材料,但是在其考古學文化被認識的基礎之上,進行文化因素分析,我們不但可以加強認識中原文化與相關族群之間的關系,更可以建構出以某一族群為中心的原史,理清族群之間的復雜關系。
而中原地區的原史考古在考古學以及古文字、文獻記載三種材料并重的情下,除了研究與考古學相關的各種課題外,還可以在文字資料的幫助下,建立中國原史的年表,并結合古文字、文獻記載的時間、人物、事件、地點,復原出一種將考古學文化與史實相結合的中國原史時代。
參考文獻
[1] 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1998。
[2] Hawkes, Christopher"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155-168,1954.
[3] Daniel, Glyn,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1.(此處轉引自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
[4] Dictionnaire de la Prehistoire,1988,Directeur de la publication Andre Leroi-Gourham, Pres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Paris.(此處轉引自劉文鎖:《論史前、原史及歷史時期的概念》,《華夏考古》1998年3期,93頁)。
[5] 見home.swipnet.se/~w-63448/mespro.htm。
[6] 張光直:《對中國先秦史新結構的一個建議》,《中國考古學論文集》,三聯書店,1999年9月。
篇(6)
然而,雖然自20世紀80年代起即對音樂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架構予以討論(見下文)但對該領域研究理論的探討卻相當缺乏。這是不正常的,由于理論是研究方法的基礎,所以需要高度關注。這一問題,直到最近才受到學科發展史研究的較多重視。在本文中,我想討論音樂考古學方法論體系的一些基本原則,包括研究的一般范式,并附加一些與人類學學科有關的理論思考。在我看來,民族音樂學、民族考古學和實驗考古學與這些理論思考的關系更為密切,它們將有助于構成方法/理論的背景,并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參考。
音樂考古學研究的方法論架構
在所有已提出的音樂考古學研究范式中,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受到推崇(14)。大家均贊同,音樂考古學由一系列多學科的方法或分析模式所組成,其具體方法則由研究主題所依賴的資料所構成。如前所述,這些研究資料具有多樣性,它包括與音樂相關的發現和涉及音樂的歷史記載,有時甚至是依然存活的音樂傳統。由人類過去的遺物可知,這些資料在類型和內容方面均存在個體差異。重要的是,為獲得實證性的結果,所有資料均應考慮以互補的方式加以比較。換句話說,這些資料均應予以同等對待。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種方法的有效性已經得到許多研究的證明。分析方法的多樣性還表明,最佳的研究結果乃由不同領域的專家組成的研究團隊所獲得。
已有的研究范式顯示,音樂考古學的具體研究方法會有所不同,這主要基于應用的資料和分析的模式。在研究的總體目標上,可從音樂知識(包括“文化知識”、“樂器學知識”、“律學知識”等等)(15)到文化/自然的聲音(16),也可從音樂表演(17)到音樂文化(18)。根據音樂考古學研究的一般范式(見下文),以及上述音樂考古學的定義,我將研究的總體目標界定為過去的音樂行為和聲音。
研究方法的主要差異,體現在音樂考古學家和民族音樂學家對過去的音樂所持有的不同觀點,后者已經在20世紀60年代由Merriam予以闡述(19),隨之由Blacking(20)、Nettl(21)和Mendívil(22)等人做過進一步探討。雖然大多數音樂考古學家傾向于研究過去的音樂行為和聲音,包括與依然存活的音樂文化做比較,但后者僅作為一種輔助的研究方法。民族音樂學家雖然對考古和歷史問題感興趣,但更傾向于研究現狀并探尋其中尚存的過去的蹤跡,從而將歷史科學作為輔助的研究方法。兩者的出發點都是有價值的,且并不互相排斥,但對其交互關系的探究目前則所見不多(見下文)。
如果將現存的所有資料和重要的分析模式加以整合,即可形成一種普遍適用的音樂考古學研究的方法范式。這可用一般的范式來表示(見圖),并可作為世界范圍內個體研究的結構框架。這個范式由兩個同心圓圍繞總體目標構成,其中所有的部分均可作為獨立研究的課題。外圈聯結著四組音樂考古材料(發聲器、音樂圖像、音樂文獻資料以及存活著的音樂傳統),內圈是一些主要的學科,分析模式通常即從中產生(音響學、樂器學、考古學、音樂圖像學、民族音樂學、民族歷史學和文獻學)。
音樂文獻資料 文獻學 音響學 發聲器 樂器學 民族歷史學 過去的音樂行為和聲音 考古學 音樂圖像 存活的音樂傳統 民族音樂學 音樂圖像學
J52Y401.JPG
圖 音樂考古學研究的一般范式
由于研究材料的情況各自不同,因此音樂考古學研究的結果也具有不同的意義,重要的是每種方法要針對不同的個案研究。最為全面的研究結果只能在每項資料具有足夠的信息時才能獲得(23),這意味著音樂考古學研究的成功更多依賴的是特殊的原始資料及其互補性。材料經常是殘缺不全的,但也要作為研究的課題,因此以一種或幾種方法去處理它們通常是不夠用的。音樂傳統的年代越久遠,研究就會變得越困難;文獻資料越豐富,探索其原貌的基礎就會越好(24)。因此,音樂考古學研究和闡釋的可能性確實是十分有限的,在涉及到非常遙遠的、僅遺留有極少物質資料的音樂文化時尤其如此。
音樂考古學研究與民族音樂學
比較音樂學作為民族音樂學的前身,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就已出現。十分顯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屬于歷史科學(25)。除了方法的不同以及后來受到嚴厲批評的假設和臆斷之外,它與音樂考古學具有一些共同的研究目標。在研究的課題領域中,比較音樂學家重視音樂的起源,他們認為這在當今所謂的原始文化中可以進行考察,并可從單線進化朝著“文明的”方向來分析音階構成和樂調體系(26)。20世紀60年代早期,作為新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歷史問題包含其中,民族音樂學被視為音樂人類學(Alan Merriam),重點研究音樂在社會中所產生的作用。在音樂與文化史一章中,Merriam指出,要通過音樂和樂器研究重建文化史(27),這是民族音樂學研究的組成部分。對于歷史科學如考古學和民族歷史學的研究目標來說,這樣的研究方法也是有價值的。
Merriam之后的學者,例如Blacking和其他人,都提出特殊的音樂和社會形態是特定文化認知過程的產物,在音樂的行為方式和社會組織之間具有牢固的聯系。根據這種理解,音樂文化依賴于人類組織和聲音模式,聲音的生成是有組織的相互作用的結果(28)。Blacking認為,民族音樂學的目標是研究文化結構及其音樂之間的關系,并認為文化與人為組織起來的聲音是相互依存的。近來推斷,對音樂結構的社會文化關聯性的探索并未取得太多的成功(29)。然而,不能否認研究文化樣式與音樂之間關系的重要性,因為音樂從未與它的創造者的個人經驗相脫離,音樂的創造者深入地參與到廣闊的文化和歷史進程之中(30)。
當探索民族音樂學對音樂考古學的適用性時(31),兩個學科間的一項重要結構差異便顯現出來。音樂考古學最明顯的矛盾是,截止近代(以1877年留聲機的發明為轉折點),過去的所有音樂都消失了。然而,音響考古學研究并非不可能,一些研究表明,這個矛盾至少能部分得以解決。不同的文化產生不同的樂譜形式,它們很難被解讀,但至少一部分能被破譯(多數例子與美索不達米亞、古希臘和古羅馬有關)。文獻資料也為我們提供了儀式歌曲和圣詠的文本;在古文字和其他歷史文獻中,表演實踐、演奏技術乃至音響風格都是相互關聯的(從不同程度的主位與客位角度觀察)。現存的描述顯示了樂器的種類和特有的演奏姿態(遵循著不同的藝術習俗和規則),樂器的發現至少能幫助我們重建創作音樂的構成元素(例如基音頻率、和聲、音色和音程等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擁有大量的音樂考古材料,結果仍是有限的,因為在大多情況下,過去的音樂在節奏和旋律結構方面均超出了科學研究的范圍(見下節)。
另一方面,音樂表演和與其產生相互作用的社會文化語境,在民族音樂學和音樂考古學中都是熟知的研究課題。事實上,有時會有豐富的研究材料。從有關音樂發現的考古學背景,到大量的圖像和文獻記載,使我們更多地了解過去的音樂文化。在這種情形下,作為研究課題,由于資料的完整性和零散性各異,會導致研究方法的不盡一致,但從研究目標來看,音樂考古學和民族音樂學是一致的。就音樂考古學而言,在將過去音樂行為的社會文化面貌呈現在面前的同時,過去的聲音只有在某些方面能夠得到復原。
民族考古學和實驗考古學
20世紀60年代早期,傳統考古學受到所謂新考古學的挑戰,新考古學所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傳統考古學將出土文物的描述作為主要的研究目標。Binford和其他人轉向人類的行為和文化模式,將物質文化的解釋作為一種考察手段,而不是局限于物質的形態范圍(32)。從考古人類學(Lewis Binford)引發的問題,關注考古學人工制品的生產技術以及它們的特定社會文化功能。即便沒有進行過充分的討論,但這種方法對音樂考古學研究的適用性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得到公認(33)。依我來看,新考古學有兩種方法對于古代聲音和音樂行為的研究至關重要,即:民族考古學和實驗考古學。
民族考古學
如果將考古資料與民族志資料的比較作為有價值的研究工具,那么民族考古學則是通過對當今民族事象的研究,來了解過去的文化樣式。Hodder定義了兩種不同的研究類型:考古學與民族志器物如各種工具的形制比較(關系類比);過去與當今技術處理相似性的比較(形式類比)(34)。在民族考古學中常用的方法是直接歷史研究法,當具備歷史和文化的連續性條件時,直接比較便成為可能,而一般比較法則無需這樣的鏈接即可構建其相似性(35)。當對不同文化資料的解釋做多樣性考察時(36),應用民族志類比方法來理解考古資料的主觀風險便可降低。
民族志類比方法對音樂考古發現的解釋相當重要,這說明它與民族音樂學研究關系密切。確實,民族考古學的方法可以作為音樂考古學與民族音樂學之間的橋梁,但在探索它們的交叉性方面,目前所獲經驗并不多。直接歷史研究法在眾多個案研究中得以應用,如西班牙統治前的美洲音樂文化與當今美洲土著音樂傳統的比較(37)。但間接的比較也是有用的,尤其是狩獵采集社會與史前音樂文化的比較(38)。
盡管音樂考古學的解釋有其優長,但與后世時間跨度較大的文化做比較研究仍然面臨相當大的困難。對音樂傳統做時間跨度和歷史深度的考察,在音樂考古學和民族音樂學中是最具挑戰性的分析研究。更為復雜的問題是,我們對過去的認識常常是靜態的,音樂考古學的解釋反映出這種問題,在原始材料不足時尤其如此(39)。少量樂器或圖像的發現,并不一定代表一種特定的音樂文化,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由于文化內部和跨文化之間長久的交互作用,文化本身也會發生變化。不過,即使像樂器那樣的器具,在很長的時間 內可能會保留它們的形態,且很可能被吸收和植入新的環境之中,因此會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功能和意義。一種特定的樂器形制可以傳留數千年時間,如東亞的琴箏類樂器和東南亞的弓形豎琴。但用這些樂器演奏的特定音樂以及特定的表演背景和含義,均可能發生相當程度的變化。在追索音樂傳統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中,對文獻和圖像資料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關注過去音樂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意義方面尤其如此。
實驗考古學
實驗考古學研究旨在運用復原和重建古代生活樣式的手段,并通過與過去的比較,來從事考古學研究(40)。與民族考古學方法相比,它基本上不是詮釋他者(如依然存活的原住民文化);相反,考古學家轉而成為行為人,通過他或她自己的切身體驗,來比較實驗的價值。在被稱為模擬實驗的方法中,研究者發現了一系列與過去的經驗類似的技術變革。常見的研究課題是,使用原始工具和技術對考古發掘物進行實驗性的復制。對古器物使用方式的重建即其顯例,如舊石器時代的燧石工具,能夠發出與勞動相關的特殊而有節奏的聲音。一些燧石擁有動聽的石制板體樂器的音響,即使它們不具備音樂功能,但在過去至少應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顯然,實驗考古學的方法在音樂考古學研究中是適用的。有關音樂考古發現的樂器學和聲學研究已經超過一個世紀,如今在音樂考古學中更是必不可缺。有兩種分析方法最為常見:第一,復制品和“仿真模型”的實驗性制造;第二,復制品的實驗性演奏,或如果可能的話,演奏發聲器原器。這兩種方法是密切相關的,因為發聲器的實驗性復原,往往是實驗性演奏的前提。實驗音樂考古學的研究,通常是與樂器制造商和音樂家共同合作來實現的。
實驗制作過程提供了精確的樂器學信息,其所需前提條件往往是對制作材料的分析,包括對材料的產地、處理以及工藝的考慮,常使用直接目測觀察和考古測量的方法(光譜學、X光照像技術、材料研究,等等)。這些分析還提供了制造的特殊信息和古代加工材料的知識,以及制造完成后樂器的操作乃至演奏痕跡。此外,也能夠了解樂器獨特的聲學原理。實驗方法還可通過仿真模型得以實現,即根據特定的研究對象,不必使用原材料來復制樂器(如氣鳴樂器)。
對古樂器或其復制品的試奏,能夠考察樂器的演奏技巧,并能顯示特定樂器的音響性能(若幾種樂器發現于同一考古環境當中,或圖像中描繪的是一組樂器,就要考慮它是獨奏或合奏所用)。發聲器在保存狀況較好且可演奏的條件下(如陶響器、陶笛、螺號、陶號、石制板體樂器,等等)可以用作實驗研究,而樂器殘品以及不宜演奏的樂器(如古代弦樂器)則需以復制品來進行實驗研究。與此相關的是音響空間和音響性能的研究,其中聲學模化軟件和3D應用程序也被應用。
如上所述,演奏姿勢和技巧以及出土樂器的聲音特性,都能通過實驗來加以重建和檢測。當涉及氣鳴樂器(例如帶指孔的骨笛、排簫或螺號)以及成套的體鳴樂器(如編磬和編鐘)時,重建其音列也是可能的。然而,實驗性的演奏在音樂考古學中屬于最困難的研究方式,因為我們往往并不掌握過去音樂的特殊結構及其重要信息。再者,雖然文獻與圖像資料的有關信息有一定價值,但即使在演奏姿勢方面,從特定發聲器的人體生理學角度看,也會限制其演奏技巧和聲學性能,因此其真實性存在較大的差距。以笛子為例,實驗性演奏的結果不能視為特定音階或調式的證據,因為不是所有的指孔可以均等地使用,并且還可通過呼吸控制技術以及指孔的部分閉合等來改變音響(41)。例如,如果只是給出樂器尺八(同上),人們可能完全不曉得日本尺八音樂,這同樣也適用于舊石器時代由禽鳥骨和猛犸象牙制造的笛子,這只不過是采用了最早的考古學案例而已。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可以在復制品上奏出與公元前33000年樂器同樣優美的旋律。事實上,正如Nettl用一些顯著的例子所論證的那樣(42),重建古代音階體系以及其它音樂構成要素,仍然帶有很大的推測成份。只要有相當數量的考古材料,即可通過定量分析,來幫助獲得驗證的結果。然而,在大多情況下,發聲器的聲學研究并不能揭示出過去音樂的旋律和節奏方面的足夠信息。在聲音的再現技術產生之前,過去音樂的音響全都消失殆盡。
以往何時、如何以及為什么制造樂器并用來發音的問題,較之過去音樂的構成問題,在音樂考古學中會起到更大的作用。前述科學研究中的局限,屬于科學與藝術結合的臆測或即興發揮。顯然,這樣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研究者或音樂家的想象,它相當于對音樂史的藝術化闡釋,只是簡單反映了目前我們對過去音樂的看法。
本文譯自Arnd Adje Both. "Music Archaeology: Some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009(41): 1-11.
收稿日期:2013-10-12
注釋:
①我基本采用兩個早期的釋義:“通過古物遺存研究作為文化的音樂”(Olsen 1990: 175),“古代聲音和音樂行為的考古學”(Lawson 2004: 61)。
②Blacking, John. "Ethnomusicology and Prehistoric Music Making." In Hickmann, Ellen, and David W. Hughes. Ed.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usic Cultures: 3rd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330-331. Bonn: Verlag für 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 1988.
③Both, Arnd Adje. "Aztec Music Culture." In "Music Archaeology: Mesoamerica," ed. special issue, The World of Music 2007(49)/2: 91-104.
④原文為:archaeology of sound,譯者注。
⑤原文為:sound archaeology,譯者注。
⑥原文為:music archaeology,譯者注。
⑦原文為:archaeomusicology,譯者注。
⑧Hickmann, Ellen. Aims, Problems and Terminology: Current Research in European Archaeomusicology. Ed. Graeme Lawson. Cambridge Music-Archaeological Reports, 6, Cambridge, 1983; Vendrix, Philippe. "Archéo-musicologie ou musico-archéologie." In Otte, Marcel. Ed. Sons originelles: Préhistoire de la musique. 7-10. Liège: Université de Liège, 1994.
⑨Megaw, J. V. S. "Problems and Non-Problems in Palaeo-Organolo gy: A Musical Miscellany." In Studies in Ancient Europe: Essays Presented to Stuart Piggott, ed. J. M. Coles and D. D. A. Simpson, 333-58, Leicester, 1968.
篇(7)
在關于美術考古學科關系的認識中,目前學者較多涉及的是與考古學、美術學、社會學、歷史學、圖像學等學科的關系,這其中涉及學科的本源、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學科的意義等諸多方面,涉及面不可謂不廣、不可謂不具體。遺憾的是,在這些關系的討論中,基本上沒有考慮到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之間的特殊關系。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不僅在研究對象上有相同之處,而且在研究資料的獲取上也有相同之處;同時,在接受的影響上也有相同之處。因此,我們提出美術考古的敘事特征和與宗教美術的學科關系作為理論深入的探討視角。
一、與研究對象相關的敘事邏輯
這是一個關于敘事邏輯的學科定位問題。我們認為,美術考古如果作為分支學科看待,那么,從敘事邏輯角度看,它不是考古學的分支學科而應當是美術學的二級學科。
1.美術考古是將研究對象作為美術史現象來描述的。“以田野考古發掘和調查所獲得的美術遺跡和遺物”[1](P5)是美術考古的研究對象,在美術考古的研究過程中,這些美術遺跡和遺物轉化為美術發展史上的敘事遺存,圍繞美術遺跡和遺物展開的研究是關于構圖、造型、色彩和主題、風格、藝術進步等美術學科范疇的研究。
2.考古學的學科方法并不支持美術考古的研究趨勢。目前學術界中,不論是將美術考古歸之于考古學學科還是將美術考古歸之于美術學學科,學者們都希望美術考古擁有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更加廣泛的研究領域,但是,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并不支持美術考古這種具有擴張性的發展要求。
3.美術考古的研究成果極大地提高了美術史研究的學術影響。這一點最好理解,美術考古將美術史的研究進入到石窟藝術、墓葬藝術、巖畫藝術等考古遺存的領域,美術史上的許多空白被填補,許多文化遺存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美術史在作出貢獻的同時也提高了自己的學術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
因此,我們認為美術考古不應作為考古學的分支學科,而應當作為美術學的分支學科。通過對美術考古定義的討論,我們提出一個求教大方的表述:美術考古是一門以田野考古發掘和調查所獲得的美術遺跡和遺物為研究對象、在美術史層面上展開研究活動的美術學分支學科。
二、與宗教美術相關的敘事特征
這是一個從敘事特征角度討論學科關系的問題。
1.從邏輯關系上對敘事特征的討論。
從形式邏輯的角度看,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在概念上存在的關系是交叉關系。從敘事特征看,美術考古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因為原因而成為考古對象的,如墓葬藝術作品、石窟藝術作品等;第二部分是因為社會動亂、自然災害等原因而成為考古對象的,如古建筑遺址、被掩埋的藝術作品等。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深入于藝術活動之中,留下了豐富的美術作品。
2.關于美術作品埋葬方式的敘事認識。
在通過考古手段而獲得的美術作品中,其埋葬方式毫無疑問是美術作品完成敘事的重要內容,可是這一點目前沒有深入的研究。在目前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的研究論文中,研究對象的確定常常是側重于從作品的發現角度來認識的,即考古學的角度。
3.關于敘事意義的理論認識。
敘事作品是一個動態的意義生成系統。[2-6]通過學科邏輯關系的認識,我們可以從邏輯角度認識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之間所存在的共同性;通過作品埋葬角度的認識,我們可以從作品存在的角度認識兩學科之間存在的差異性。同時,兩學科的結合思考還可以在操作層面上提供可以深入的理論意義。這個意義,就是在認識美術考古和宗教美術學科特征的基礎上突出兩者結合思考后的指導意義,即強調宗教美術作品和與之相關的美術考古作品所具有的敘事意義。
3.1敘事主題的單一性(或集中性)。
在宗教美術作品和與之相關的美術考古作品中,敘事的結構往往都顯得非常宏大,幾乎所有的構圖都試圖包括天上和地下、凡間和世外,這是指導的必然結果。
3.2情節的真實性。
宗教美術是描寫另一個世界的,與現實世界對照,它是不真實的。但是,宗教美術作品能夠存在的理由卻是來自于宗教經驗,即這些作品的內容是真實的。這樣的真實在作品中得到了普遍支持,即作品表現了情節的真實性。情節的真實性當然是來自于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宗教經驗對這樣的真實是支持的態度。宗教美術作品的構圖體現著這樣的“真實性”。
3.3物象的符號化。
在宗教美術作品中,物象符號化的手法無處不在,每一個物象都拒絕隨意的理解,必須從某一個已經存在的特定的概念來入手,從而得到物象的象征意義。
綜上所述,就學科性質的認識而言,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之間存在的關系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命題,這兩門學科的共性可以使我們在認識學科性質上尋找到諸如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邏輯關系,特別是在接受的影響上所存在的相同敘事結構,使我們更容易理解美術考古和宗教美術的學科定位。
參考文獻:
[1]楊泓.美術考古半世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2]阮榮春,主編.絲綢之路與石窟藝術[M].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2004.
[3]朱滸.全國首屆藝術考古學理論研討會會議綜述[J].中國美術研究,2007,(3).
篇(8)
與美術考古學關系最密切的兩個學科是考古學和美術史學,這里有必要通過比較,明晰三者研究對象的知識邊界(參見下面比較表)。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通過考古調查和發掘獲得的實物資料[6],美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其中的一部分,即“實物資料”中的“美術品”部分;另外,傳世品也是美術考古學重要研究對象[7](P17),而它只是考古學研究中的平行參考資料。根據美術品的特征,下列兩類實物排除在美術考古學研究對象之外:一是與古代人類活動有關但“未經人類加工的自然物”,如動物化石、植物孢粉等;二是僅具有實用功能,難以引起人審美感受的人工創造物,如灰坑、窖藏、礦井、水渠、壕溝等遺跡。美術史的研究對象包括建筑、雕塑、繪畫、工藝美術、書法、篆刻等美術種類[1](P526)。它與美術考古的關系尤為密切,因為二者的研究對象和資料基本相同,只是側重點和研究方法各異。二者的差別在于美術史是在縱向的時間序列中研究審美關系的發展演變,它的時間范圍可以從古代一直延續到當代;而美術考古則要在特定的“考古學文化”這樣橫向的共生關系中,探討“奠定這種審美意識的經濟生產、社會制度、民族文化和受這些制約的一系列的特定環境下的審美創作活動”[8](P139),它只限于古代。該學科旨在通過美術遺跡和遺物的視角,深入研究隱藏在那些“物”背后的“人類觀念”。例如,在繪畫方面,美術史主要研究卷軸畫,著重于表現手法、風格流派、畫家生平等等,以把握時代的審美風尚和規律;而美術考古主要研究巖畫、建筑壁畫和墓室壁畫。它要盡可能參考同一時期所有的考古資料、文獻記載,以求在全面復原歷史的情況下來微觀某一美術作品,不但是時代的審美意識(確切地說,這方面要借鑒美術史的研究成果),而且是支撐這一審美意識的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社會的方方面面,最后力求達到對該時期人類文化觀念的認知和體察。再如,美術考古的研究對象多是雕塑藝術品和工藝美術品,這些作品因中國“重道不重器”的思想根源,很少有明確的創作者姓名留下,因此它們代表的是一種群體作品,具有社會性特征;而美術史則著重個案研究,如對藝術家或者藝術流派的關注,因此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9](P232)。歸根結蒂,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是服務于該學科的研究目的的。考古學旨在論證存在于古代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規律;美術史在于研究美術的歷史發展及其規律;美術考古則是通過古代遺留下來的美術品了解人類的文化史和觀念史。
從特征中把握研究對象
中國的厚葬之風體現了古人“視死如生”的觀念,墓室是死者在另一個世界生活的縮影,他(她)既要繼續享受人間的榮華富貴,又渴望在仙境中獲得再生;隆重嚴肅的墓葬儀式和祖先祭祀活動,正體現了活人與死人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生人往往借著死人的余蔭,就是借著祖宗的功德或顯赫的威名來在社會上立足。而死人又借著生人的功業而聲名得以顯耀,已死者和仍活著的人雖然死生之路斷,幽明之路隔,但兩者之間的關系,仍然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10](P180)正因為此,墓葬的形制規模、布局裝飾和明器的使用,無不體現了當時人們的精細心思。它們凝結了高度的藝術性,但當初人們在建造和制作時,卻抱有明顯的功利目的,這里藝術之美是服務于功利之用的。這樣以來,中國的墓葬中包含了大量的社會文化信息,漢代墓葬出土的畫像石磚就被喻為漢代社會的百科全書,美術考古學正要透過藝術來解碼社會。
篇(9)
中圖分類號:K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0-0000-01
《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學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王仁湘先生是畢業于四川大學考古學專業的知名學者,對其著作進行研讀,對我們的學習、研究具有極強的指示作用。王仁湘先生在史前考古研究領域有極高的造詣,對仰韶文化的研究更是有其獨到之處。故選擇論文集中的《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半坡和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三篇文章進行精讀。三篇文章分別從考古學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學文化之間的關系及考古學文化命名三個問題展開。這三個問題,無論是在考古學理論研究還是在田野考古實踐中都是時常碰到的核心問題。本文分別從文章的主要內容、觀點等方面做介紹。
一、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命名―《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與程序問題》
《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與程序問題》一文曾發表于《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該文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論述,系統的介紹了學界對考古學文化命名這一問題所展開的討論。文章第一部分,詳細介紹夏鼐先生對考古學文化命名這一問題做出指導意見的具體論述及相關背景。文章第二部分,列舉了各家看法,并提出獨到見解,如:指出應在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中應強調陶器群的量化問題。文章第三部分,介紹各家對考古學文化“三要素” 的觀點,同時指出考古學文化“三要素”中,最核心的是“特征”。文章第四部分,是本文創新之處,提出考古學文化命名的確認要通過國家級的學術機構(如中國考古學會),并詳細闡述了“命名確認”的程序。
二、區系類型問題的研究―《半坡與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
《半坡與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一文曾發表于《文物》2003年第4期。該文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論述。文章主要圍繞半坡與廟底溝類型確立及關系問題展開論述,文章第一部分,介紹了1959年,類型劃分問題的提出,及半坡早于廟底溝、后者早于前者、兩者同時并存這三種說法的提出。文章第二部分,重點介紹了廟底溝早于半坡這一最初的簡單論證,安志敏、馬承源學者的觀點。文章第三部分,又介紹了一個完全相反觀點的提出即半坡是老者,1962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一個簡要的地層關系報告,它對兩類型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文章第四部分,又是一個新論證,即同時并存(犬牙交錯的兩個類型)。
三、對考古學文化淵源的解讀―《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
《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一文曾發表于《考古》2003年第6期,從文章題目可知該文重點探討仰韶文化“淵源”,即仰韶文化的“源頭”問題。該文主要從五個方面展開敘述。第一部分,80年代確定仰韶文化源頭的歷程。安特生將河南、甘肅發現的彩陶,同中亞土庫曼的安諾文化彩陶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中國文化西來說”。梁思永先生發現了安陽后崗“三疊層”,尹達先后多次撰文否定了“西來說”、“六期說”。但仰韶文化的來源問題并未得到解決。第二部分,從多源觀到一源觀。“分源”問題的提出,是一個重大突破。嚴文明、張忠培先生發表了相似的“分源”觀點,嚴文明先生建議將仰韶文化“一分為二”,將后崗―大司空和半坡―廟底溝作為兩個不同系統區分開來。第三部分,關于仰韶文化與仰韶體系。王仁湘先生指出,研究仰韶文化的來源,追本最為切要。目前學界構建的大仰韶文化體系內涵并不是單一的,內涵不同、源流不同。王仁湘先生將隴東―關中―陜南―豫西中心區的仰韶文化,分別命名為半坡文化、廟底溝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即典型仰韶文化。北首嶺下層劃為前仰韶文化。周邊分布區分別命名后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崗文化等。第四部分,前半坡來源問題。王仁湘先生在文中指出白家村文化(大地灣、老官臺文化)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直接來源。同時“北首嶺類型”似乎是白家村文化向仰韶文化過渡的一個中間類型,是已知仰韶文化最近的淵源,但北首嶺類型和仰韶文化半坡類型之間還有一段不小的缺環。第五部分,前仰韶:20世紀沒有完全破解的迷。
四、幾點思考
1、王仁湘先生在《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與程序問題》一文的第四部分(“命名確認”程序)中提出考古學文化命名的確認要通過國家級的學術機構(如中國考古學會),并詳細的闡述了“命名確認”的程序。這是他的創新之處。
2、通過這三篇文章的閱讀,發現它們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著密切的聯系。這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為出發點分別介紹了考古學文化的命名、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及它們之間的關系以及考古學文化淵源的探索問題。這三個問題在考古學文化的研究中自始至終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考古學文化研究的核心內容,也是我們在考古實踐中常常遇到的問題。那么,我們將運用什么樣的方法來進行考古學文化研究呢?
3、欲對一個考古學文化進行研究應當首先把握住它的空間范圍和時間幅度。這項研究中通常要用到類型學的方法。其次就是考古地層學的運用。
4、同樣的地層,為什么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王先生在《半坡與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一文中指出:爭辯的各方使用了地層學和類型學這樣的方法,路徑相同,證據確鑿,結論卻大相徑庭。為何出現這樣的局面,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里,怎樣解決,現在似乎還沒有到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但是在前人探索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我們依然可以總結出一些方法和經驗來。在考古學研究中,地層學和類型學是基本理論,關于這兩個理論的基本原理及基本內容上文已做詳細闡述,但是如何正確熟練的運用這些理論卻是一個較難的問題。
5、通過閱讀王仁湘先生的三篇文章,我對考古學文化及考古學文化的研究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們會發現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尚存在一些缺陷與不足,但是這也是我們不斷改進研究方法的動力,前人在探索過程中耗費的時間和精力,他們長時期的堅持等等,有太多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地方。
參考文獻
[1]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
[2]嚴文明:《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中的兩個問題》,《文物》1985年8期。
[3]張忠培:《研究考古學文化需要探索的幾個問題》,《中國考古學:實踐?理論?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安志敏:《試論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考古》1959年10期。
[5]馬承源:《略論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的問題》,《考古》1961年7期。
[6]楊建芳:《略論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的分期》,《考古學報》1962年1期。
[7]蘇秉琦:《地層學與器物形態學》,《文物》1982年4期。
篇(10)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2-0141-02
一、書名及作者簡介
書名:《民族文物通論》,作者:宋兆麟,1936年生于遼寧省遼陽市,是我國著名的民族考古學家。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兼職教授,中國民俗學會首席顧問,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長期從事考古學、民族學、民俗學研究,側重于中國史前文化和民間文化的研究,主要學術著作有《中國遠古文化》、《中國原始社會史》、《巫與巫術》、《中國生育信仰》、《中國民間神像》、《中國民族文物通論》、《共妻制與共夫制》、《女兒國親歷記》等。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經說過的“南汪北宋”兩位考古學者,其中的“汪”指汪寧生,“宋”就是指宋兆麟先生。蘇秉琦先生是宋兆麟的老師,這樣的評價從考古學的角度出發,既肯定了宋先生利用民族學資料去研究考古問題的學術方向,同時也是對他的一種鞭策。宋先生一直把這句評價當作自己研究工作的動力和目標。
二、內容概要
全書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理論方法問題,分七章,包括民族文物的概念、特點,田野調查方法,民族文物的整理保管,研究民族文物的理論與方法,民族考古問題,民族文物鑒定,民族文物的應用等。
第二部分為具體民族文物研究,分十章,民族文物豐富多彩,種類繁多,作者選擇了若干典型個例,與考古遺物對比,進行比較研究,這種綜合性研究,不僅介紹了若干研究方法,也進一步闡述了民族文物的價值。
第三部分為古代民族風俗畫研究,分七章,作者在本書中選出了若干清代民族風俗畫,加以剖析,對民族文物研究和鑒定有重要借鑒。
由于時間關系與精力所限,筆者僅選取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進行一些淺顯的歸納與總結,全書作者以第一部分的理論方法為基礎,輔以第二部分的具體事例,系統地論述了民族文物的相關理論,筆者也從具體事例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論方法的理性認識。筆者認為通過這兩部分的概述與分析,可以大致把握民族文物的核心內容與內在精神。作者在闡述民族文物理論時,詳以事例,并構建出一個較為全面的民族文物理論體系,為民族文物的保護工作提供了夯實的理論基礎。
三、書中經典
(一)民族文物定義
什么是民族文物?目前爭論較多。作者認為,民族文物是文物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的部分。民族文物是自民族產生以來,各民族所創造的、具有一定民族文化信息、又有一定歷史階段、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的文化遺物。民族文物是民族文化的物態形象,看得見,摸得著,是民族文化的有形載體。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所遺留下來的文物也具有多民族的內涵,這正是中國文物的重要特色。具體來說,民族文物有廣義狹義之分,前者是指自古而今的民族文物,是從民族產生至今各族所遺留下來的有價值的實物資料。包括考古發掘品、傳世文物和近現代民族文物。后者指清代或近代以來各民族所使用的文物。
作者對民族文物做了較為全面客觀的定義,使民族文物從空間與時間上與現在相連接,并有所區別。不僅總結出民族文物具有文有其獨特的特點物的一般特征,如不可再造、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等,而且歸納了近代民族文物也有其獨具的特點:
第一,古代民族文物多埋藏于地下,有地層保護,近代民族文物多于地上,最容易受到損壞;第二,古代民族文物多為無機物,近代民族文物則以有機物質為主,文物保護難度較大;第三,古代民族文物欠完整,近代民族文物較完整、信息量大,不但結構完整、功能明確,還有種種傳說;第四,古代民族文物基本為國家所有,近代民族文物有相當一部分屬于私人所有,這給文物征集工作帶來了一定難度。
(二)研究民族文物的理論方法
1.民族文物應該有自己的層次學。作者從自己所學考古學的背景出發,把相應的理念與構想帶入民族文物中,并根據民族文物的特點,提出民族文物層次學。如果比較而言,考古學的文化史是有序的,有明無誤的遞呈關系,下早上晚。考古學家可根據地層關系及所包括的文化遺物進行研究,然而民族文物沒有地層的堆積和保護,干擾嚴重,古今摻雜,而且本身又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具有無序性或紊亂性,關系錯綜復雜。民族文物研究不能像考古學那樣按地層發掘,而要有自己的理論方法,把無序的民族文物清理出來,弄清來龍去脈,找出時間、空間序列,也就是分清歷史層次,各就其位,還原其本來的歷史坐標。
為此,作者提出可以建立一種民族文物層次學,作為指導民族文物研究的理論之一。其中應包括下列內容: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物制度,找出其標準文物,作為鑒選有關民族文物的尺度;同一時代的同類文物,又有發展演變規律,運用這些規律也可以鑒別同一時期的有關文物。這樣就可以把堆積一處的眾多民族文物按時代系列,分出早晚,明確其時間性,這一點在工具、器皿、服裝、工藝品等方面都很實用,能找出它們的層次關系。
民族文物層次學,使數以萬計的民族文物的定位清晰起來,每件民族文物都能找到自己的歷史坐標――時間階段與空間位置,這對現階段的民族博物館工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應該建立民族支系學。作者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民族支系學,用以明確民族文物的族屬,這是對民族文物的細化。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而且不少民族內部又分許多支系,反映在物質文化或文物制度上當然也千差萬別。我們在處理民族文物時首先應該確認屬于某種民族,即確定民族文物的族屬,這是民族文物工作的基礎。其次為了區別出民族支系、地區,必須把某一民族的支系、地區分別開來。
以清代云南彝族為例,即有摩察、羅婺、魯屋、聶素、撒摩都等支系,每個支系都有一定地域、物質文化特點,其文物是不一樣的。類似問題在藏族、納西族、白族、傣族、哈尼族、苗族、蒙古族都或多或少存在著,民族內部的支系,不僅涉及族源,族史,在分布地區、語言、文物上也有明顯差別,因此作者認為民族支系學在民族文物研究上有重大意義,可建立民族支系學理論體系,還原出民族文物曾所在族屬的全貌。
民族支系學的宗旨是探索各支系的淵源,在本民族中的地位、文物和語言特點、分布區域及其演變,本支系與其他支系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異同。從中得出的理論原則,必然會深化民族史、民族學研究,有助于物質文化和民族文物的探索。如果說民族文物層次學是解決民族文物發展系列的準則,那么民族支系學則是解決民族間、民族內部支系間關系的重要理論準則。
任何一個民族支系的確定,都應該歸納出若干文化特征,如同考古學文化必須有“一群具有明確的特征的類型品”,具體地說,即分布于一定地域的、存在一定時間的,具有若干共同特征的民族文化。這些特點,既是該支系所特有的,又是他們與其他支系相區別的地方。以海南黎族為例,其包括五個支系――■黎、杞黎、本地黎、美孚黎、法透黎。每個支系在地域分布上是不一樣的,語言也有一定差別,當然在文身的圖案上也有一定差別。
四、存留問題的淺析
(一)五大民族文物系列
作者在書中針對民族文物的分類提出五大民族文物系列:生產工具、舟車、手工工藝、宗教文物與文字。筆者認為還應包括民族服飾、生活用具和建筑,構成民族文物系列。
因為從分類的內容來看,作者是從功能的角度來劃分民族文物的,如果增加民族服飾、生活用具和建筑,就反映了民族文物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全貌。
(二)有關“民族考古”
作者在文中全面論述了民族文物與考古的問題,客觀分析出民族考古的定位與內涵。
首先,不能把民族、考古比較研究與民族考古學混為一談。
其次,民族考古比較研究應該是考古學的一種新的研究方法。1975年美國75屆人類學會的主題就是“民族考古學――民族學與考古學的關系”。也說明它是兩種學科的結合,是考古學與民族學比較研究的方法。不難看出,民族考古比較研究是以考古學為主,民族學只是它的一種研究手段,所以應該突出考古學。最后,作者認為所謂民族考古學并不具備一種學科的特征。
由于學科是指學術研究部門的分類,每種學科的確立,必須有自己的研究領域,自己的研究對象、方法、理論和任務,但是民族考古學并沒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對象,所研究的課題都是考古學的內容,也沒有自己的理論與方法。作者認為,他們做的,只是把民族學方法、資料引進考古學而已。
綜上所述,民族學與考古學比較研究,只是多學科比較研究的方法,還不能單獨成為一個學科――“民族考古學”。
篇(11)
196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成員、歷史學部主任、學部委員、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主任。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考古學報》《考古學集刊》《中國考古學》(英文版)主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考古學學科評審組專家。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委員。國家級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享受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古都學會名譽會長、德國考古研究院通訊院士。
研究領域主要為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學和秦漢考古學。
先后在美國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澳大利亞拉楚布大學、日本東京大學、韓國首爾大學、德國考古研究院、瑞典東方博物館、意大利波羅尼亞大學、法國遠東學院、墨西哥國立人類學研究所、秘魯國立歷史博物館、埃及開羅大學、印度國立博物館、巴基斯坦國際文化交流中心、越南考古學院、香港中文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等海外著名大學、學術機構進行學術講演、訪問研究。
曾先后參加并主持秦都咸陽遺址、西漢十一陵、關中唐十八陵、秦漢櫟陽城遺址、西漢杜陵陵園遺址、漢長安城遺址、秦阿房宮遺址等考古勘探、發掘。已出版考古學專刊、專著、論文集十余部,二百五十多篇。
專業介紹
考古學(本科)
門類:歷史學
學制:4年
授予學位:歷史學學士
簡介:考古學就是根據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實物,研究古代社會歷史的科學。按照考古學研究的年代范圍、具體對象、所用手段和方法的不同,考古學可具體劃分為史前考古學、歷史考古學、田野考古學及各種特殊考古學等分支。本專業培養具備考古學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有進一步培養潛能的高層次專門人才和能在考古、文物、博物館等事業單位及國家機關從事研究、教學、管理等實際工作的考古學高級專門人才。學習內容包括考古學的基本理論、方法與技能,考古學多學科交叉發展趨勢和世界考古學發展概況,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史、研究現狀;接受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博物館學、文物學理論、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古代漢語、史料學、地理學、第四紀環境學、古人類學等方面的基本訓練。根據陽光高考網的統計數據顯示,該專業2012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性別比例:男47%:女53%;近幾年全國就業率區間:2010(85%~90%),2011(80%~85%);該專業全國報考碩士較集中的專業:考古學及博物館學、考古學、文物與博物館、科學技術史等。
打開電腦,輸入“劉慶柱”進行搜索,關于劉老個人經歷的介紹性文字不多,更多的是他那一長串的研究成果。9月初的一天下午,記者帶著眾多讀者對考古專業的好奇,敲開了劉老的辦公室。“請進。”隨著一聲底氣十足的回應,劉老起身,笑容滿面地招呼我們進門,桌上早就備好了茶葉、水杯。
劉老比他的實際年齡年輕很多,面色紅潤,腰板挺直,精神矍鑠,言談間思維非常敏捷。兩個小時的談話,劉老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往古代的大門,讓我們體驗了一次跨越時空的穿越,考古,原來如此神奇!
大學招生指南:您認為考古學是一門怎樣的科學?
劉慶柱:考古學是研究時間的科學。考古學所研究的時間,跟物理學研究的時間有差異。物理學是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從物質結構角度來研究時間,而考古學則是以時間為軸,研究以人為對象以及和人相關的環境的科學,是一個更大的時空人文概念。因此說考古學也是人學,研究人的科學。人類通過考古了解自己從過去幾百萬年,幾十萬年一直到現在,歷經了怎樣的變化。這種變化是由何種因素引起的。比如現在的各種疾病,以前就有嗎?還是以前沒有,現在變異了?找出發展變化的因素,就能為現在各種疾病的治療提供有力的參考。
19世紀中期,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兩門大學科結合的基礎上產生了考古學,因此考古學也是一門綜合性科學。它的很多方法論都是來自于自然科學,研究的問題卻不單單局限于物品本身,而是透物見人,通過所發掘的物品,推斷當時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機構、主流的思想文化,等等。
大學招生指南:我們該怎樣理解考古學所研究的范圍?
劉慶柱:如果劃定一條時間分界線,分出古代和現代,分界線一側的古代時空范圍都是考古學所要研究的內容。人類的歷史大約是200萬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按中國來說才4000多年,不到整個人類長河的百分之零點幾。因此要想弄清楚歷史,必須要通過考古學,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幾的問題都要考古學來解決。
我總說我這一輩子越干越覺得有點失望,失望在哪兒呢,好多東西越弄越不清楚了,越干越沒頭緒了。我總對我的學生說,你們年輕趕緊寫,別到了像我這個年紀,前怕狼后怕虎總感覺沒說透,下筆總有猶豫。但后來我也考慮,對于沒有完全說透的東西也要辯證看,要是所有東西都說透了,那就沒有科學了,科學就結束了。我能把科學做到頭嗎?不用說科學,就是科學的一個方面我也做不到頭,因為它是滾動式的,發展的。什么是發展?發展就是否定之否定。真理都是階段性的,沒有永恒的,都是相對的,相對于這個時空階段的認識論,認識基礎,你只能看到這一步,而人的一生相對于你所要研究的東西來說,時間太短。所以考古學是永遠奮斗不完的,既有魅力,也有挑戰力,還有想象力。在這里你不能停步,也停不了步。
大學招生指南:當初為什么會選擇考古學呢?
劉慶柱:我初中那會兒就對歷史、文學感興趣。到高中時開始對哲學、世界史比較感興趣。因為當時我家離圖書館很近,看書很方便,就去看了很多這方面的書,但后來我就覺得關于好多事情的評論反反復復的,反而弄不清楚了。比如歷史,這中間還不是簡單的好與不太好的說法區別,有可能是是與非、紅與黑的差異,那么歷史到底是什么樣子?怎樣弄清楚歷史的本來面目?有沒有更科學、更先進的辦法去驗證?不能想怎么說就怎么說。后來我就接觸到了考古學,這是拿物說話的,這些被挖出來的東西,它本身不會帶有立場、觀點。但是寫東西的人就有立場,有觀點,尤其寫作者是跟當時的歷史、當時的政治、當時的經濟、當時的文化有關的人。比如,不會說自己的民族不好,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最優越的,等等。但世界上沒有“最”字號的,你要是最優越的,難道別人都是二等的!其實,世間萬物沒有絕對,恰恰是人類把許多東西說成了絕對。因此,想弄清楚事物的真實面貌,就得找些更客觀的,更科學的手段去驗證,才不容易被某些人為的資料所左右。
大學招生指南:您實際接觸到考古后,感覺它跟您想象的一樣嗎?
劉慶柱:好像沒差距。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我的關注點不在其他方面,就想著能夠發現些什么東西,解決些什么問題;另一方面那個時代跟現在不一樣,生活條件的反差沒那么大,現在夏天有空調,冬天有暖氣,70年代冬天都是用煤球爐子,里頭外頭一樣冷,夏天里頭外頭一樣熱。可能有時候在地里頭感覺還比家里要舒服點,但也不好受,像五六月的時候,鉆到玉米地里去考古,那時候,地里玉米都長高了,人站在空地上都覺得熱,鉆到玉米地里頭悶得很,鉆探又不能穿長袖衣服,玉米葉子拉得身上一道一道的口子,很難受。但如果發現了重要遺跡現象,什么難受都全被拋之腦后。如果興趣點不在考古的人去那樣的地方,奔著錢去的,卻找不到錢,那他才難受呢。
80年代考古的時候,生活條件有了一定改善,有一陣子我們租住的是農民擱放農具的房子,房子分兩層,上頭放糧食,下頭住人,因為放糧食的房子得保持通風,到了冬天,不刮風還好,一刮風四面透風,睡覺的時候煤球爐子一封,屋里放一盆水,不一會兒就結冰了。半夜里,老鼠在頭頂上噔噔噔地跑,跑著跑著,“吧唧”就有一只小老鼠掉下來。但那時候我天一亮去做發掘,晚上回來寫東西,總覺得有干不完的事兒,也就不覺得苦了。所以說,人必須得有個奮斗目標,有奔頭,有了奮斗目標,有了奔頭,其他無關的東西也就淡化了。
大學招生指南:您對考古學如此著迷,考古學的意義具體都表現在那些方面?
劉慶柱:只要你認為關于人的有趣的問題,考古學都能給你解答,風水問題、疾病問題、算卦問題……考古學都能給你一個科學的解答。比如,古代的皇帝迷信嗎?為什么外國的中心建筑是教堂,中國故宮里頭核心建筑是太和殿?看似普通的建筑,它傳達出的是一種政治理念,是誰服從誰。皇宮里頭唯一有的廟是太廟,太廟不是供奉釋迦摩尼的,是供奉皇帝的列祖列宗的,以此證明皇帝身份的合法性,是對自我的一種證明。這就說明了國家的性質是政教合一還是國家至上。清朝的皇宮跟唐朝的皇宮有什么區別嗎?沒有,這就是對國家核心文化的認同。什么是傳統文化,傳統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多民族共同體,同類項體現在哪兒?中華民族普適的文化價值在哪兒?等等,這些都是考古學家探究的物質文化要表明的東西。
考古學就是通過研究過去掌握對現在仍起作用的規律,或是通過研究過去,解決用現在的辦法解決不了的難題。比如90年代論證三峽大壩的可行性,大壩多高的蓄水水位合適?雖然考古學無法解決諸如大壩可以承載多高的水位,引起怎樣的生物變化這樣的問題,但通過考古學可以找出歷史上這個地方的水位最高達到過哪兒。當然,僅僅憑借考古學找出歷史水位高度,不表示最大承載量能到這里,還需要去找物理學家做計算,找地質學家看巖石的性質能不能承受得了。
比如現在研究氣候,考古也研究氣候。說現在氣候變暖了,你怎么知道氣候變暖了,得有對比才成。2000年前的氣候怎樣,1000年前的氣候怎樣,得形成一條曲線圖,從歷史的長鏈條來看才能夠找出規律。考驗真理最主要的根據就是時間,真理都應該放到時間這個長鏈條里頭去考察,在時間隧道中就可以得到證實。比如對全球變暖原因的探討,主要原因是什么?是空氣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嗎?三千年前北京地區氣候溫暖還有象呢,后來變冷了,到2000多年前又變暖了,這是為什么?要研究這個問題,首先得弄清楚導致全球變暖的因素有哪些,然后各占權重多少得說清楚。不能為目的性而一味地夸大某些原因,這其實是人為地將學科割裂,都從各自學科的角度來考慮分析問題,難免得出片面的結論。
考古學是研究人的科學,應該說是未知數很大的科學,很具有挑戰性的科學,既屬于人文科學范疇也屬于自然科學范疇,最先進的自然科學方法可以被考古學采納為己所用,那些考古學要去研究解決的很古老的問題,同時也可以是很先進的問題,挑戰性也就在這,光解決古老的問題就失去了趣味,古今結合才會有用。所謂:“有為才有位,有位得有為。”因此考古學得有所作為,對歷史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古為今用,如果純粹是為古而古,那是沒有意義的。
大學招生指南:談到學科之間的聯系,您對當前的學科教育有什么看法?
劉慶柱:學科是人分的,所有的學科都有優點也都有局限,認識到這個,就要注意多學科結合,注意復合型人才的培養。然而我們當今的時代,不像柏拉圖那個時代,不像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時代。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積累的知識越來越多,因此作為個人,必須有一個切入點。愛好自然科學,可以從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去展開,愛好人文科學可以從哲學、歷史、文學等切入,得選一科,不能一把抓。
教育有教育的規律,從小到大,由淺入深,分學科是必然的。學習真像蓋房子,先要打好地基,先專后博,不斷聯系學習,一點點地積累。但頭腦中始終得有用聯系觀點看問題的弦兒,比如搞學術研究都需要有個學科帶頭人,他雖然不做某些方面的具體研究,但知道相關的聯系,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需要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