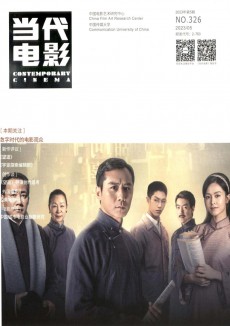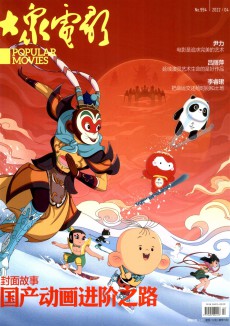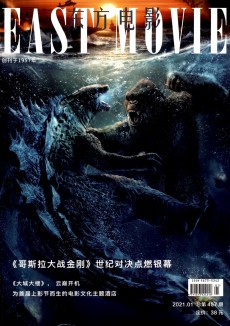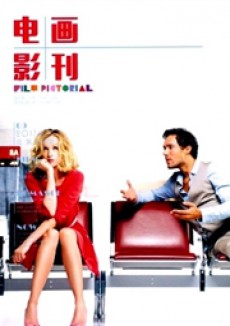非遺電影的故事化表達(dá)
時(shí)間:2023-03-24 14:39:24緒論:寫作既是個(gè)人情感的抒發(fā),也是對(duì)學(xué)術(shù)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fā)表云整理的1篇非遺電影的故事化表達(dá)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fā)。

隨著時(shí)代的快速發(fā)展,國家處在變革的浪潮之中,許多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受到西方文化沖擊、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變革、國人價(jià)值取向變化等影響,漸漸走向衰落。
一、“非遺”題材電影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談及“非遺”題材電影,首先需要明確相關(guān)概念。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法》規(guī)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chǎn)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tǒng)文化表現(xiàn)形式,以及與傳統(tǒng)文化表現(xiàn)形式相關(guān)的實(shí)物和場(chǎng)所,以下簡(jiǎn)稱“非遺”。非遺題材電影的概念在此基礎(chǔ)上引申而來。王巨山與李帥超在《構(gòu)建民族記憶的文化景觀——談“非遺”題材電影的創(chuàng)作與傳播》這篇文章中提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題材電影不是因?yàn)槟撤N技巧而得名,而是以題材為中心確立的一類電影。這類電影緊緊圍繞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事象本身或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承人的事跡展開創(chuàng)作,或反映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歷史命運(yùn)與時(shí)代傳承,或反映傳承人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續(xù)中的曲折經(jīng)歷。”[1]由于現(xiàn)代生產(chǎn)生活方式變遷、社會(huì)認(rèn)知和理念上的偏差、保護(hù)措施不夠有效等原因,部分非遺面臨著失傳的危險(xiǎn)。鑒于此,國家越發(fā)注重非遺的傳承與保護(hù)。藝術(shù)工作者也敏銳地捕捉到這一發(fā)展趨勢(shì),開始將目光投向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挖掘其中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使之成為創(chuàng)作的母題,呈現(xiàn)出一系列膾炙人口的優(yōu)秀電影作品,如《百鳥朝鳳》《一個(gè)人的皮影戲》《爾瑪?shù)幕槎Y》等。通過相關(guān)影視作品,社會(huì)大眾加深了對(duì)“非遺”文化的了解,相較于傳統(tǒng)傳播方式,影像傳播具有更直觀,易接受,更真實(shí)的特點(diǎn),對(duì)創(chuàng)新“非遺”保護(hù)路徑,促進(jìn)“非遺”的傳承與發(fā)揚(yáng),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二、“非遺”題材電影故事化表達(dá)創(chuàng)作傾向
談及電影的分類,根據(jù)內(nèi)容、形式、功能不同,可分為諸多類型,這里我們不進(jìn)行具體類型的劃分,只是根據(jù)創(chuàng)作方式的不同,簡(jiǎn)單將其劃分為故事片和紀(jì)錄片。簡(jiǎn)單來說,故事片所表現(xiàn)的是由創(chuàng)作者虛構(gòu)出來的故事,經(jīng)過藝術(shù)化加工,是導(dǎo)演想讓受眾看到的事情;紀(jì)錄片則記錄了真實(shí)的生活,將事物的原貌展現(xiàn)在受眾面前,是經(jīng)過簡(jiǎn)單的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剪輯加工的產(chǎn)物,力求真實(shí)。如今,國內(nèi)的電影創(chuàng)作實(shí)踐存在著兩種創(chuàng)作傾向,上海白玉蘭國際紀(jì)錄片影展主席應(yīng)啟明在分析國產(chǎn)紀(jì)錄片的狀況時(shí)指出:“紀(jì)錄片的‘故事化’和故事片的‘紀(jì)錄化’其實(shí)是當(dāng)今電影發(fā)展進(jìn)程中的兩股潮流。讓中國的紀(jì)錄片善于講故事,這不僅僅是一種拍攝手法,更是符合現(xiàn)代人審美需求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2]
(一)“非遺”題材紀(jì)錄片故事化
梳理初期電影史不難發(fā)現(xiàn)電影“記錄真實(shí)”這一核心特點(diǎn),紀(jì)錄片沿襲了電影這一特性并逐漸發(fā)展。紀(jì)錄片是以現(xiàn)實(shí)生活為創(chuàng)作素材,表現(xiàn)真人真事,并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行藝術(shù)加工的一種電影或電視藝術(shù),表現(xiàn)真實(shí)是紀(jì)錄片的核心。紀(jì)錄片可以真實(shí)再現(xiàn)“非遺”存在的現(xiàn)實(shí)空間,直觀展現(xiàn)“非遺”傳承人所面臨困境時(shí)對(duì)“非遺”文化的堅(jiān)守。正是因?yàn)椤罢鎸?shí)”的特性,創(chuàng)作者更多地選擇這種藝術(shù)形式。同時(shí),紀(jì)錄片也面臨著拍攝周期較短且內(nèi)容龐雜、現(xiàn)場(chǎng)拍攝情況復(fù)雜多變、說理性較強(qiáng)不易被接受等問題,在最終效果上,不如故事片更容易獲得受眾認(rèn)可。部分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者發(fā)現(xiàn)了這一問題并結(jié)合大眾需求,在作品中出現(xiàn)了紀(jì)錄片故事化的創(chuàng)作傾向。紀(jì)錄片故事化在保留“真實(shí)性”的同時(shí)增強(qiáng)戲劇性,有別于傳統(tǒng)紀(jì)錄片,用故事的方式呈現(xiàn),使之更容易被受眾所理解和接受,增強(qiáng)傳播的張力。在紀(jì)錄電影《天工蘇作》中,創(chuàng)作者將蘇州具有代表性的九種傳統(tǒng)工藝宋錦、核雕、燈彩、明式家具、蘇式船點(diǎn)、蘇繡、香山幫建筑營(yíng)造、緙絲、玉雕與十二位“非遺”傳承人堅(jiān)守傳統(tǒng)文化的故事相結(jié)合。電影不再是教科書式的普及,而是以傳承人的視角為切入點(diǎn),講述他們與這些傳統(tǒng)工藝的不解之緣。蘇州船點(diǎn)非遺傳承人董嘉榮一輩子都沉醉在船點(diǎn)鉆研中,退休后以照顧孫女為寄托,但孫女長(zhǎng)大了,要離開家去接受更好的教育,臨別前,老人將萬般不舍都凝聚在給孩子做的船點(diǎn)中。他把孫女最愛的卡通形象做成了惟妙惟肖的船點(diǎn),祖孫二人溫馨的一幕被鏡頭記錄下來。紀(jì)錄片以故事化的手法展現(xiàn),為生硬的“非遺”披上一層溫暖的外衣。以溫情的故事展現(xiàn)“非遺”傳承相比于填鴨式的一味輸出,達(dá)到了良好的傳播效果。但這種創(chuàng)作傾向是否對(duì)紀(jì)錄片記錄真實(shí)的本質(zhì)產(chǎn)生了動(dòng)搖?是否影響了受眾在觀看紀(jì)錄片時(shí)的審美感受,使之對(duì)紀(jì)錄片與故事片的區(qū)分產(chǎn)生了混淆?因此,這種傾向還是存在一定問題,有待商榷。
(二)“非遺”題材故事片紀(jì)錄化
故事片是綜合了多種藝術(shù)形式,以表現(xiàn)和虛構(gòu)為基礎(chǔ),通過演員表演來完成的一種影片類型。與紀(jì)錄片不同,故事片的紀(jì)實(shí)性是在藝術(shù)表現(xiàn)基礎(chǔ)上的紀(jì)實(shí),其所展現(xiàn)出的真實(shí)并非生活真實(shí)。故事片具有較強(qiáng)的戲劇性、可觀賞性、商業(yè)性,這些特性使之更貼近受眾需求,同時(shí)也容易被復(fù)制,成為一種模板化的產(chǎn)物,好萊塢電影生產(chǎn)模式就是典型的代表。這些優(yōu)點(diǎn)在促進(jìn)商業(yè)片、故事片快速發(fā)展的同時(shí),也側(cè)面暴露出所存在的問題,模式化的生產(chǎn)使部分影片過度商業(yè)化,大量運(yùn)用商業(yè)噱頭吸引受眾的關(guān)注,完全喪失了真實(shí)性,過于追求戲劇化效果。因此,在進(jìn)行創(chuàng)作時(shí)應(yīng)注意規(guī)避唯商業(yè)化、過度戲劇化、模板化復(fù)刻等問題。“非遺”是千百年傳承而來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凝結(jié),因此在進(jìn)行“非遺”題材創(chuàng)作時(shí)必須格外注意其文化背景,不能喪失真實(shí)性,在傳統(tǒng)技藝、歷史傳承、精神延續(xù)等方面都要求真實(shí),展現(xiàn)“非遺”文化真實(shí)的生存現(xiàn)狀。因此,在部分影片中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創(chuàng)作傾向,他們主張?jiān)趧?chuàng)作時(shí)應(yīng)發(fā)掘“非遺”的文化內(nèi)核,在真實(shí)的基礎(chǔ)上,發(fā)揮故事片在人物形象塑造、敘事情節(jié)、故事結(jié)構(gòu)等方面的優(yōu)勢(shì),將故事片與紀(jì)實(shí)性相結(jié)合,創(chuàng)作出社會(huì)大眾喜聞樂見的“非遺”故事。例如,“非遺”題材微電影《花兒金》,根據(jù)真人真事改編,以國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花兒金”第五代傳承人金鐵鈴為故事原型,講述了金鐵鈴不忘初心,苦心鉆研,堅(jiān)守傳承的故事。影片中金廣成因頸椎病嚴(yán)重,無法參加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博覽會(huì),孫子小金看出爺爺?shù)男乃迹父鸂敔攲W(xué)習(xí),傳承技藝。影片在孫子跟爺爺悉心學(xué)習(xí)中鋪展出花兒金的制作工序,漿鑿染窩粘攢,六道傳統(tǒng)工藝在教學(xué)過程中自然地講述出來,既保證了故事性、觀賞性,又將傳統(tǒng)手藝的精髓展現(xiàn)在觀眾面前。影片的最后有一段對(duì)“非遺”傳承人金鐵鈴的采訪,金鐵鈴講述了“花兒金”的發(fā)展歷程和自己對(duì)“非遺”的堅(jiān)守。這種手法使整部電影更添真實(shí)性。故事片的紀(jì)錄化在貼近受眾需求的同時(shí)也做到了“非遺”文化的普及,相比于紀(jì)錄片更容易被人所接受,增大“非遺”的傳播張力。但這種傾向并不被業(yè)界廣泛接受,許多人認(rèn)為這類影片過于平淡,戲劇性較弱,不能廣泛地運(yùn)用。以上兩種創(chuàng)作傾向既有優(yōu)勢(shì)也有劣勢(shì),還未形成可以廣泛推行的創(chuàng)作方式,筆者在這里進(jìn)行歸納總結(jié),只是想討論業(yè)界這種實(shí)踐的可行性,希望可以通過實(shí)踐者們的不斷創(chuàng)新一起探究“非遺”保護(hù)新路徑。
三、“非遺”題材電影的故事化表達(dá)
(一)空間環(huán)境的敘事功能
“非遺”題材影片中,無論是何類型在呈現(xiàn)時(shí)總歸會(huì)依托于真實(shí)的“非遺”,而不是憑空捏造的,而真實(shí)的“非遺”大多有著悠久的歷史,并處于特定的地理空間中,如果脫離“非遺”土生土長(zhǎng)的特殊環(huán)境,“非遺”便喪失了其生命力。在“非遺”題材影片中,不僅故事情節(jié)、人物形象、劇作結(jié)構(gòu)等參與敘事,“非遺”特定的鄉(xiāng)土環(huán)境同樣起到了空間敘事的作用。真實(shí)的鄉(xiāng)土空間、本地方言、特有的民歌曲調(diào)等均是敘事的組成部分,為“非遺”故事增添了一抹淳樸的鄉(xiāng)情。“非遺”題材電影《云朵上的繡娘》以羌族的人文歷史以及當(dāng)?shù)氐脑鷳B(tài)風(fēng)土人情為背景,展現(xiàn)寧強(qiáng)羌繡文化,影片以漢中寧強(qiáng)極具特色的風(fēng)土人情為主線,講述了啞女繡娘金鳳在親情、友情的幫扶下最終完成傳統(tǒng)羌繡作品《景星麟鳳》的故事。影片中出現(xiàn)了大量陜西寧強(qiáng)的自然風(fēng)光,將當(dāng)?shù)厝罕姷恼鎸?shí)生活融入影片創(chuàng)作中,古老鄉(xiāng)村中非遺傳承人的堅(jiān)守與當(dāng)?shù)靥赜械目臻g環(huán)境相呼應(yīng),引發(fā)了觀眾對(duì)羌繡和守護(hù)者的崇敬之情,鄉(xiāng)土鏈接著鄉(xiāng)情,受眾對(duì)故土的眷戀也反映了國人對(duì)民族的情感依戀。空間敘事起到了渲染烘托、抒情表意的作用,在增加故事真實(shí)性的同時(shí),也易引發(fā)受眾共鳴,因此在“非遺”題材創(chuàng)作時(shí),應(yīng)利用好鄉(xiāng)土環(huán)境,增強(qiáng)其空間敘事功能。
(二)“非遺”精神的外化
“非遺”題材影片傳播過程中不僅為國人普及“非遺”知識(shí),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傳播,“非遺”精神可概括為一種追求極致的匠人精神和永不放棄的執(zhí)著堅(jiān)守。影片中“非遺”精神被具體的物件所外化出來,受眾在觀影的過程中被這種純粹的精神所感染,真正理解“非遺”的本質(zhì)。“非遺”題材電影《花兒金》中,開頭部分,孫子問爺爺:“這樹為什么不開花?”爺爺說:“大家都看的時(shí)候,花就開了。”而到了結(jié)尾處,孫子說:“爺爺,您看,棗樹開花了。”爺爺說:“據(jù)說這棵百年的棗樹還能結(jié)出果來呢。”祖孫二人簡(jiǎn)短的對(duì)話被分別放置在影片的開頭和結(jié)尾部分,相同的問題,回答卻截然相反,這里的棗樹具有象征意義,棗花的未開和盛開象征著“非遺”花兒金能否傳承下去,影片最后,百年的棗樹開花了,甚至還要結(jié)果,象征花兒金終于找到傳承人,并且重新被大眾所熟知。百年樹齡的棗樹見證了花兒金代代相傳,這不僅是非遺傳承人執(zhí)著堅(jiān)守的象征,也是花兒金“非遺”精神外化的一種產(chǎn)物。除此之外,許多觀眾所熟知的影片中都有“非遺”精神的外化,比如《百鳥朝鳳》中的嗩吶、《一個(gè)人的皮影戲》中的皮影等,這些具體的物件貫穿電影始終,推動(dòng)影片矛盾沖突的展開,小小的物件在“非遺”傳承中不斷沉浮,也象征了“非遺”保護(hù)之路的艱辛,這是匠人對(duì)傳統(tǒng)文化執(zhí)著堅(jiān)守精神的外化。
(三)“非遺”堅(jiān)守者的人物形象塑造
人物形象塑造是電影敘事重要的組成部分,一個(gè)有血有肉的人物,往往更易引發(fā)受眾共鳴,產(chǎn)生情感鏈接。關(guān)于人物形象塑造,姚扣根和陸軍曾詳細(xì)解釋:“戲劇人物的塑造,從藝術(shù)形象出發(fā),主要是塑造出各具特色、栩栩如生的個(gè)性形象并在這些個(gè)性形象上,各個(gè)打著他們自己所生活的那個(gè)時(shí)代和社會(huì)的印記,即塑造出具有典型意義的‘這一個(gè)’。”[3]人物形象塑造離不開人物性格,性格鮮明的人物更加具有感染力,而在“非遺”題材電影中,大多有“守護(hù)者”這一形象,他們往往具有堅(jiān)韌不拔、追求極致的性格特點(diǎn)。同時(shí),復(fù)雜多樣的人物性格塑造出典型人物。“守護(hù)者”的形象不僅是“非遺”最好的代言人,同時(shí)也反映出一個(gè)時(shí)代的悲歡。《百鳥朝鳳》中的焦三爺,一生為嗩吶而活,直至死亡都沒放下心中的堅(jiān)守。他收下天明的那一天要他發(fā)誓,嗩吶離口不離手,這是他對(duì)天明的要求,也是自己踐行了一輩子的事。無論面對(duì)洋樂隊(duì)的沖擊還是百姓不再認(rèn)可嗩吶,焦三爺從未放棄,依舊堅(jiān)守匠心,尋找突破困境的辦法,表現(xiàn)了焦三爺堅(jiān)韌不拔、百折不撓的性格特點(diǎn)。影片最后,焦三爺與徒弟合奏了一首《百鳥朝鳳》,這首曲子要吹給有德行的人,不僅是送故人最后一程,也是與嗩吶最后的告別。直到吹到吐血,焦三爺?shù)膯顓榷紱]有跑一個(gè)音,側(cè)面反映出老一代匠人追求極致的性格。天明接過焦三爺嗩吶的那一刻,也代表了這門傳統(tǒng)手藝?yán)^續(xù)延續(xù)的可能,焦三爺終于能夠安心地離開。焦三爺這一人物一出場(chǎng)就帶著不怒自威的氣勢(shì),但是對(duì)徒弟也有著柔情的一面,復(fù)雜的人物性格塑造出生動(dòng)的人物形象,同時(shí)也引發(fā)了受眾對(duì)“非遺”和“時(shí)代”的反思。
四、結(jié)語
“非遺”題材下不同類型的影片有著不同的創(chuàng)作傾向,但是都離不開其內(nèi)核——真實(shí)的非遺故事。“非遺”題材電影依托于真實(shí)的非遺技藝,在故事結(jié)構(gòu)、人物形象塑造、情節(jié)敘事上施以創(chuàng)作,增強(qiáng)其觀賞性和可接受度,加深社會(huì)大眾對(duì)“非遺”的了解與喜愛,推動(dòng)“非遺”的傳承與發(fā)展,將傳統(tǒng)“非遺”與現(xiàn)代傳播技術(shù)相結(jié)合,創(chuàng)新了“非遺”傳播的路徑。
參考文獻(xiàn):
[1]王巨山,李帥超.構(gòu)建民族記憶的文化景觀——談“非遺”題材電影的創(chuàng)作與傳播[J].民族藝術(shù)研究,2016,29(04):36-42.
[2]希拉·柯倫·伯納德.紀(jì)錄片也要講故事[M].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3]姚扣根,陸軍.編劇學(xué)詞典[M].上海文匯出版社,2017.80.
作者:郭玥 于利平 單位:山東藝術(shù)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