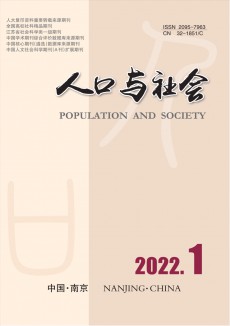人口紅利的定義大全11篇
時間:2024-01-16 16:18:34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人口紅利的定義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國內外學者從“機會”、“期限”、“源泉”、“過程”等不同的角度定義了人口紅利,界定了它的本質。
“機會論”將人口紅利的含義和本質界定為人口年齡結構年輕化提供的經濟增長的機會。發展中國家人口經歷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結構轉變。此結構中,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相對較低,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相對較高。它使一個國家擁有較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撫養負擔輕,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機會,即“人口機會窗口”。
“期限論”將人口紅利的含義和本質界定為人口撫養比處于高低兩個閥值之間的一段時期。一個國家在人口年齡結構不斷轉變的過程中,如果人口總撫養比低于某個閥值,則人口機會窗口開啟。一旦高于某個閥值,則人口機會窗口關閉。人口紅利就是介于兩個閥值之間的,有利于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
“源泉論”認為,較高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會導致勞動力數量的擴大和社會儲蓄量的增加。它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源泉,這種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或源泉就是人口紅利。
馬瀛通和穆光宗從過程的層面界定了人口紅利及其本質。馬瀛通認為,所謂人口紅利,實質是指在一定平均預期壽命及科技水平的基礎上,歷經努力使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從不適應向適應轉變的過程。而穆光宗將人口紅利的實質界定為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過程。
人口紅利的分類研究
關于人口紅利的分類研究,目前學術界最權威、最有影響力的分類是將它分為第一和第二人口紅利。第一人口紅利是指生產性人口比重增加導致的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人口年齡結構轉變過程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的增加會導致一個國家生產性人口比重的增加和撫養性人口比重的下降,從而導致人均產出的不斷增長。在第一人口紅利的基礎上,Andrew Mason and Ronald Lee進一步提出了第二人口紅利的學說。在人口老齡化的過程中,有勞動能力的人出于對未來養老的擔心,在年輕時會產生更強烈的資產積累動機,導致社會的投資增加,引起資本深化,即使有效勞動力數量下降,國民經濟也會因人均資本的增加而保持一段快速增長的時期,這一情形稱為“第二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關于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現有文獻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實證研究。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否顯著,學術界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
一種觀點是以蔡、王德文、王豐等學者為代表的“顯著論”。蔡認為在1978-1998年間的年均9.5%的GDP增長率中,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轉移的貢獻分別為24%和21%。王德文等的研究表明,中國總撫養比的邊際效應為-0.115,即總撫養比下降一個單位將導致經濟增長速度加快0.115個百分點。王豐等人的實證研究結果指出,人口紅利解釋了中國1982-2000年間經濟增長的15%。
另一種是以Bloom,Canning,Sevilla,Williamson,尹文耀,李善同為代表的“非顯著論”。他們認為,大量勞動年齡人口的存在不一定會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源泉,而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下降也不必然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桎梏。雖然“顯著論者”的實證結果表明,“人口紅利”對20世紀東亞經濟高速增長的貢獻達到1/3,但“非顯著論者”發現,經歷了和東亞國家類似的人口結構改變的拉丁美洲,出現了高通貨膨脹和政治不穩定的經濟社會被動局勢,經濟增長裹足不前,人口紅利并沒有使拉丁美洲各國實現自身的發展。對于用人口紅利解釋東亞經濟增長奇跡的學說,“非顯著論者”的反駁是,日本和韓國“人口機會窗口期”與“經濟高速增長期”的錯位使“顯著論者”對于用人口紅利來解釋經濟增長的理論大打折扣。日本的“人口機會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期出現在1955-1973年。“人口機會窗口期”對應的是經濟增長的低速期甚至負增長期。顯然,用滯后的“人口機會窗口期”來解釋經濟增長有失偏頗。
二是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條件研究。人口紅利并不必然導致經濟增長,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需要一定的條件。人口機會窗口等于人口紅利是目前理論界對人口紅利的誤解,人口機會窗口的開啟只是為獲得“人口紅利”提供了一個機會,并不會自動地導致更快的經濟增長。勞動力的充分就業是獲得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是實現人口紅利的關鍵,勞動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給是利用人口紅利的保障。
三是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途徑研究。穆光宗將這些途徑歸納為三種效應:創富效應、投資效應、積累效應。創富效應源自于勞動力的充裕供給所創造的社會財富。投資效應是指高儲蓄率導致的投資增加所產生的經濟增長效應。積累效應是指社會保障支出少和生產性消費支出多而導致的財富積累效果。
人口紅利計算標準問題的研究
要衡量人口紅利的程度和人口紅利期限的長短,必須要解決人口紅利衡量的標準問題。現有文獻大都用理論撫養比、老齡化率、有效撫養比、社會撫養比等單指標作為計算人口紅利程度或水平的標準。理論撫養比是指一個國家被撫養人口與撫養人口的百分比值,可分為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和總撫養比,是用來計算人口紅利最簡單、最常用、最基本的指標。陳友華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為基準,將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和總撫養比是否分別低于30%、23%、53%確定為人口紅利存在與否的分水嶺。與陳友華不同,車士義建議以總撫養比和老齡化率兩個指標共同計算或衡量人口紅利的高低。以總撫養比50%為基礎條件,以老齡化率等于10%為分界線,將人口紅利分為“真正的人口紅利”和“虛假的人口紅利”兩個階段。王豐提出“有效生產者”和“有效消費者”的概念和計算方法,并利用“有效生產者”和“有效消費者”之比來衡量人口紅利。“有效生產者”和“有效消費者”這一對范疇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避開了就業或所謂剩余勞動力的問題,同時也考慮了不同年齡的被撫養人口存在不同消費需求的現實。陳濤是提出用“社會撫養比”計算人口紅利水平的學者。他認為“人口紅利”受人口規模、人口素質、就業結構、生產與消費模式等因素的影響,不同年齡的被撫養人口的消費需求不同,而且不同產業勞動力的撫養能力也不同,這就需要對不同的消費需求和不同的撫養能力進行標準化。據此,陳濤引入“標準消費人口”的概念,對不同年齡結構人口的消費狀況和不同產業的勞動人口的生產狀況進行統一,并將標準化后的撫養比稱為“社會撫養比”。
中國人口紅利持續期長短問題的研究
關于中國人口紅利持續期長短的問題,學術界存在悲觀派和樂觀派兩種對立的觀點。悲觀派認為,中國人口紅利持續的期限在20-40年之間,劉易斯拐點即將來臨,勞動力短缺即將出現。中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在近30年的時間內就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使我國的人口紅利來得早、去得快。
樂觀派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期非常漫長,我們沒有必要對“中國將出現人口負利”之類的問題杞人憂天。馬瀛通在將人口紅利的實質界定為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從不適應向適應轉變,逐齡進行更替乃至周期性更替的過程的基礎上,認為人口紅利會與日俱增,不可替代,是21世紀中國跨越式發展的動力。穆光宗在將廣義人口紅利的實質界定為人力資本的積累和人力資源的開發的基礎上,指出人口紅利與其說是有無問題,不如說是大小問題。由于廣義人口紅利的實質是人口創造財富的過程,因此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存在一個時期,有一個時間表的命題本身就是錯誤的。
人口紅利的區域應用研究
在人口紅利問題的分區域應用研究上,王承強、楊宏娟、何景熙、洪、田艷波分別研究了山東、遼寧、和云南等地區人口紅利的實現過程及其對區域經濟的增長作用。王承強根據瑞典1957年生命表的人口類型劃分標準,對山東省及其區域人口紅利進行了過程判斷。研究表明,山東省在1984年就已經進入了人口紅利期,比全國早了6年,將于2036年退出人口紅利期,比全國晚6年。楊宏娟的研究表明,遼寧1982年進入人口紅利期,1990年進入人口暴利階段,且直到2020年前均為人口暴利期,人口紅利將于2022年以后消失。何景熙預測了自治區未來30年的人口規模和結構的變動,預測數據顯示,近年來隨著婦女總和生育率的下降,正處在人口快速轉變之中,2010-2030年間,將出現勞動力適齡人口比例最大、社會總負擔比最輕的“人口紅利”期。洪發現云南人口機會窗口于2000年首次開啟,將于2035-2040年閉合,整體上比全國滯后十年。田艷波認為少數民族人口轉變的過程與全國相比存在著一定的特殊性,人口紅利期大致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較全國要晚5-20年時間。
研究評述與展望
雖然學術界對人口紅利的文獻較多,基本形成了研究框架,但總的來看,上述研究還剛剛起步。為了更好地認識、掌握和利用人口紅利,學術界至少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縱深層次的研究。
需要對人口紅利的本質做更權威的界定。盡管學者們從“機會”、“期限”、“源泉”、“過程”等不同的角度或側重點界定了人口紅利的本質,但似乎都沒有完全抓住該事物的本質特征,這就需要學術界繼續深入探討人口紅利的本質。
需要對人口紅利的計算標準做進一步的研究。不同學者計算人口紅利程度或水平的指標不統一,指標選用的非統一性導致了不同學者對我國人口紅利期限長短問題認識的非一致性。此外,學者們計算人口紅利水平運用的都是單一指標,這種簡單化處理限制了學術界對人口紅利水平衡量問題向縱深方向發展。因此,目前學術界急切需要構建一個權威化的人口紅利評價指標體系和預警指標體系。
需要從內部結構的解析入手,深入探討人口紅利的分類。人口紅利是由人口結構的演化導致的,而人口紅利內部本身也存在結構問題。不同數量、質量和結構下的人口紅利將具有不同的屬性特征。據此,能否將人口紅利分成人口數量紅利、人口質量紅利和人口結構紅利?人口結構紅利能否進一步分為人口性別結構紅利、人口城鄉結構紅利、人口產業結構紅利、人口區域結構紅利等等?筆者認為,這種嘗試是很有意義的。
需要探討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結構性問題。不同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外貿結構下的人口紅利應該是不相同的,這就需要我們研究不同經濟結構下的不同的人口紅利表現形式,以及隨之產生的不同的經濟增長途徑或方式。
參考文獻:
1.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12 (3)
2.于學軍.中國人口轉變與“戰略機遇期”[J].中國人口科學,2003(1)
3.陳友華.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數量界定、經驗觀察與理論思考[J].人口研究,2005
篇(2)
一、引言
人口因素是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我國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出生率迅速降低。僅用30多年的時間完成了發達國家需要100多年完成的人口結構轉變。安徽省的人口結構變化同樣經歷這樣一個過程,進入了勞動力供給充足,人口撫養比負擔較輕的時期,即人口紅利期。因此以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結合對人口紅利與安徽省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分析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國內外研究綜述
Bloom和Williamson(1998)在研究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及地區創造“東亞奇跡”時,發現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導致人口撫養比的下降,對經濟的增長起了很大的貢獻,從而首次提出了人口紅利這一概念。人口紅利的一個具體的定義便是人口結構變化過程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增加所帶來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從而給經濟的發展帶來一個促進作用。Mason和Birdall(2001)認為生育率的下降會帶動整個社會儲蓄率的上升,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大,將有利于人口紅利的形成從而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Mason和Lee(2004)進一步把人口紅利分為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并指出第一人口紅利是通過勞動力供給和降低人口撫養比來帶動經濟的增長,第二人口紅利則是通過提高社會儲蓄率和增加資本積累來推動經濟增長。
國內學者也對人口紅利進行了相關的研究。著名人口經濟學家田雪原早在1983年就預見性的提出應當充分利用我國人口撫養比下降的機會,帶動社會經濟發展。王德文等(2004)指出我們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人口紅利,并將人口撫養比作為一個變量加入到經濟增長因素分解模型當中,通過計算發現人口紅利的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比例超過25%。陳友華(2005)選擇瑞典1957年的生命表為標準人口,計算發現中國從1990年開始進入人口紅利期,這一時期將持續到2035年結束這和原新等(2006)的研究結果較相似。蔡昉(2008)認為人口紅利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中起著重要作用,人口紅利的實現必須通過一系列政策條件相配合。蔡昉(2010)解釋了人口轉變與二元經濟的關系,并指出增加國民收入、保持經濟增長是解決我國未富先老問題的關鍵。王金營,楊磊(2010)認為在過去的30多年里人口年齡結果變化所帶來的勞動力負擔下降對經濟的增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為了更好的利用人口紅利我們應當制定適當的勞動力就業政策來促使經濟更好的發展。
然而國內外學者研究的范圍大都在一個國家的范圍,默認該地區的人口不對外流動,從而忽略了人口流動對人口紅利的影響。因此對安徽省這樣一個勞動力輸入大省的人口紅利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將有助于彌補這一塊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三、人口紅利對安徽省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
(一)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動分析
人口紅利是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出現的,而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是人口轉變的基礎,因此對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變動的分析將有助于我們認識人口紅利的形成。
1970年以來安徽省人口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人口結構實習了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轉變。
數據來源:1995-2010年《安徽統計年鑒》
表1列出了1994-2009年的安徽省人口變動情況。一般認為出生率在15‰以下屬于低水平;在15‰-30‰之間屬于中等水平;在30‰以上屬于高水平。死亡率在10‰以下屬于低水平;在10‰-20‰之間屬于中等水平;在20‰以上屬于高水平。如表1所示大概可以判斷安徽省人口進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類型。這種人口轉變為安徽省人口紅利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二)安徽省人口撫養比變動分析
人口撫養比指總體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是衡量一個地區人口撫養負擔的重要指標。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安徽省人口撫養比也隨之發生變化。撫養比的高低影響社會勞動力的供給和總儲蓄率水平對人口紅利有重大的影響。
從表2可以看出,近年來安徽省撫養比總體上呈現出“一升兩降”的狀態,即老年撫養比上升,少兒撫養比和社會總撫養比下降。目前安徽省處于人口撫養比較低的時期,十分有利于人口紅利的形成。
(三) 勞動力投入對安徽省經濟增長作用分析
有關研究表明人口紅利主要通過勞動力供應對經濟的增長產生影響。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來考察勞動力投入對安徽省經濟增長的作用。
Y=A(t)LαKβμ
其中Y代表工業總產值,用安徽省生產總值表示;L為勞動投入,用從業人員數表示,K為資本投入,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表示;α是勞動力產出的彈性系數,β是資本產出的彈性系數,μ表示隨機干擾的影響,μ≤1。從這個模型看出,決定工業系統發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勞動力數、固定資產和綜合技術水平(包括經營管理水平、勞動力素質、引進先進技術等)。
令μ=1對上述式子兩邊取自然對數則有:
lnY=lnA+αlnL+βlnK
根據1986-2009年《安徽省統計年鑒》24年的數據,用Eviews5.0的普通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估算,經檢驗模型不存在自相關性,得到回歸模型如下:
LnY=-18.876+4.376Lnl+0.234Lnk
(-5.78) (5.43) (6.31)
其中R2=0.968 F=2898.891 D-W=2.541
由此可知模型的擬合優度和顯著性都比較高。D-W值為2.541則說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關。進一步檢驗得知方程也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和異方差。則表明此模型有較好的說服力。有上述檢驗可知,勞動力產出的彈性系數為4.376,即在1986-2009年勞動力投入每增加1%,GDP增加4.376%。可見勞動力投入對安徽省經濟增長具有重大的影響。
四、結論與建議
(一)加強養老保險市場建設,完善社會養老體系。
安徽省的人口轉變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人口紅利,但隨著老年人口數量的不斷增加,老年人口撫養比不斷加重,將會削弱人口紅利。因此必須加快完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加大地方性財政投入,建立起較為完善的養老保險體系。政府要進一步增加老年人的醫療保障投入,擴大醫療保障的范圍,優先滿足老年群體的醫療服務。同時要強化政府主導的作用,把社會養老工作擺在重要位置,完善相應的政策支持體系,有效地支持養老保障體系的運行。
(二)加強促進就業的力度。
勞動力的供給程度決定人口紅利的實現程度。因此大力發展勞動力市場建設,促進就業對安徽省人口紅利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加大就業資金的投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制定相關的政策為社會創造良好的就業環境。同時要根據實際情況,加大待業人員和就業人員的培訓。也要考慮不同就業人員的情況,采取不同的就業政策。鼓勵大學生適當降低就業要求,積極參與社會經濟活動。
(三)加強人力資源建設。
對人口紅利的利用不能只考慮勞動年齡的絕對數量,更要注意提高勞動力的質量,這樣才能充分利用當下的人口紅利。因此首先要加強人力資源建設,提高勞動力的人口素質將有助于延長人口紅利期,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率進而推動安徽省經濟的發展。同時要優先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推進素質教育。最后要率先建立老年人才的開發和利用機制。根據經濟發展和社會的需要加大老年人才開發力度,支持退休的專家參與經濟建設。
參考文獻:
[1]王德文、蔡昉、張學輝.人口轉變的儲蓄效應和增長效應[J]. 人口研究,2004(5)
[2]陳友華.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數量界定、經驗觀察與理論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篇(3)
一、人口紅利的定義與指標刻畫
“人口紅利”這一概念,最早是由國外經濟學家在研究東亞“經濟奇跡”時提出的。關于人口紅利,Mason and Lee(2004)提出了兩個人口紅利的說法,分為“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
“第一人口紅利”是指人口出生率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提高,勞動力供給增加,表現出人口總體負擔相對較輕的局面。
對于“第二人口紅利”的說法,即是在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的過程中,作為理性的個人、家庭和政府,在生命周期假理論說下,其個人行為、家庭行為和政府公共政策的選擇將針對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會對預期的產出和消費做出合理的安排。在人口轉變的特定階段,由于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不斷提高,理將導致國民儲蓄提高和資本供給增加,這對經濟增長起到較大的推動作用,他們將其稱為“第二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刻畫指標很多,國際上統一用勞動力負擔來刻畫人口紅利,相對于勞動力撫養負擔,還有一個勞動力經濟負擔的概念,這是由于不同年齡段的人口消費水平的差異比較大,勞動力經濟負擔大致反映出了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相對于勞動力人口的消費情況,這能夠更好的測算不同年齡階段人口的社會消費結構以及產生的經濟效用。然而實際上,撫養負擔其實并不僅僅體現在消費上的物質供給和經濟支撐,同時也體現在精神以及情感上的支持和慰藉。因此,通過撫養的數量比即勞動力撫養負擔更能反映真實的負擔狀況。
因此本文中的人口紅利指標即用撫養負擔來刻畫,而撫養負擔又存在理論撫養負擔和實際撫養負擔。二者并不等同,差距在于勞動參與率,若全部的勞動力年齡人口都參與到經濟活動中,理論撫養負擔與實際撫養負擔保持一致,一般情況下,實際撫養負擔要高于理論撫養負擔。
然而,需要指出是,本文將采用理論的撫養負擔,而非實際撫養負擔,由于我國的勞動力市場非市場化以及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官方勞動力就業統計范圍僅限于城鎮勞動力,而忽略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并且具體到勞動力年齡階段的勞動參與率較難,即使估計的數據也與實際差異較大,很難反映真實情況,因此,就用勞動力年齡人口來代替勞動力就業人口。
二、人口紅利的特征
為了對人口紅利進行比較充分的認識,研究人口紅利的特征是特別重要的,對于一般文獻中提到的三點:高勞動參與率、低撫養比、高儲蓄率。這只是從表面上一些簡單的特征表述,下面詳述人口紅利的具體特征。
(一)差異性
人口紅利差異性包括地區差異、進入時間差異、紅利持續時間的差異、結束時間差異、結構差異等。
(二)不平衡性
一是人口紅利的區域不平衡,人口流動使得我國東中西部的人口紅利存在差距。
二是人口紅利的城鄉不平衡,城鎮化也在影響著我國人口紅利的城鄉差距。
三是人口紅利持續時間的不平衡性,相對而言,東部人口紅利持續時間因中西部的勞動力人口流入被延長了,城鎮人口紅利持續時間因農村勞動力的流入被延長了。
(三)時效性
人口紅利僅僅只是勞動力資源在一定時空條件下的配置結果,不是永久性的經濟增長源泉。我國的人口紅利是一個短暫而又一次性的過程,這種人口紅利不可儲存,必須即時存在、即時消費。
(四)成本性
因為人口紅利消逝后的社會面臨的是人口負債,人口紅利所創造的經濟發展機遇是迎接人口老齡化的關鍵。因此,必須充分利用當前的人口紅利,通過經濟社會的不斷積累來應對人口負債階段的各種挑戰。
(五)條件性
人口年齡結構轉變帶來的勞動力比重較大只是為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充要條件。人口紅利只是一種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一種人口年齡優勢,人口紅利不等于經濟紅利,也就是說,人口轉變雖然帶來人口紅利,但是并不必然促進經濟增長。因此,人口紅利的兌現具有條件性。
三、我國人口紅利的分析及預測
隨著人口結構的轉變,我國人口紅利正在發生著變化,《聯合國人口展望》預計到201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停止增長,隨后將會慢慢減少。此外,盡管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上升,但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使得老齡化趨勢初現。根據此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10年滿15周歲到60周歲之間的勞動年齡人口是9.2億, 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約為1.65億,2020年將增加到2.4億,2030年時則高達3.4億,屆時約占我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根據目前的人口紅利趨勢,很有必要對我國未來人口紅利進行預測、分析,下面是采用聯合國發展報告中的數據所作出的預測分析。在1950年到2050年期間,我國的勞動力總撫養比的變化表現出上下波動的形態,其中有兩大拐點:一是1965年附近的總撫養比達到最高點,另一個點是2013年左右的最低點,自從2013年起,總撫養比因人口老齡化而不斷的增加,盡管人口紅利在2013年左右消失,但仍有持續近30年的平衡期,在將來的這一時期,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但人口負債并不顯著,也是一個應對于人口負債和老齡化調整的重要“緩沖期”,仍處于一個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時期。
從1950-1990年,總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均呈現出“倒U”型軌跡,在這一階段,老年撫養比一直穩定的保持在8%左右,1990年之后,少兒撫養比在不斷的下降,直到2030年左右達到谷值,1990年到2050年,總撫養比呈現出“U”型軌跡,在2000年,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2015年老齡化加速,促使老年撫養比迅速增加,負擔迅速加重。在1950-2050的一百年里,總撫養比的變化在1950-1990年期間主要因為少兒撫養比的變化,而在1990-2050年期間主要由老年撫養比變化來解釋。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的“交叉點”發生在2030年左右,即從2030年,老年撫養比歷史性超過少兒撫養比,開始全面的影響我國的經濟社會。
四、政策建議
借鑒國際經驗,在面對老年負擔加重的挑戰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有所不同,發達國家采用了移民以及延長退休年齡等政策,而有些發展我國家強調了勞動年齡人口積極參與經濟活動,為此采取了加強教育和培訓、勞動力市場改革等措施。我國應該根據自身情況,采取合適的政策,然而擺在我國經濟發展面前的兩個重要問題就是:一是如何盡可能充分利用即將消失殆盡的人口紅利;二是如何利用人口紅利積累的經濟社會基礎應對未來人口負債的挑戰。人口紅利優勢轉變、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協調發展;勞動力全流通與充分參與;提高老年市場參與戰略;集中型撫養和贍養戰略等等。(作者單位:南京財經大學)
篇(4)
一、我國“人口紅利”問題的由來
我國學者多把“人口紅利”定義為“一個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而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因為從人口對于經濟的作用來看,人在成年之前是需要投資物資來照看的,因此要消耗一定的人力和物力。人在成年之后就可以具備一個成熟勞動力所擁有的技能,便可以對經濟的發展有定的貢獻。在退休之后,由于身體機能的下降,則不具備一個正常勞動力所具備的條件,也就不能給經濟發展帶來動力。因此,若一個社會的青壯年在人口中的比重相對來說較高的話,就會對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就會形成相應的“人口紅利”。但是這和一國的經濟發展的結構是分不開的,一般來說,人口紅利和經濟發展的二元經濟結構是分不開的。因為在二元經濟的第一階段,由于傳統部門可以向工業部門提供幾乎無限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的工資完全取決于維持生活最低費用的標準,因而勞動力的價格很是低廉。而“人口紅利”就會出現在這一階段。但是當這一階段完成后,勞動力幾乎全部向工業部門轉移以后,就會出現所謂的“劉易斯拐點”,從這一點以后,由于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其的工資水平也就開始上漲。因此,“人口紅利”也就逐漸消失。我國由于處于二元經濟的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的過渡,出現了工資水平開始不斷上漲的現象,這也許意味著我國的經濟的劉易斯拐點就要出現,而就會相應的出現一系列問題,對于我國來說就是“人口紅利”消失后的問題。
二、我國“人口紅利”是否要開始消失
近幾年來,由于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我國的勞動力的工資也不斷的上漲,就有我國的“人口紅利”即將消失,劉易斯拐點即將來臨的說法。現在分析一下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首先,我國的經濟現在正處于二元經濟的轉型期間,面臨著勞動力即將從傳統部門到工業部門轉移完畢的境地。因此,我國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特別是沿海地區表現尤為明顯。最近幾年,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區出現的“民工荒”,就充分的說明了這一問題,因而,我國經下來要做的工作是解決好“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問題,做好經濟的轉型發展。
三、應對“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措施
在面對“人口紅利”即將消失的問題時,我們可以做一下幾點來改善我國的就業狀況:
(一)實施更加合理的產業政策,在使用勞動力的方法上大膽創新
要保證非技術類的勞動力得到充分的利用,不要過早的進入勞動力稀缺的狀態。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占了人口的50%以上,因此我國的勞動力轉移應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劉易斯拐點所帶來的現象,不會在短時間內很充分的暴露出來,應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如何有效利用勞動力是極為重要的。可以提高工人的勞動效率,還可以從生產方法和技術以及生產設備做一定的提高。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劉易斯拐點的發生進程,從而可以爭取更多的時間,實現人口素質的提高以及經濟轉型發展,從單純的依靠廉價勞動力帶動經濟的發展,到高科技人才引領經濟。
(二)對農民工進行培訓,提高其技能,但是要特別注意對先進技術的教授
首先,要做好技能培訓,特別是對高中后沒有繼續進行高等素質教育的人要進行一定的技能培訓,因為他們已經是成熟的勞動力。這意味著我國需要繼續興建高等職業院校,以滿足對這部分人群的教育需要;其次,要對下崗之后還未再就業的職工以及返鄉農民工的做好再就業培訓工作,幫做其找到工作。再就業的培訓,主要是對現今需要的技術的教授,讓其重新具備一個勞動力的資格。除此之外,還應該當下政府對再就業的一系列政策的培訓,讓其明白自身所有的一些優惠條件;再次,要對我國的教育體制進行改革,縮小農村和城市的教學成果的差別,使所有人都有公平受教育的機會,這樣才能提高我國人口的整體素質。總之,就是要提高現有勞動力的整體素質,不再是考勞動力的數量,而是靠勞動力的質量來吸引投資者。
(三)要改善雇主與雇員之間的關系,以及農民工進城之后待遇
首先,在雇主與雇員之間建立一種更牢固的關系。因為在進入劉易斯拐點之后,勞動力不像原來那樣似乎是無限供給的,變成了勞動力稀缺,因此,雇傭方從原來的有利地位變到了不利地位,其必須要對其所擁有的勞動力給予激勵,這種激勵不僅僅是物質上的,還有精神上的,這樣才能建立和諧的雇傭關系;其次,對于農民工進城,要給予充分的合理的待遇。長期以來,我國就有歧視進城的農民工的傳統,因此農民工在城里的就業環境就相對來說比較的差,他們子女在城里的學習環境也相對來說不是太好,因此我國政府應該出臺相關的政策以幫助其公平,平等的就業。
篇(5)
中圖分類號:C92-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10-0010-04
據統計,2000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達到8 811萬,占全國總人口比重的6.96%。按照國際標準,中國基本進入老齡化社會。而2004年,在我國的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又持續出現“民工荒”現象。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無限供給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將受到限制。中國真的失去“人口紅利”了嗎?從人口增長的估算看,回答是否定的。中國勞動力增長率的下降最早也應當是5年以后的事情,更何況多余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以及教育的投入可以減緩勞動力增長速度下滑帶來的負面效應。有專家預測,中國今后15年仍處于收取人口紅利的黃金時期。關鍵是我們如何挖掘人口紅利的巨大效應,使我國巨大的人口壓力轉變成人力資源優勢,從而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
一、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
所謂“人口紅利”,是指在一個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從而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換句話說,人口紅利就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年齡結構,即形成一個“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在此階段,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儲蓄和投資不斷增長,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從而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有利。
上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創造了所謂的“東亞奇跡”,實現了經濟的騰飛。而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人口轉變帶來的有利時機正是東亞經濟增長出現奇跡的重要原因之一。東亞經濟起飛發生在人口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轉變階段,這種積極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為經濟增長帶來了一個獲得“紅利”的“機會之窗”。在1970―1995年期間,東亞經濟實現了年均6.1%的人均GDP增長率,高于其穩態增長率(注:穩態增長是指處于均衡狀態的經濟增長,可參見Barro, R.and Sala-i-Martin(1995),Ewnomic Growth,MacGrall Hill.)4.1個百分點,據估算,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為1/4~1/3,而在東亞奇跡(超出穩態部分即4.1個百分點)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達1/3~1/2。
同樣,人口紅利對于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第一,在具備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這一潛在人口優勢的條件下,勞動的參與率和就業率均保持較高的水平,這就意味著一個人口結構產生的充足勞動力資源得到了較好的利用。改革期間勞動密集型產業迅速擴張,得以大規模吸納就業,從而把人口年齡結構優勢轉化為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有研究顯示,在1982―2000年期間,我國人口紅利對GDP增長的貢獻比率高達26.8%,或者說,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有1/4以上是靠大量的廉價的勞動力支撐的。第二,經濟活動人口比例高且就業率較高,使得社會儲蓄總量大,經濟活動中的剩余總量也大,這就使得中國在改革期間達到較高的儲蓄率,社會財富不斷增加。用每年固定資產形成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表示,在整個改革期間我國的儲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1993年達最高44%。我們應該看到,一方面,這得益于改革開放所形成的以市場化為核心的良好的制度環境,使得中國經濟能以高速增長。在促進就業的同時,大幅度提高了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整體人口撫養比的下降,減輕了社會的撫養負擔,因而提高了人口的生產性,人口紅利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有資料顯示,在過去20多年的中國經濟增速中,有28%來自于物質資本,24%來自于勞動力的數量,24%來自勞動力的質量,也就是人口素質的提高,21%來自人口流動,還有3%是無名因素,如管理水平等。由此可見,人口因素對于經濟增長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
二、我國人口紅利期的特點
由于人口紅利是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形成的,因而人口轉變過程不同,人口紅利的特點也就不同。我國的人口轉變過程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初,結束于90年代末,用了25~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從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轉變,而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完成同樣的人口轉變過程卻經歷了近百年的時間。然而,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的這一人口轉變,是在社會經濟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雙重作用下,特別是以后者效果為主的情況下實現的。相對來說,它不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而是通過強制性生育政策使我國人口生育率在短期內快速、大幅度下降,從而過早地迎來了人口紅利期。而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的人口轉變過程是在個體生育意愿主導生育行為的基礎上完成的,因此,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是個緩慢、漸變的過程。
而研究表明,人口紅利的持續時間主要取決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勞動力比例越高,人口紅利持續的時間就相對較短,反之亦然。因此,雖然我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但生育水平的急速下降卻使得中國的人口紅利來得早也去得快,屬于典型的轉變快、持續短的模式。根據人口學原理,一般我們將人口撫養系數或人口負擔系數(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百分比)在50%以下的時期稱為“人口之窗”或“人口紅利期”。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人口紅利期應始于1990年,結束于2030年,前后持續時間大約為40年,而到 2010年左右,中國的人口負擔系數將降到最低。也就是說人口負擔系數呈現出先降后升的倒“U”型趨勢,即老年人口比重雖然不斷攀升,但勞動年齡人口占整個人口的比重仍處于上升的趨勢,而到2010年前后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將達到最高。從這以后,該比重逐漸下降。直到2030年,中國完全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期結束。這也是大多數人口學家所持有的主流觀點。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人口負擔系數只代表理論負擔比,而非實際負擔比。真正意義上的負擔系數應是不在業人口與在業人口的比例關系,而不是根據年齡劃分。因此,他們認為中國的人口之窗應始于1980年左右,2020年即將關閉。但不管哪種觀點,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它就是一個短暫而又一次性的過程。因此,如何把握這短暫而又潛在的歷史機遇,將人口紅利繼續轉化為現實的、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在當代中國就顯得尤為重要。
另外,對大多數已經完成人口轉變的發達國家來說,人口轉變過程與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幾乎是同步的。因而當出現勞動力供給減少,人口老齡化的情況時,在這些國家恰好出現資本替代勞動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變化,即產業結構全面升級,技術結構轉向勞動節約型和資本密集型。而我國是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通過強制生育政策提早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因而生育率的下降是遠遠超前于社會經濟發展步伐的。也就是說,我國是在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還沒有相應變化的基礎上,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因而也就過早地出現了勞動力供給減少現象,也就意味著中國即將失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經濟增長也就有可能喪失可持續性。所以說,中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導致了“未富先老”,產生了其他國家未曾遇到的許多問題,構成了特殊的政策挑戰。
三、當前妨礙人口紅利發揮效應的主要因素
雖然人口紅利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我國人口狀況的特殊性,即人口年齡結構相對有利于經濟增長,但人口的基數過于龐大,使得人口紅利的兌現在某些方面受到制約。
(一)我國的就業形勢十分嚴峻,并且在未來可能會進一步惡化,這就造成勞動年齡人口就業的不充分。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主要表現為:(1)20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經濟增長方式不合時宜的轉變,使得GDP對就業的拉動減少;另一方面,由于產業結構調整,造成大批城鎮職工下崗,失業現象日益嚴重。(2)仍然有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等待向非農產業轉移。(3)每年有數百萬到上千萬新增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在就業機會不充足的條件下,這種就業壓力便轉化為失業率的逐年上升。
以定義狹窄的城鎮失業率為例,1990年城鎮失業率為2.2%,2000年提高到3.1%,2001年上升為3.6%,2002年上升為4%,而2003年達歷史新高4.3%,雖然4.3%這一數字從表面上看似乎并不代表著很高的失業水平,但從其連續多年攀升的事實來看,當前的失業問題還是十分嚴峻的。另外,許多勞動年齡人口由于長期處于失業狀態下,可能就會因此喪失信心而退出勞動力市場,勢必會造成勞動參與率的下降。這樣一來,就會有相當一部分勞動年齡人口成為社會需要負擔、撫養的人口,而這部分人卻不能創造財富,因而造成了勞動力資源的極大浪費。
(二)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制約著人口紅利的實現程度。從勞動年齡人口的分布看,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農村地區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大量的農村勞動力人群從土地中走出來,走向城市,走向發達地區。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農民工”占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46.5%,其中第二產業占56.7%,建筑行業占80%。因此說,中國收獲人口紅利的程度應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發展程度。但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這一事實決定著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國首次公布的“中國教育與人口資源問題報告”顯示,農村勞動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33年,而城市為10.20年。另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預測,目前中國至少有1.2億農村人口流入城鎮,其中1/3~1/4為15~25歲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業,但得不到應用的教育與培訓。低素質、低成本的勞動力同時決定了創造力也相對較低。比如,制造業1小時勞動力的價格,美國是30美元,中國大約是2美元,而美國的勞動率也比中國高10~20倍。可見,提高勞動力素質,提高勞動力成本,中國才能更好地兌現人口紅利。
(三)當前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因素仍然存在,使得人口紅利效應的發揮受到影響。根據M.P.托達羅的城鄉人口流動模型,只有在遷移的預期收入超過預期成本時,農民才會選擇進城。一般來說,農民進城的收益包括經濟收益、技能收益以及文化收益。農民進城的成本包括遷移成本、機會成本(即農民從事非農產業的活動而放棄務農收入)、高于農村的城市生活費用以及心理成本。而現實是,近年來農民進城收益并無提高,進城成本卻明顯上漲,因而削減了農民進城的愿望。這也是在免除農業稅、給予種糧補貼(即務農收益相對提高)后,我國部分地區一度出現“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成為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另一大因素。其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成為各種歧視性政策安排的載體,提高了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妨礙了他們流入城鎮后的順利就業。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市場歧視制度,當地勞動者和外地勞動者工資收入存在差異,同工不同酬;用戶籍限制外來勞動力就業范圍,保護本地勞動力優先就業;失業、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與戶籍掛鉤,不覆蓋外來勞動力;就業相關的政府服務機構只為本地勞動力提供服務等。因此,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過程并不十分順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勞動力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影響到人口紅利的兌現。
四、我國人口紅利的實現途徑和具體措施
從分析中,我們知道,未來10―15年是我國人口紅利最為豐富的時期,但人口年齡結構的改變并不會自動地導致經濟的快速增長,必須與適宜的政策、體制以及是否充分就業相聯系。因此,我們必須牢牢把握這短暫而又潛在的機遇,最大限度地擴大就業,最大化地發揮人口紅利的巨大效應,提高勞動力資源利用效率,從而實現經濟的快速持續增長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一)采取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實現充分就業
解決人口紅利兌現問題的關鍵當然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我國應采取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選擇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圍繞擴大就業采取多種有效措施。比如,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中小企業和私人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開放服務業市場,擴大就業容量;取消對勞動力流動的各種限制,培育勞動力市場等等。通過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從而使我國的失業率降到最低,實現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的雙重目標。另外,在具體實施就業優先原則的過程中,客觀上要求我們做到,有利于降低失業率的調控政策要優先于其他政策;有利于促進就業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優先其他財政支出給予安排;就業崗位的增加要優先于社會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發展要優先于其他要素市場;勞動者利益要適度地優先于資本的利益等等。通過充分就業的實現,將為我國目前這樣一個相對年輕和豐富的勞動力大軍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二)消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實現城鄉勞動力的合理流動
眾所周知,未來城市勞動力的提供,必須依賴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而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卻成為限制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因此,只有逐步取消這種排他性的政策措施,才能保證農村剩余勞動力暢通無阻地轉移出來,才能減少農村中勞動力的沉淀。具體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在就業機會上消除戶籍對就業范圍的限制,提供給外來勞動力公平的就業機會;要根據崗位的需要,交由勞動力市場來選擇;在待遇上,規范目前混亂的非正規勞動力市場,保護外來勞動力的合法經濟權益等等。同時,還要加強管理和引導,做到農村勞動力的有序流動。只有這樣,才會使得勞動力資源得以優化配置。這不僅有助于保證持續的勞動力供給,而且還會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直接貢獻,經濟增長速度會更高。世界銀行一項模擬表明,在今后能把農業勞動力轉移出1%、5%、10%的假設下,全部GDP將分別提高0.7,3.3和6.4個百分點。(注:世界銀行(2004),《全國產品和要素市場分割:經濟成本和政策建設》,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備忘錄。)
(三)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提高勞動生產率
由于歷史和國情的原因,中國走的是一條依靠農業積累和廉價勞動力推動的工業化道路。從短期看,勞動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經濟的發展,但從長期看,勞動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勞動力素質和低勞動生產率的反映,它無疑將阻礙經濟的發展。因此,對于中國來說,要想在未來獲取更多的人口紅利并不是體現在勞動力數量上的優勢,而是要通過人力資本存量素質的提高來形成一個更具有報酬遞增,更加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源泉。也就是說,通過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進一步提高勞動力成本。而大力發展教育是提高勞動力素質的一條重要途徑,尤其是發展農村地區的九年義務教育。此外,還應積極發展職業技術教育,開展適應勞動力市場需求的專業技能培訓、文化培訓、職業教育等等,從而使我國農業勞動力在進入非農產業就業之前,就獲得必要的職業技術訓練,增加了勞動供給的有效性,進一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我個人認為,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內,就地區而言,教育投入的重點應放在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就教育結構和人才培養結構而言,應加快擴大和提高職業技術教育的規模和水平。通過普遍提高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術(技能)水平,使我國人口紅利效應最大化。
(四)做實個人賬戶,建立可持續的養老保障體系
眾所周知,“未富先老”是中國老齡化的最大特點,老年人口絕對數和相對數的增加,將使社會負擔日益加重,社會保障資源面臨巨大壓力。而且由于農村流動人口數量巨大,必然會引起未來農村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這也是中國老齡化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如何進一步完善城鎮養老保障體系,如何建立一套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適合農村特點的保障體系在當前就顯得尤為重要。
我國從1997年起實行養老保障制度改革,旨在形成一個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體系。但是,由于個人賬戶存在“空帳”問題和社會統籌基金不足,使得養老保險絕大部分用于當年養老金發放,實際積累小于職工個人賬戶記賬額。這就造成改革后養老保障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個人賬戶只是名義上的,實際上整個養老保障體系仍然是百分之百的現收現付制。而根據國際經驗,支撐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障體系需要以相對年輕的人口結構,有效率的稅收體系,有效且安全的基金管理和治理機制為條件。目前,后兩個條件在我國尚不完全具備,而從第一條件看,雖然目前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仍然較大,但社會的養老負擔已經大幅度上升。實際上,如果沒有財政的補貼和擠用個人賬戶資金,養老統籌基金每年支出大于收入的數額都是巨大的,長期累積下去則會形成一個巨額缺口,現收現付制度將難以為繼。目前養老統籌的覆蓋率也很低,2002年,離退休人員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比例為84.1%,而城鎮就業人員參加比例僅為44.9%。
因此,應對老齡化挑戰,就必須選擇可持續的養老保障模式。以人口結構變化方向為依據,做實個人賬戶,實現完全的個人積累,就是一種具備可持續的養老保障制度。而從時間的緊迫上說,現在就應該從現收現付養老保障制度向完全積累制度過渡。為了支撐這個過渡,還需要把農村轉移勞動力納入新的保障體系,提高當前保障基金的繳費水平和社會供養“中人”的能力,從而實現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穩過渡。政策模擬表明,到2020年,每一種政策情形具有不同的社會養老負擔。如果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城鎮養老保障體系,同時,實行完全的個人積累新體制,到2020年,社會養老負擔率最低,只有25.3%,比不進行這兩項改革的情形低大約19個百分點。
參考文獻:
[1] 蔡.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兼論充分就業如何促進經濟增長[J].人口研究,2004,(2).
[2] 朱洪,郭亞模.淺析中國人口紅利及其兌現途徑[J].西北人口,2007,(2).
[3] 汪小勤,汪紅梅.“人口紅利”效應與中國經濟增長[J].經濟學家,2007,(11).
[4] 蔡,毛美艷.“未富先老”與勞動力短缺[J].開放導報,2006,(2).
Discussing about the Function of the Population Bonus to the Economy Continuence Growth
WANG Hong-mei
篇(6)
中圖分類號 F06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7)04-0035-05
隨著科學發展觀的進一步落實,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城市就業壓力將更加嚴重,中國就業壓力將進入新的高峰期,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失業與環保、社會穩定、產業結構調整等一系列問題以更加復雜的方式交織在一起,對改革、穩定和發展形成巨大壓力。針對這一系列問題,以張坤為代表的學者率先提出中國經濟存在“壓縮型”特征[1],這種特點表現在經濟、社會、人文等各個層面,對中國人口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課題。
1 壓縮型工業化社會的一般特征
聯合國開發署環境專家D?O?Conner指出,早期發達國家經歷了幾個世紀完成的工業化,在東亞國家卻只花了數十年,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顯著縮短,這種縮短的工業化被有關專家稱為“壓縮型工業化”[1]。壓縮型經濟社會典型特征是工業化進程超速發展,產業結構急劇轉變,就業矛盾突出,資源環境問題復雜。
1.1 工業實行“跨越式”發展,產業結構變動幅度大
工業的快速崛起是“壓縮型”工業化社會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現在工業突然而快速地替代農業,與“非壓縮型”工業化國家相比,缺乏自然成熟的過程。如:英國的工業革命自18世紀開始,到 21世紀仍處于工業信息化階段,而工業后進國[2]則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就完成了由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社會的轉型。如韓國1965年的GDP中工業產值的比重為25%,1990年已迅速上升到了45%,同期農業部門在GDP中的比值從39%下降到9%;我國自50年代開始工業化,到2005年,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從20.9%上升到47.3%,與此同時,農業總產值在GDP中的比重從50%左右下降到12.4%
1.2 人口膨脹與結構性失業并存
工業發展初期,經濟快速增長和對勞動力的需求造成人口出生率急劇上升,隨著世界工業朝著自動化、信息化方向的發展,工業產業對簡單勞動力的需求下降,而巨大的人口基數使勞動力的供給增加,使就業與失業問題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以我國為例,從1952-1995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都超過10‰,總人口從57 482萬人激增到130 756萬人(2005年),人口數量的迅速增加導致就業問題出現。從“九五”期間開始,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出現失衡,下崗失業人口大幅上升,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進入“十五”,就業與失業問題更為突出,不僅總量供求失衡,而且結構失衡。
1.3 人口增長結構演變歷程縮短
從東亞人口發展史上看,后進工業國家的人口結構變化(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所經歷的時間僅為發達國家的1/3。目前,我國已經進入一個低生育階段,標志著我國用不到30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經過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的過程。根據聯合國(2002)預測[3],65歲及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例從10%增至20%,各國所用年數為:中國20年(2017-2037);日本23年(1984-2007):德國61年(1951-2012):美國57年(1978-2028)。
2 壓縮型工業社會的“人口紅利”特點
2.1 “人口紅利型”經濟期的縮短
發達工業化國家“人口紅利”期出現的時間與工業化進程大致相同,持續時間為100年左右。由于后進工業國家經濟增長“追趕效應”作用,人口急劇膨脹,“人口紅利”期迅速到來,持續時間縮短。以我國為例,由于政策和社會因素,在經歷20世紀50~60年代生育高峰期后,從80年代初期開始,我國進入了“人口紅利期”,“人口紅利”期最多持續60年(見表1),而以我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在60年內完成工業化過程尚不可知。人口撫養系數[5]在短期內趕超發達工業國家。如在20世紀5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撫養系數比為0.7~0.8,到2000年,撫養系數比降低到0.6左右,同期發達國家人口撫養系數比僅下降了0.039,基本穩定在0.55左右。人口結構的黃金時期也被“縮短”,意味著勞動力資源減少,經濟發展必定受阻。
2.2 “壓縮型”工業化與“人口紅利”期的交織
“壓縮型”工業化帶來的人口老齡化負效應將使社會總儲蓄開始減少,繼而總投資下降,通過乘數作用影響經濟持續發展,同時,人口撫養比上升、勞動力資源開始減少、日益龐大的養老金使政府開支增加。
顯然進入老齡化社會需要一定的“社會積蓄”才能支付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費用”。因此,經過充分工業發展和財富積累的發達國家在進入老齡化社會時都較為富裕,如英國等發達國家從成年型社會向老年型社會轉變用了80年,同期人均CDP為5 000~10 000美元,而后進工業化國家完成這種轉變只用了發達國家1/3的時間,我國完成這種轉變用了大約20年,人均CDP只有1 000美元左右。這種“未富先老”正是“壓縮型”工業化國家所獨有的。
工業化后進國家的“追趕效應”和“結構效應”使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節奏快、社會轉型幅度大、經濟畸形發展,致使在“人口紅利”期內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獲得“人口紅利”,相反卻出現了“壓縮型”綜合性的問題:自然新增勞動力+城鎮失業勞動力+城鎮化帶來的農業勞動力,與產業結構改變、城鎮化和因過快工業化導致的制度不完善等問題交織在一起,形成后進工業化國家獨特的人口特點,如果不及時采取相應的措施,“人口紅利”將迅速轉變為“人口負擔”。
2.3 人口“紅利”中存在泡沫現象
具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只是獲取“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社會要享有“紅利”還需要與本國勞動力資源相匹配適合的制度環境、政策措施、人文環境和足夠的工作崗位等,這些條件和“人口紅利”一起構成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源泉。
大多數后進工業化國家為了盡早獲得“人口紅利”,在工業化起步階段鼓勵生育,如戰后日本人口在1947-1949年出現了持續三年的生育高峰期。這三年共出生約806萬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3.2%猛增至33%~34.3%,我國在1952年人口出生率高達37%。同時各國政府大力發展教育,1990年,日本大學毛入學率為29.6%,2003年大學毛入學率達到了47.7%,同期韓國大學毛入學率從386%上升到77.6%,新加坡從18.6%上升到48.3%,中國從3.0%上升到7.5%[6],到2005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9%,但當我們考察教育科研經費的投入時卻發現,從1990-2005年,盡管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由569億元增加到3 951.59億元,增長了5倍多,但是財政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全國教育經費占GDP比重從2002年最高點3.32%下降到2005年的2.16%,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教育投入水平,也低于發展中國家教育投入占GDP 4%的水平,這種急于求成的教育發展模式導致了教育質量的低下和教育層次的單一化。同時,由于后進工業國急于實現產業現代化,是知識技術引進的主要國家,急需技術創新,導致對高素質人力資本的需求,而本土產業在國際產業鏈中所處的地位要求實用性中檔人才,這種多樣化的需求與本國單一的人力資源素質不相匹配,導致大部分勞動力資源沒有形成與本國經濟相適應的人力資本,出現了“人口紅利”泡沫。
2.4 長期非自愿失業人口的存在使實際撫養系數高于理論數據
實際撫養系數計算公式中分子為0~15歲幼兒和65歲以上老人,該公式暗含的前提條件是充分就業。只有當社會自然失業率低于6%時,理論撫養系數才與實際相符。但當大量失業勞動力存在時,被撫養人口就不僅僅限于少兒和老人了。另一方面,后進工業化國家普遍存在出生缺陷人口居高不下的問題,目前,我國每年有80萬~120萬的出生缺陷嬰兒,15年后,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先天性缺陷人口也要從系數公式的分母中扣除,這時實際撫養系數往往要高于理論撫養系數(見表2)。
3 人口紅利壓縮的后果―大量持續性失業的經濟學分析
人口基數大,勞動力資源豐富正是獲取人口紅利必不可少的條件,它可以通過生產和消費行為為經濟增長提供不竭的動力,因此,人口基數大不應該是導致失業的直接原因,只有當它同不合適的產業結構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才會出現勞動力供大于求現象。孤立地判斷人口和產業結構是否合理是不科學的,只有將他們納入一個系統之內來考察,這樣的判斷才有意義。由于人口總量是既定現實,界定人口與產業是否適應就涉及到重新判斷發展中國家現行產業是否適應人口的問題。
以我國為例,我國屬于壓縮型工業化國家,產業結構在50年里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從農業社會步入工業化、信息化社會(這種轉變是部分和不均衡的)只用了幾十年時間[8],就業形勢也相應發生變化,其中最顯著的就是經過一個短期的就業高峰,從1997年開始失業率開始進入風險區,并一直持續居高不下。對這個問題本文的理解是現行產業結構和我國的人口特征不相適應。
3.1 現代化的產業結構要求與勞動力現代科學素質[9]普遍低下不相適應
在國際產業自動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隨著國際產業梯度轉移,后進工業國家也順應潮流,大力發展自動化、信息化工業,一方面提高了本國資本和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顯示出后進工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后進工業化國家處于國際產業轉移的低端,勞動力素質低下,基本上沒有能力為本國要求現代化的企業提供必須的高技術產品,勞動力處于閑置狀態,沒有發揮生產,相反,對高科技產品的需求和大量人口的存在為發達國家的生產性產品和消費性產品提供了市場。因此,就業壓力、人口紅利期縮短、人口泡沫等問題從表面上看是勞動力供大于求,總量失衡,實際上是“趕超型”工業化過程中,整體產業結構升級太快、太陡,缺乏相應的人力資源支撐造成的。
3.2 生產性消費的盲目跟進
在自動化、資本化、信息化的全球性的呼聲中,大部分學者一致推崇通過技術和資本投入帶動經濟增長,于是幾乎各行各業開始千方百計地爭取項目、更新設備,期望在資金有限的條件下,通過解雇員工、增加投入來達到改資本廣化為資本深化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這種生產性高消費導致大量勞動力富余,一方面,由于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作用,使就業結構發生轉變,一部分崗位永久性地消失;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產品的生產知識含量較高,需要具有較高教育程度的技術人員,而人口素質的提高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就業結構無法及時調整,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工業不是在大量吸納勞動力而是開始飽和吐出勞動力,第三產業緩慢增長的就業機會,難以容納同時來自農業和工業外溢的勞動力。生產性的消費向發達國家產業盲目跟進導致了各產業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直線下降。
3.3 對西方理論的“非本土化”借用
工業化和信息化是全球化趨勢,但是實現這種目標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應該因國而異。
早期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資本替代勞動力所獲得的巨大發展是顯而易見的,大多數后進國家希望通過模仿他們的發展模式達到本國經濟的騰飛,甚至用急進的方式企圖將“失去的工業化時間”抓回來。因此,相應出現了一批介紹和推崇西方理論的學者和官員。但是,引介理論首先要理解理論,而要對西方理論進行充分的理解必須從歷史的角度研究其出現時的社會整體背景。
早期工業化國家進行技術創新的背景是:①人口稀少,勞動力不足,生產能力低下,工匠們通過技術創新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彌補勞動力資源的不足;②技術創新路徑自下而上,是自發創新,沒有行政干預;③具有“歐洲特色”的科舉制度是技術創新的制度背景。工業革命前我國正處于經濟文化鼎盛時期,由于歐亞文化和生產力水平相差太遠,歐洲社會無法直接模仿借用類似中國科舉制度來選拔人才,只能通過手工藝創新來達到快速從學徒“升級”到業主的目的,因此,工藝技術創新成為手工作坊的生存之道,之后的工業革命在此基礎上展開;④自由、開放的經濟是技術創新的宏觀經濟條件。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人文背景與西歐大相徑庭,如果只重視借鑒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而忽視技術的同化和吸收,將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假設把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按照其價值定義為“一千英鎊”技術,把發展中國家的本地技術定義為“一英鎊”技術[10],如果發展中國家貿然引進“一千英鎊”技術會給本地的“一英鎊”技術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基礎和國情,“一千英鎊”技術不能馬上被當地經濟消化和吸收,大量勞動力失業和經濟增長放緩將在一段時間里存在,社會穩定將受到威脅。
4 通過產業結構創新解決人口問題
目前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是:早期工業化國家分階段出現的社會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同步爆發,如人口問題、就業問題、環境問題、收入分配問題等,這些問題不僅多而且盤根錯節、相互交織具有綜合性和復雜性,而且與本國國情結合形成各具特色的“問題團”,現有的國外理論難以有效解決各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困境。綜上所述,發展中國家要使經濟和社會持續地發展,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以我國為例,可以嘗試創建符合中國國情的產業發展道路解決人口與經濟發展問題。
4.1 明確本國國情
我國的基本國情是人口基數大、國民現代科學素質普遍低下、地區發展不平衡、典型二元經濟結構。為早日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通過學習和模仿西方經濟發展方式和管理制度,實行了大規模的產業自動化,用機器代替人力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增加產量,并將這種方式廣泛地推廣到工廠和農村,這一方面使我國在短期內經濟水平得到快速的提高,另一方面導致社會產生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使社會整體消費水平低下,繼而影響自動化的最初目的―經濟增長,同時,大量剩余勞動力的長期存在又不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
4.2 構建包含國家專有要素的本土經濟學
我國失業理論的發展代表了后進國家學界“洋為我用”的覺醒歷程,特別是后兩種模式正是立足于我國實際、反思西方理論、獨立思考后的結果,但是大多數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有這樣一種思維慣性:通過模仿發達國家經濟發展路徑,考察我國實際經濟社會中存在卻相悖于他國發展路徑的“不當之處”,給予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看似有道理卻難以實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面臨的問題。經濟和人口理論的作用在于為經濟社會發展出謀劃策,提供智力支持,其中經濟社會的健康、穩定、持續發展是主體,理論、政策是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而不是通過改良社會去適應理論,然后按照理論設計進入另一發展模式。這里并不反對借用他國發展模式,但是首先應該選擇真正適合本國的模式,且在實施前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研究,去偽存真,選擇其中與本國國情相融部分,在此基礎上再對理論進行創新性的完善。
4.3 創新型產業模式為人口問題提供了解決之道
根據本國國情選擇,創新理論是壓縮型工業化國家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的根本,關鍵在于政府和學界思維方式的改變,對國際經典理論不迷信不盲從,采取審慎的態度對待“舶來品”,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創建適合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
以人口問題為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數量、人口結構、人口素質、失業等方面,走入了因果倒置的誤區,從根本上講失業、人口數量、人口質量等問題是相對存在的,是經濟社會發展偏離本國國情導致的結果,并不是人口本身就存在問題。因此,研究不應繼續糾纏于問題的表象,而應該尋找問題產生的根源,從源頭上解決問題。如失業問題產生的根源在于:當國民整體經濟社會水平不高的條件下,產業特別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全面盲目自動化,忽視了我國人口眾多、正處于人口紅利期的特點,無視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舍本逐末,花費有限的資金外購昂貴的自動化設備替代人力,導致失業現象大量存在,而且由于這種結構性失業是外生因素(國際產業梯度轉移)引起的,與早期工業化國家不同,很難在短期內通過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容納失業人群(產業國際自由轉移與勞動力要素的不能自由流動造成這一問題),即“一千英鎊”技術摧毀了“一英鎊”技術,經濟和人口問題以扭曲的方式交織在一起,因此,只有建立適合本國的中間技術產業,即“一百英鎊”技術型產業才能充分利用本國充裕的勞動力,使經濟真正獲得“人口紅利”。這種中間技術型產業可以將科技含量高的“一千英鎊”技術分解為若干能適應本地產業、本地技術和本土教育水平的新型“一百英鎊”產業,這種新型產業一方面提高了本地“一英鎊”技術型產業的技術含金量,幫助提升國內經濟和技術水平,使發展中國家盡快與世界經濟接軌:另一方面,大量中間技術產業的存在能充分吸收發展中國家豐富的勞動力,使社會能平穩地渡過產業結構轉型期,使發展中國家延長“人口紅利期”,充分享受經濟與人口發展帶來的福利。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張坤.推行循環經濟是解決我國復合型環境問題的重要舉措[A].張坤.循環經濟理論與實踐論文集[C].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5:32.[Zhang Kun Recycle economy style is the essential way to solve our countries’ composite environmental problem [A].Zhang Kun Recycle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papers[C].Beijing:The environment and science press,2005:32.]
[2] 胡鞍鋼.國情與發展[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5:74.[Hu Angang National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M].Beijing:The university of Tsinghua Press,2006,5:74.]
[3] 王文軍,李蜀慶.建立循環經濟解決壓縮型工業化社會中的環境問題[J].中國工業經濟,2005,(9).[Wang Wenjun,Li Shuqing.Develop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to Solve the Environment Issue in the Condensation Model Industrialization Society[J].Chinese industrial economy,2005,(9).]
[4] 蔡防,王德文.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與勞動貢獻[J].經濟研究,1991,(10).[Cai Fang,Wang Dewen.China's sustainable economy increase versus the labor’s contribution[J].Economy Research 1991,(10).]
[5] 宋豐景.國內失業問題研究最新進展[J].經濟問題,2005,1[Song FengjingThe latest research on the unemployment in China[J]Economy Problem,2005,(1)]
[6] 陳淮.我國勞動力市場政策的主要指向[J].中國勞動,2004,(5).[Chen HuaiOur countries’main policy direction on the labor market[J].China Labor,2004,(5).]
[7] 姚裕群,莫榮.中國城鎮失業率為7%已進入風險區[J].熱點研究,2002,(10).[Yao Yuqun,Mo Rong.China’s urban unemployment ratio has reach 7%,and is going to risk area now[J]Hot Research, 2002,(10).]
[8] 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China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group. From a huge population country step into a strong human resources country[M]. Beijing: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3]
篇(7)
[中圖分類號] F0 [文獻標識碼] B
一、引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經濟維持了高速穩定的增長態勢,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而這幾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與我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眾多的勞動人口為我國經濟增長做出了極大貢獻。根據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人口紅利”效應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人口老齡化”作為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一個突出現象,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成為了許多經濟學家的研究內容。不論是“人口紅利”還是“人口老齡化”都與我國的人口控制制度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近些年來出現的一系列人口現象都與我國的人口政策,特別是計劃生育政策有著密切的關聯。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的觀點,不同的制度安排決定著不同的經濟績效,從而影響著人類的行為方式。可以說,制度是至關重要的。
在我國,計劃生育制度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其對于人口變化和家庭生育決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很多經濟學家也探討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而這一影響途徑是用人口作為中間變量的。近些年來,新家庭經濟學的興起,特別是用微觀經濟原理解釋家庭生育決策的方法和成果的廣泛傳播,為研究家庭行為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另外,近一段時間一個被廣泛討論的名詞――“失獨家庭”,也是本文寫作的背景之一,所謂“失獨家庭”是指獨生子女由于出現了各種意外傷亡,而其父母不再生育或收養子女的家庭。可想而知,這種狀況對于家庭是多么沉重而殘酷的打擊。而且根據有關機構的估計,目前我國至少有100萬個“失獨家庭”,且每年以7.6萬個的數量增加,由此可見我國目前的人口結構和家庭結構的脆弱性和復雜性。不僅如此,計劃生育制度實施以來,雖然促進了我國向低生育率的轉變,為經濟增長做出了很大貢獻,但也給社會帶來了諸多問題。因此,面對這一問題,近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分成了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應該繼續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另一種認為應該逐步放松,甚至取消計劃生育政策。
二、生育決策理論相關研究綜述
家庭生育決策理論是人口理論中的一個重大主題,而經濟學對于人口問題的關注則由來已久。眾所周知,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是一個典型的雙向關系,人口變動對于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而經濟發展又推動著人口結構和數量的轉變。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行為的一門科學,而家庭作為經濟的微觀主體之一,更是經濟學家所重點關注的領域,用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家庭活動則推動了一門新的學科,即“新家庭經濟學”。新家庭經濟學主要研究家庭生育決策;家庭成員的就業決策與勞務分工;以及家庭組織經濟問題等。因而,生育決策理論作為新家庭經濟學的一個核心主題,得到了經濟學家們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并建立了若干種家庭生育決策理論模型,用以解釋經濟發展中的生育率變化以及不同經濟條件下的家庭生育決策。
在家庭生育決策研究中被廣泛使用的理論主要包括:萊賓斯坦的“邊際孩子合理選擇”理論,貝克爾的“數量質量替代”理論,卡德威爾的“財富流”理論,以及伊斯特林提出的“生育供給與需求模型”和“生育率臨界假說”。
這些年來,面對國外學者對于生育決策問題不斷涌現的學術成果,國內學者依據本國國情,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造性的解釋和學說。李小平(1992)提出的“期望孩子效用”概念,他認為父母的生育意愿取決于孩子帶來的期望效用,而非實際效用,政府可以通過降低孩子的期望效用來降低父母的生育意愿,從而達到降低生育率的目的。彭希哲和戴星翼(1993)提出了“風險最小化原則”,他們認為風險最小化原則表明我國農村地區夫婦決定是否再生育子女時,其內在的動機是為了分散風險,即通過選擇生育數量來規避風險,使風險得以減弱。應當說明的是,風險最小化原則和效用最大化原則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風險最小化原則可以用效用最大化原則的函數式表示,但其最明顯的區別在于政策含義,風險最小化原則要求通過降低風險來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國家對少生的家庭進行補償,然而效用最大化原則要求通過提高孩子的成本或降低孩子的效用來降低生育意愿。對于我國落后的農村地區而言,風險最小化無疑更為適用。
周雙超(1996)則認為傳統的成本―效用理論忽視了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孩子對于家庭的效用是不同的這一事實,他認為孩子對父母的效用主要包括享受效用和必需效用,而父母對孩子的需求主要分為奢侈需求和基本需求,因而,當孩子是奢侈品時,父母對孩子需求的彈性較大,當孩子是必需品時,父母對孩子需求的彈性較小,因此,對于我國落后的農村地區而言,父母對孩子的需求是基本需求,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父母對孩子的需求趨向于向奢侈需求轉變。
經典的西方生育決策理論提供了一整套用于研究家庭決策行為的工具和視角,但是它的運用建立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基礎上,一般的基本假設包括:家庭生育決策以追求效用最大化為目標;家庭中的個體均為完全理性的經濟人;每個家庭中的個體是完全自由的,其對于出生人數和出生間隔完全可以自主決策和控制;孩子既是一種耐用消費品,又是一種生產物品,他具有消費性和生產性;市場環境是完全競爭市場,即商品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是完全競爭的。經濟形態為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商品經濟關系高度發達且無處不在。
只有滿足以上的假設條件,其通過模型得到的結論才能夠成立,顯然,對于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中國來說,其假設條件并不完全滿足。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龐大的13億人口,市場經濟制度遠未建立完善,且在廣大農村地區,商品經濟遠未成熟,收入水平還較為低下,存在著自然經濟的殘留思想和觀念。因此,簡單的套用西方經典理論是切不可行的。在研究過程中,需要注重本國國情,從實際出發,靈活地運用和吸收西方生育決策理論,注重不同的假設前提,借鑒分析方法,從而得出符合我國實際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我國的家庭決策和家庭活動具有一些特殊且重要的特點,例如:①父母一般會撫養子女到成家立業為止,即當子女完婚后才會真正脫離父母撫養,因此,家庭撫養子女的時間要長于西方國家。②家庭養育子女成本的內容比西方國家要多,除了一般的費用,通常還包括買房,結婚等費用。③具有濃厚的“養兒防老”的傳統,子女的保障效用極為重要,這源于深厚的傳統思想觀念,較為落后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家庭養老”的傳統。④我國的家庭,尤其是農村家庭中具有濃厚的“宗族文化傳統”,“傳宗接代”,“人丁興旺”等觀念深入人心,其宗族的生育壓力較為明顯。⑤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生育政策,政策控制力度較強,家庭的生育決策空間較小,絕大部分家庭的生育子女數量為0-2個。⑥經濟處速發展中,經濟變革、社會變革、文化變革都深刻而明顯,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因素較之西方國家更為復雜和多變,因此,需要更為多樣且細致的分析。
總而言之,對于西方理論的應用應當重視假設前提,借鑒分析框架,絕不能生搬硬套,更何況,西方生育決策理論中的很多結果尚需實證檢驗,很多理論還存在空白和有待發展之處。與西方經典生育決策理論相對應,我國學者的研究更注重本國的實際和國情,更加關注特殊的文化體制因素對于生育決策行為的影響。但是,我國學者的分析也具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對于理論的重視不夠,多傾向于利用西方現有理論進行實證分析,而缺少對于模型的構建與理論的創新。另外,對于西方生育決策模型的運用缺少前提,片面的運用從而導致錯誤的結論。而且研究多局限于微觀范疇,缺乏對宏觀變量影響的研究。
三、制度變遷與生育決策的相關性研究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定義,制度有兩層基本含義:一是制度是一種行為規則,它決定了社會主體在社會生活中可以選擇的行動方式。二是制度是人們結成的各種經濟、社會、政治等組織或體制,它決定著一切社會經濟活動和社會經濟關系的展開。按照制度的層次,制度可以分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實施機制。制度包含著激勵和約束的雙重功能,制度的變遷推動著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轉變,不同的制度安排決定著不同的經濟績效,也對人產生不同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促使人的行為的改變,同時也改變著人的決策方式和權衡關系。
不同的制度安排導致不同的經濟環境,不同的經濟環境導致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用發生變化,家庭中的個體面對著成本和效用的變化會做出不同的生育決策,體現著制度變遷對于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下面將簡要介紹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變遷對于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
曾毅和舒爾茨(1998)主要研究農村對于生育率的影響。他們運用羅吉斯特多變量回歸方法和生命表分析方法進行相關數理統計分析,他們認為在集體所有制的“大鍋飯”體制下,實際上會對農村生育多孩的夫婦給予了一種經濟補償,而的推行則打破了“大鍋飯”體制,客觀上取消了對生育多孩夫婦的補償,從而導致了生育率的降低。通過數值分析,他們得出結論:在改革前期,削弱了生育控制,而在后期使家庭傾向于少生孩子,同時加強了生育控制。王水雄(2002)則通過將博弈論內容引入生育決策模型中,建立了生育的博弈模型,從而證明了在沒有制度控制下,當公共領域中存在大量資源,且實行平均分配制度,人們此時傾向于多生孩子,從而導致了“公地的悲劇”,這表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制度將會導致家庭傾向于多育孩子,而市場經濟體制且產權明晰的條件下,家庭傾向于少育孩子。
與此類似,鄭龍真,史清華(2006)通過調查樣本數據,運用博弈分析方法,比較了無制度控制下的農民生育決策行為和有制度控制下的農民生育決策行為。得出在無制度控制下家庭將會選擇多育孩子以爭奪公共資源,在存在制度控制的條件下,人們將會減少孩子的生育數量。張華寧、陳紀平(2009)的研究利用產權經濟分析的方法,通過在人口增長率的統計分析中加入政府產權制度效率參數和計劃生育政策強度參數,通過將實證分析和邏輯推演相結合,得出兩個基本結論:一是由于產權制度的變遷,不同的產權制度導致不同的績效,由于產權界定具有規模經濟性質,隨著產權制度體系效率的提高,導致家庭生育行為的變化,進而導致過剩人口數量逐步減少,人口增長率下降。二是由于產權界定不完全,導致人們擁有多個孩子以獲取更多的公共資源,從而導致“非生產性”過剩人口的增加,進而導致人口生育率的上升。
對于計劃生育制度變革是否會引起家庭生育決策的變化,即是否會引起生育率的反彈,學界基本上呈現兩種態度。顧寶昌(2010)提出改變計劃生育政策,即放開二胎不會引起家庭生育行為的改變,也不會導致人口失控。而朱中仕和陳華(2012)的研究表明調整現行人口制度的時機還不成熟,在短時期內將會引起家庭生育行為的改變,導致人口生育率的反彈。
通過不同學者對正式制度變遷與生育決策的相關問題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正式制度包括產權制度、農業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計劃生育制度等社會經濟中的一系列制度都會對家庭生育決策產生影響,進而對人口增長率和生育率的變化產生影響。
四、生育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根據有關部門的估計,我國因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而少生的人口達到3.38億。同時也大大加速了我國人口轉變的進程,人口轉變是指從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狀態轉變到兩者都很低的狀態的過程。根據國際經驗,人口轉變一般要經歷三個階段:一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階段;二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的階段;三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階段。[21]在我國,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對生育的有力控制,經過30年時間,我國便進入了第三階段,即通常發達國家處于的階段。與我國相同收入水平和發展程度的國家均處于第二階段,因此,我國人口的迅速轉變無疑是實行嚴格計劃生育政策的結果。
與我國人口轉變過程迅速推進相伴隨的是人口老齡化加劇和“人口紅利”效應,按照聯合國的劃分標準,在全部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10%,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超過7%,即被稱為老齡化社會。據此推論,由于2000年65歲老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96%,我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根據預測,到2050年我國老齡化水平將超過20%,成為名符其實的“銀發國家”,這對于我國的長期經濟增長將會產生復雜的影響。
在人口老齡化的同時,我國的經濟增長也長期受到“人口紅利”的積極影響。“人口紅利”是由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于1998年正式提出的。根據標準的定義,“人口紅利”是指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占總人口的比重較低,這種總人口結構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特征使社會負擔較輕,勞動力供給充足,儲蓄率和投資率處于高位,且絕對量不斷增長,另外,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也不斷增長,從而有利于經濟的高速發展。
很多經濟學家都對“人口紅利”的增長效應進行了研究和檢驗。其中,蔡P(2004)通過運用經濟增長因素分解法得出,東亞奇跡中大約有四分之一應歸結于人口結構因素。同時,他認為大約23.71%應歸功于人口紅利的作用。汪小勤(2007)認為高的勞動參與率會促進儲蓄率和投資率的提高,進而加速經濟發展。王德文,蔡P(1999)的研究表明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回歸系數為0.109,-0.113,且均顯著。一般而言,年輕化的人口年齡結構可以推高儲蓄率,主要因為工作人口的比重增加導致收入增加,從而導致儲蓄增加,而且,年輕人的儲蓄意愿和能力也較高。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促進了家庭生育行為的變化,進一步引發了人口轉變,產生了“人口紅利”效應,根據預測,在2000-2030年間,勞動負擔系數在50%以下,在2030-2050年期間,勞動負擔系數將逐步上升,到2050年將上升至64.36%,屆時,我國將由“人口紅利”轉變為“人口負債”。
由此可知,21世紀的前30年,將是我國利用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機遇期。因此,對于人口紅利的研究就顯得格外重要。在當前學者對于人口紅利的研究中,既出現了許多成果,也存在著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一是對于人口紅利和經濟增長相互關系的研究,多側重于將人口因素、人均收入、人均GDP等指標相聯系。而人口紅利對于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分配結構以及就業結構的影響的分析較薄弱。二是對于人口紅利對于經濟增長的傳導作用與傳導途徑的分析較模糊。三是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出現人口老齡化與人口紅利并存的階段,這一特殊的人口現象對于經濟增長的長期影響如何,也值得深入研究。
[參 考 文 獻]
[1]加里?斯坦利?貝克爾.家庭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62-214
[2]李小平.期望孩子的交易價格及其在生育控制中的應用[J].中國人口科學,1992(5):49-56
[3]彭希哲,戴星翼.試析風險最小化原則在生育決策中的作用[J].人口研究,1993(6):2-7
[4]周雙超.生育需求的經濟分析[J].人口與計劃生育,1996(2):41-44
[5]盧現祥,朱巧玲.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420-432
[6]曾毅,舒爾茨.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對生育率的影響[J].中國社會科學,1998(1):129-143
[7]王水雄.生育的博弈模型:中國的例子[J].社會學研究,2002(6):82-94
[8]李建民.生育理性和生育決策與我國低生育水平穩定機制的轉變[J].人口研究,2004,28(6):2-18
[9]鄭龍真,史清華.農村家庭生育行為的博弈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06(3):29-33
[10]王躍生.制度變革、社會轉型與中國家庭變動――以農村經驗為基礎的分析[J].開放時代,2009(3):97-115
[11]張華寧,陳紀平.理性人口過剩:人口的產權經濟分析[J].經濟管理,2009(7):166-171
[12]顧寶昌.中國人口:從現在走向未來[J].國際經濟評論,2010(6):95-111
[13]朱中仕,陳華.由赴港生子到生育公地悲劇的認識[J].人口研究,2012,36(4):103-112
[14]蔡P.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機制改革的理論思考[J].中國人口科學,2001(6):1-8
[15]黃步云.家庭生育選擇行為的經濟學分析[J].西北人口,2005(1):61-64
[16]鄭真真,李玉柱,廖少宏.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J].中國人口科學,2009(2):93-102
[17]王金營,顧瑤.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條件、問題即對策[J].人口研究,2011(1):74-81
[18]蔡P,都陽,高文書等.勞動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現實[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20-40
篇(8)
與以往不同的新常態
中國經濟報告:世界和中國都在經歷著巨大的變化,在你看來,中國經濟新常態與過去相比有哪些主要的不同特征?
青木昌彥: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在經歷了前所未有的35年高增長后已進入新常態時代。中國乃至整個亞洲,當下都迎來了一個可以媲美“工業革命”和“計劃經濟體制終結”的重大轉折期。在人口、就業等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結構上,一些不可逆的變化正在開始發生。這些動向會對未來產生怎樣的影響?思考這一問題時,比起短期的需求面的要素(比如消費、投資、出口,即所謂“三駕馬車”),更要重視中長期的供給面的各種要素。這樣,有關人均GDP增長的人口、制度、經濟的相互關系就會明朗起來。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計,中國的GDP(以當前價格計)在2009年就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如果以購買力平價來測算實際GDP,中國的經濟增長成績將更為驚人。中國2013年的實際GDP達16.149萬億美元,大約相當于日本的3.5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測算)。盡管在人均GDP水平上,中國依然落后日本約70%,但根據我利用省級數據進行的估算,中國沿海地區的人均GDP已達13449美元,僅落后日本約60%。“新常態”作為經濟學上持續增長的供給要素的新階段,有著以下的特征。由于農業就業比率的下降促進經濟加速增長的庫茲涅茨效果和由于勞動人口比率的增加促進經濟加速增長的人口紅利的效果逐漸減小,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可能性開始轉向依賴全要素生產率增加的階段。要回應這一挑戰,關鍵在于在人力資本積蓄的同時,進行企業經營和治理的改革。而要實現這些,則需要考慮如何在經濟領域實現法治。在資本收益率高于經濟增長率的少子老齡化社會,中國現階段出現的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的解決之道都取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與之相輔相成的公司治理改革。
中國經濟報告:你前面提到,中國按實際人均GDP計算已成為中等收入國家,那么中國能否繼續維持與過去相當的高增長率?如果不能,有哪些因素在決定和影響著新常態下的增長機遇?
青木昌彥:這可以用事實來說話。首先來做個簡化計算,把人均GDP增長率分解為不同的供給來源。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增長可能性的公共政策討論往往集中在短期的需求因素上:出口、投資以及公共和私人消費――俗稱的“三駕馬車”。然而對長期增長潛力的評估卻離不開供給方面的因素。中國在2008-2012年年均8.62%的人均GDP增長率可以分解為如下幾個來源:
(1)工作年齡段(15-64歲)人群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也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對人均GDP增速的貢獻約為0.46%;(2)工作年齡段人群的勞動參與率下降(主要是因為學校教育增加),給人均GDP增速帶來的負面影響約為-0.57%;(3)從低生產率的農業部門(A部門)向高生產率的城市部門(U部門)的勞動力轉移,即所謂的庫茲涅茨效應,貢獻值約為3.11%;(4)城市部門員工的人均生產率提高,貢獻值約為5.46%。
在研究中,我曾從歷史和國際比較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成績(圖1),這幅圖展示了日本、韓國和中國在過去半個世紀的人均GDP增長軌跡及其供給源頭分解結果(借助各個國家的官方數據)。對三國的柱狀分解圖進行對比,我們能立刻得出如下幾個印象:
(1) 庫茲涅茨效應是三個國家高增長時期普遍發生的現象,日本(1955-1970年),韓國(1970-1990年),中國(1982-1987年,2000-2012)。
(2) 在三個國家的高增長時期,人口紅利也普遍存在。不過這個效應在逐漸減弱,日本在1990年后甚至最終出現負效應。
(3)工作年齡段人群的勞動參與率變化對人均收入增速可以產生不容忽視的正面或負面影響,取決于下面將談到的若干社會因素。
(4) 由于庫茲涅茨效應和人口紅利的減弱趨勢幾乎是不可逆轉的歷程,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可持續增長的可能性將主要依賴城市部門人均生產率的繼續提高,尤其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中國經濟報告:那么,哪些供給因素決定著經濟新常態的特征?
青木昌彥:圖1所包含的是從國別比較和歷史背景得出的信息,這將有助于我們再來分析各種供給因素對新常態面臨的發展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可以看到,經濟新常態的特征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庫茨涅茨效應能否繼續發揮作用,從人口紅利到后人口轉型的成敗,影響勞動參與率的社會因素,全要素生產的增長等方面。
無需為庫茲涅茨效應的消失而惋惜
中國經濟報告:結合一些有此經驗的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中國的庫茲涅茨效應能否繼續發揮作用?
青木昌彥:歷史上的第三位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哈佛大學的西蒙?庫茲涅茨觀察到,農業部門在產值和就業比重中的長期下降是“經濟增長的數量特征”。這一實證研究結論是基于其對當時還極為缺乏的歷史和國際比較數據的艱苦的收集分析。法國用了60年時間(1880-1950年)才使農業就業比重下降了19個百分點(從52%到33%),德國用51年(1882-1933年)下降了13個百分點(從42%到29%),美國用40年(1870-1910年)下降了19個百分點(從50%到31%),等等。除19世紀早期引領工業革命的英國外,農業就業人口比重的減少過程都是相當緩慢而長期的。相反,圖2表明,東亞各經濟體的這一過程被壓縮到更短時期完成。中國沿海僅用了20年(1990-2010年)就下降了近28個百分點(從50.0%到23%),內陸也下降了25個百分點(從68%到43%)。1990年,制造業的人均產值比農業部門高出4.0倍,2008年高出5.1倍。因此,大規模和快速的庫茲涅茨效應成為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高速增長的極為顯著的促進因素。
從圖2中還能得到一個有趣的對比結論,可能與預測中國未來的增長軌跡有關。日本和韓國的農業部門就業比重分別在1970年和1990年下降至約20%,同高增長時期結束的時點基本吻合。在20%的分界線之后,兩個國家農業部門就業比重的下降變得相當緩慢,主要是通過農村家庭的子女上學而進入城市部門。兩國的農業都主要依靠人數逐漸減少的老一代人來維持,由政府的產品價格補貼政策提供保護。
中國經濟報告:結合中國的情況,新常態下的庫茲涅茨效應又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青木昌彥:由于中國沿海地區的農業部門就業比重目前可能已達到20%的臨界點,內陸也處于逼近過程中,關于庫茲涅茨效應的影響,中國社科院的研究者利用官方2009年居民調查數據測算出,當時仍在農業部門就業的農村居民人數約為2.11億,而離開農村、在城市部門就業的人數約為1.86億。中國政府在2014年確立了一項重要政策,計劃到2020年再從農村轉移出1億就業人口并幫助他們在城市安家。然而2009年的調查發現,仍在農村工作的人口中約70%的年齡已達到或超過40歲。此后數年,肯定又有大量年輕人離開農村,留下的人的整體年齡更為老化。在我看來,為實現上述的宏大政策目標,有兩個議題亟待重視。
第一個議題是,年齡偏大的那些勞動力的技能是否在農村之外有合適的就業出路。社科院的研究者認為有此可能,因為城市就業環境需要高技能與低技能工作的互補。第二個議題是,年齡偏大的這些人是否有搬離農村的激勵?我聽說存在40歲以上的農村移民返回戶口原籍的U型回歸現象。假如這的確是個不容忽視的普遍情況,背后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這些年齡偏大的人群對社會保障以及子女上學負擔的憂慮在增加;另一方面他們在農村的土地權利可能有所升值,能部分緩解上述的憂慮。
U型回歸現象本身可能有雙重影響,對城市部門的庫茲涅茨效應產生消極作用,但返鄉農民已掌握的城市部門生產技能可以擴散到農村及其附近區域,是種反向的庫茲涅茨效應。為把兩個方向的勞動力流動的潛在好處都發掘出來,就必須從法律和行政上去除現有戶籍制度對社會保障、入學招生以及農村土地權利的制約。社科院的研究者測算,由此帶來的“改革紅利”可能給2015年的GDP增速貢獻2.03個百分點,此后逐漸下降到2020年的1.61個百分點(由于人口老化,人均GDP的增速可能更低)。如果政策目標實現,這個效應最后也將基本消失。他們的上述測算低于我估計的2008-2012年的庫茲涅茨效應(3.11%)。所以無論如何,庫茲涅茨效應在2020年之后的中國都將變得微乎其微,就像目前的日本和韓國,特別是如果到時候已引入了能促進生產率提高的農村。庫茲涅茨效應是欠發達經濟體在增長階段的獨特現象,無需為其最終消失而惋惜。
中國經濟報告:可否詳細講解一下圖中人口紅利轉型的意義和影響?
青木昌彥:從人口紅利到后人口轉型:圖1顯示了人口紅利的重要影響,其定義是工作年齡段(15-64歲)人群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增加導致人均GDP增速的提升,分別針對日本(1955-1970年)、韓國(1970-1990年)和中國(1982年至今)的高增長時期。這些現象的出現,分別是由于各國在二戰、朝鮮戰爭和災難之后的生育率高峰以及嬰兒死亡率下降所致。先不考慮中國在1970年代引入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隨著日本、韓國這類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可持續增長的前景開始更多地取決于勞動力質量的提高,而非數量增加。然而,人力資本價值的提升同時意味著家庭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包括學校教育、家長的時間和精力以及其他培訓等。結果自然導致生育的子女數量減少,這個現象被人口學家和統一增長理論稱為人口轉型。此外,隨著生產、生活以及醫學的進步,相對于新生兒的數量來說,曾經帶來人口紅利的那代人的長壽會最終導致人口紅利減少,甚至造成負面影響。這個新的趨勢如今被某些學者稱為第二次人口轉型或者后人口轉型,該現象在東亞地區變得尤其突出。
再請看圖3,縱軸上的年份位置根據每個國家進行了調整,使各國的工作年齡段人群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的高峰重合:日本是1990年,中國是2012年,韓國是2015年。在此時點后,人口紅利將加速衰減。盡管存在時滯,三個國家在這方面還是表現出了驚人的相似性。不過也有點值得注意的差別――中國在高增長時期之前有著更高的生育率,在隨后至今有更高的人口紅利,在未來的短期內受負面影響的進程也較慢。然而聯合國在2012年開展的預測所采用的總生育率是1.6左右,似乎過于樂觀,超出了2010年人口普查得出的1.4左右的官方估計值(按某些人口學家推算更是只有1.2左右)。如果把這些可能的偏差考慮進來,負面人口紅利對人均收入增長率的拖累很可能更大。徹底取消獨生子女政策或許有助于緩解這一下降趨勢,并增強民眾的個人選擇自由,但影響有限,因為后人口轉型的一個根本原因是收入的增長(壽命延長)以及家庭對人力資本投資的理性計算。
影響勞動參與率的社會因素
中國經濟報告:在負面人口紅利的拖累越來越大的情況下,中國如何才能更好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日本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有可以借鑒的經驗?
青木昌彥:如果說庫茲涅茨效應的逐漸消失以及后人口轉型的快速到來是經濟新常態的基本特征,那么要實現可持續的人均GDP增長及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提高勞動參與率,并持續提高城市部門的人均生產率。就前者而言,日本近期的經歷可以有所借鑒。有兩個人群對人均GDP增長做出了貢獻,25-39歲的女性人群的勞動參與率在2000-2012年大幅提高,同時總體的生育率也有適度反彈,從2005年谷底的1.26回升到2013年1.43。上述變化結合起來表明,跟隨歐洲國家的腳步,日本女性因為結婚和生育而從勞動力市場退出的習慣到今天可能已經被扭轉。雖然中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在傳統上高于東亞的其他國家,她們對于高技術崗位的更多參與依舊可望成為維持中國人均GDP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
應對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下降的另一個可能性,是提高年齡偏大人群的勞動參與率。在2000-2012年,日本的60-64歲的男性人群的勞動參與率提高了2.81%,70歲以上的男性有8.7%仍在工作。中國目前的男性60歲、女性55歲的強制退休年齡也需要采取某種方式相應上調。前面圖1顯示,中國的勞動參與率自1990年來實際有所下降,這似乎與學校教育時間的不斷加長有關。在2009-2013年,高中入學率提高了2.7%,大學及大學以上教育的入學率提高了4.0%。教育投入的增加會在短期內導致人均GDP增長率降低,但如果能與需求匹配,還是對未來人力資本的物有所值的投資。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下一步發展的關鍵
中國經濟報告:新常態下用以保持人均GDP增長的關鍵一步是什么?
青木昌彥: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關鍵,公司治理也同樣至關重要。新常態下保持人均GDP增長的最重要源泉是城市部門的單位員工生產率的不斷提升。城市部門的單位員工生產率等于全要素生產率同資本―產值比(資本密度)的加權之和,權重分別為:1/(1-θ)和θ/(1-θ),其中θ是資本在產值中的比重。由于缺乏與圖1所采用的部門數據相匹配的可靠官方數據,這里暫時無法提供對上述兩部分的估計值。但測算中國各部門全要素生產率的多項學術研究表明,2000年代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有所下降,也就是說人均產值增長主要是依靠資本積累。資本積累如果沒有伴隨人力資本的相應增加,最終將受到規模收益遞減的制約。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正接受學校教育的年輕人群的勞動參與率提高會帶來令人鼓舞的效果。
全要素生產率源于無法用直接投入測算的人力資本與實物資本的“新的組合方式”。眾所周知的是,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就是熊彼特定義的“創新”。實現方式之一顯然是通過技術方面的創新,而這需要投資以及增加科技領域的資源投入。不過同樣需要強調的是,人力資源與金融資源在企業組織層面的創新組合也大有可為,可以更靈活地應對新興技術和變化的市場環境。發現和利用這些機遇是職業經理人的任務。
當前,對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政府擁有和控制的控股公司層級進行體制改革,引入混合所有制形式,已被列入重要的改革議題。然而此類所有制改革應該與公司治理結構改革配套實施,以增強企業管理層的職業化程度,根據企業經營標準對其進行考核,擺脫政治因素的干預。目前正在打擊的企業腐敗現象非但在道德上應受到譴責,同時也是效率低下的明證。因此很重要的一點是確保混合所有制企業的董事會根據清晰而公開的規則進行選舉,并且對市場和公眾負責。
中國經濟報告:皮凱蒂撰寫的暢銷書《21世紀資本論》讓我們關注到,西方國家的“超級經理人”獲得了超出其業績的報酬,導致更多財富向少數人集中。他認為這在資本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的經濟環境下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用沉重的財產稅進行矯正。那么隨著中國職業經理人制度的推廣,貧富差距的擴大是否也不可避免?
青木昌彥:有個辦法可能使中國避免這一陷阱,這取決于混合所有制如何構建。如果把目前國有資本的相當部分委托給多家退休基金,在金融市場上進行職業化管理,那么這些基金的受益人(退休員工和現有職員)也可以分享金融資本回報率提高的收益。或者說,公司治理改革可以取得一舉兩得的效果,既通過高效和創新的企業管理來促進可持續的人均GDP增長,同時為后人口轉型時代提供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
中國經濟報告:你對中國未來更好的發展,還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建議?
篇(9)
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基本上是處于“劉易斯”模式的初始階段:廉價的勞動力源源不斷地從農村向城市,從內地向沿海轉移,為制造業和以加工為主的出口行業的高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這種勞動力轉移本身也在不斷提高整體經濟的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的增長。
但是,近一兩年來,一些沿海地區出現了民工荒,民工的工資也明顯上升。因此,有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已經面臨“劉易斯”拐點,今后中國勞動力從傳統農業部門向現代工業部門的轉移將會放慢步伐,勞動力供給將不再是“無限”的,勞動成本將會不斷上升,GDP的潛在增長率從而下降。
“劉易斯”拐點所定義的是勞動力從傳統農業部門向現代工業部門的轉移,并不是定義勞動力從內地向沿海地區的轉移。目前,勞動力從內地向沿海轉移的速度或許已經放慢,但是,內地的農村勞動力仍然不斷向內地城鎮轉移。這并不意味著在中國整體經濟中,勞動力從傳統農業部門向現代工業部門轉移的速度放慢。
此外,“劉易斯”拐點并不意味著勞動力馬上停止從傳統農業部門向現代工業部門的轉移,只是表明這種轉移的步伐可能放慢;這不意味著勞動力馬上會出現短缺,只是表明勞動力供給將不再是無限的。
中國的城鎮化水平才剛剛達到50%,傳統農業部門仍然能夠在今后20年左右為現代工業和服務業部門提供勞動力資源。
目前一些沿海地區出現的民工荒以及沿海地區民工工資的明顯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有著積極意義,而不是負面影響。
沿海地區民工工資的明顯上升,一是反映了對過去勞動力收入增長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補償;二是對沿海地區的產業升級將起到積極的逼迫作用;三是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消費增長。
一些沿海地區出現的民工荒以及民工工資的明顯上升,可以看作是市場機制對勞動力資源在區域和行業之間的重新分配,其本身并不會對中國經濟的繼續增長帶來負面影響。關鍵是,各方面的改革和政策要跟上,進一步增進勞動力和資本的自由流動,為沿海地區的產業升級提供有利的技術創新環境,為內地城鎮化和現代化的發展提供有利條件。
在此,再說一個拐點問題。另有一位美國分析人士強調,由于中國過去30年來的“一胎化”政策,勞動年齡人口與其他年齡人口的比率將在2013年左右開始呈下降趨勢,出現人口紅利拐點,中國經濟在今后的增長將會因此減緩。
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一直呈增長趨勢,更重要的是勞動年齡人口與其他年齡人口的比率也一直呈上升趨勢,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1.07上升到目前近1.4。經濟學家將由于這一比率上升而給經濟增長帶來的貢獻稱之為人口紅利。有經濟學家估計,過去30年,中國GDP平均每年增長10%,其中1至1.5個百分點是人口紅利。
中國勞動力的素質近年來隨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呈上升趨勢。專業技術人員數量的年均增長率在2000-2007年期間維持在1%左右;全國人口中受過中等教育的比率已從1980年低于20%,上升到目前接近40%;受過大專以上教育比率也從1980年低于1%,上升到目前的8%。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人口和勞動力的素質還有很大差距。因此,只要繼續加快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可以抵消勞動年齡人口比率下降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
篇(10)
中國要經過一個減速關,似乎看上去不那么樂觀。因此,筆者想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為什么會減速,以及為什么說減速是個重要的關口。我們究竟是不想讓它減,人為的把經濟增長速度刺激起來,還是正視減速的趨勢,坦然接受它,同時考慮采取什么樣的政策來應對?所以,對于政策制定來說,當前的確是一個“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時刻。答案應該建立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拍腦袋、想當然。
“狼來了”并不可怕
黨的十提出,在2010年的基礎上,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而黨的十七大時提出的是,在2000年的基礎上,到2020年人均GDP翻兩番。前十年我們已經超額完成了任務目標。現在還剩下十年時間,如果再強調人均GDP翻番,就意味著要求更高的發展速度。因此,這次提出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再翻一番。在2010年的基礎上,2011年增長了9.2%,2012年再增長7.8%。再往后看,其實不需要7%的年均GDP增長速度就可以翻番。這個目標是很宏偉的,但是并不要求很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意味著我們可能留出余地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過去三十余年,我們一直是以接近10%的增長速度,“十一五”期間更是高達11.2%的速度。所以大家感覺如果降到10%以下,甚至到8%以下,顯然是減速了。
在整個2012年,大家聽到的都是經濟增長速度在下降。歷來國際上也總有人在唱衰中國,不斷講中國崩潰論。國內也有很多人經常在擔心。以前喊了很多次狼來了,狼一直都沒有來,但是,2012年GDP增長率降到了8%以下,狼好像終于來了。從2006年到現在,即使經歷了金融危機,GDP增長速度從來沒有跌到這個水平。看上去終于被說中了,中國經濟要減速了,那些喊“狼來了”的孩子們頓時歡欣鼓舞。但是,從以前人們所擔心的問題看,狼來了以后好像也沒那么可怕。
中國政府一直堅持增長速度不能跌到8%以下,即使遭受金融危機也要保8%,因為擔心不能滿足就業的需要,沒有足夠的就業崗位,居民的收入就會下降,就會產生社會問題。然而,2012年真的跌到了8%以下,我們看到的勞動力市場卻十分平靜:新增就業超額完成年初確定的目標,城鎮登記失業率是4.1%,和往年相比沒有什么變化。同時我們也看到,全國有23個省市自治區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很高。提工資意味著勞動力還是不足的,招工難勝過就業難。因此從勞動力市場狀況看,形勢并沒有像以前認為的,降到8%以下我們就承受不起了。
圖1顯示的是,作為公共就業服務機構的勞務市場上,要招工的和要找工作的數據。即用崗位數做分子,用找工作的人數做分母,很顯然,比值大于1的話,就是崗位多于求職人數。如果小于1,很多人就找不到工作。2012年全年保持大于1,最后是108,高于上一年,崗位還是比想要找工作的人多。當然其中的結構是不一樣的,比如大學生想找的工作就沒有那么多。
為什么我們一直怕狼來了,但狼真的來了以后,卻沒有顯示出它的兇惡的本性?我們的就業并沒有受沖擊。并不是說以前我們錯了,而是說今天的勞動力市場格局跟過去不一樣了。基本的原因就是,如果實際增長速度沒有低于潛在增長率,就不會出現周期性失業,就不會產生對就業的沖擊。潛在增長率,就是根據現有的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土地等)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水平決定的正常增長速度。潛在增長率有一個前提,即假設所有的生產要素充分就業,如果實際增長速度不低于潛在增長率,在這種情況下肯定是充分就業,甚至還可能出現招工難。2012年年初召開“兩會”的時候,溫總理宣布預計GDP增長是7.5%,最終實際增長率仍然高于目標值,也高于我們估算的“十二五”期間的潛在增長率7.2%以及2012年的潛在增長率7.5%。很顯然就不會造成對勞動力市場大的沖擊。
再從更長期的因素來看。人們都在說,經濟增長速度越快越好,沒有人說越慢越好。其實,快當然好,但是不應該說越快越好。首先,經濟增長速度并不是說哪個越發達,它的增長速度就越快。高速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一種趕超現象,你落在別人后頭,只有快于別人的增長速度才可能趕超別人。
圖2最左邊是世界的平均增長速度。隨后是幾個代表性的窮國,它們的增長速度都很快,大概都在6%-8%的水平上。再以后是所謂的金磚國家,總體上發展也是比較快的,其中有的更快一些,有的稍慢一些。再往后是發達國家中經濟比較健康的,像德國和美國。發達國家里頭比較差的日本和希臘都是負增長。正常和健康的國家也一定是最有競爭力的,筆者選了澳大利亞、奧地利、加拿大,它們是正的增長速度,但是慢于趕超國家。趕超國家處在比較低的發展水平,可能缺資本,技術差距大,但是,如果條件具備了,能夠有投資的增長,再多借鑒一些其他國家的技術,趕超速度就會快一些。實際上,越是發達的經濟體越不可能實現超常的經濟高速增長。
為什么比較落后的經濟體在趕超的過程中,可以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速度,有很多的解釋。一般來說,解釋經濟增長重要的一條是制度。一旦戰亂、政治腐敗或者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等等這些因素都解決了,或者假如大家都在相同的背景下,其他條件不變,技術差距反而是一個后發優勢。有沒有人口紅利也很重要。羅伯特?索羅是所謂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創始人,他假設勞動力是短缺的,不斷投入其它要素比如資本,就會出現報酬遞減的現象,經濟增長速度就不會太快。經濟增長的源泉來自于生產率提高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表現超乎于其它的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就更快一些。
在這個假設之下,克魯格曼在上世紀90年代就批評亞洲四小龍,認為這些國家和地區只有生產要素的投入,就是說只投入勞動和資本,但是沒有技術進步,沒有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表現不好。因此他預期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和蘇聯模式一樣,最終都要停滯下來。雖然經歷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但是金融沖擊并沒有傷害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長期增長,亞洲四小龍無一例外進入高收入的行列。克魯格曼預測不準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一個根本缺陷,就是它沒有看到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當代的發展中國家,存在著人口紅利,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勞動力不斷從低生產率的部門轉到高生產率的部門,構成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這些經濟體可以不斷地靠投入得以增長。可見,有沒有人口紅利決定了有沒有趕超的機會。中國增長過程就是在改革開放大背景之下,充分利用人口紅利所實現的。
人口紅利已經消失
人口紅利簡單地說,是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比較快,比重比較高,絕對數量比較大。因此,不用擔心勞動力會短缺,永遠不會構成經濟增長的瓶頸。如果把勞動年齡人口當作分母,把其它年齡組即依賴性人口比如年幼、年老者的當作分子,會得到不斷下降的人口撫養比,這可以幫助實現高儲蓄率。因此簡單地說,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和撫養比下降,就可以帶來人口紅利的窗口。迄今為止,我們的勞動年齡人口不斷增長,被撫養的少年兒童數量在減少,老年人口雖然也增長,相比于勞動年齡人口相比較慢一些,絕對數量沒有那么高,撫養比是在下降的。所以,這一段時期我們得到了人口紅利。
一般講人口紅利是勞動力多、儲蓄率高,其實還可以從更多的角度看。過去的30余年,幾乎在所有的增長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紅利的因素。對此我們做了一些分解,但是把它們合并在圖3中。過去30多年,我們是每年平均接近于10%的經濟增長速度,最大的貢獻來自于資本投入,就是這個資本投入也是充滿了人口紅利。有兩點大家需要理解,第一點是筆者剛才說的撫養比低,人口負擔輕,生產出來的剩余可以儲蓄起來,可以實現高儲蓄率從而資本積累,就有資本可以投入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按照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假設,勞動力是短缺的,持續不斷投入資本,就會出現報酬遞減現象。表現為勞動力無限供給的人口紅利,意味著打破了新古典假設的約束,因此不會遇到報酬遞減現象,靠投資取得經濟增長也就是可行的。
說到全要素生產率的來源,一般人們可以無限地列舉,比如推進改革、改善管理、技術進步、資源重新配置等等。大體上它主要是來自兩個部分,一個是技術進步,還有一個資源重新配置。你把勞動力、資本從生產率低的部門配置到生產率高的部門,生產率自然就改善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兩個部分與人口紅利有什么關系呢?我們又做了一個分解,也反映在圖3里面。跟前面不是一個模型,但是意思差不多。專門看全要素生產率這一塊,這里全要素生產率是17%,其中8個百分點是從低生產率部門轉移到生產率更高部門的勞動力轉移創造,構成了全要素生產率進步的接近一半。由此看來,中國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基本上來自于人口紅利。
當然,這并不是說體制因素不重要。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中國人口紅利就開始下降。只有改革開放以后,伴隨著對傳統體制的改革,以及中國加入WTO,融入了全球化經濟,我們才開始大幅度獲得了人口紅利。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主要來自于人口紅利,人口紅利滲透于所有的經濟增長源泉,是在制度條件已經存在的前提下,解釋為什么我們可以實現高于其他國家的增長速度的重要因素。
因此,符合邏輯的結論是,如果人口因素發生了變化,特別是人口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口紅利沒有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所有源泉都會發生逆轉性的變化。人口紅利消失和經濟增長減速是什么樣的關系,迄今為止還沒有討論清楚,原因是過多的膚淺研究在干擾人們深入地認識這個問題。有一個好消息就是,當人們還在爭論人口紅利是什么東西,或者爭論人口紅利什么時候消失時,我們發現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了,已經沒有必要爭了。
最近的人口普查是2010年。根據這次普查的數據,可以清楚的預測到,15到59歲的勞動年齡段的人口,2010年之后是絕對的減少(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認為,這個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減少發生在2012年)。不是說在減速,而是絕對的減少,勞動力供給是負增長。以15到59歲人口做分母,15歲以前的人口和60歲以后的人口做分子,就是人口撫養比,2010年之后開始提高,而不再是下降了。按照我們前面說的,看勞動年齡人口和撫養比,就是人口紅利的指標。這些指標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轉折,一個是從正到負,一個是從負到正。根本性轉折很自然的意味著,從2010年開始,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當然說它還會有一些潛力可以挖掘,但總的趨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口紅利消失以后,人口這一個因素會影響經濟增長的源泉。
如圖4顯示,勞動力的增長率2010年以后是負的,即今后它是負貢獻。投資的增長率過去非常高,我們假設它今后一定會下降,因為將來儲蓄率也不會有那么高了。至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我們沒有說它一定會大幅度的下降,也不知道它會不會大幅度的提高,按照趨勢描畫了一下,假設趨勢不變。
講到這里,大家可能會問兩個問題。一是人們通常是把15歲到64歲的人口作為勞動年齡人口,我們為什么提出15歲到59歲?按照以前的研究,筆者曾經預計到2013年人口紅利消失,也是依據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做出的判斷。為什么突然轉換了概念?一個原因是根據中國的退休制度,男60歲退休,女55歲退休,有一些工種女職工50歲就退休了。退休了以后,通常人們就離開了工作崗位。第二個原因是和受教育程度有關。
如圖5所示,橫坐標是講15歲到64歲的人口,縱坐標是受教育的年限,不管受哪一級的教育都加在一起。其中美國不僅受教育程度在每一個年齡段都比我們高,他們在各個年齡段受教育程度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假如我們挑一個24歲的美國人,問他受了幾年的教育,他會告訴你14年。如果再挑一個64歲的美國人,他也說是14年,沒有根本性的不同。這意味著在美國,假如勞動力短缺,找不到24歲、34歲、44歲的人,甚至連54歲的人找不到了,那你仍可以雇一個64歲的人,除非要求重體力勞動,他的技能可以是一樣的。日本情況也差不多。但是,中國不僅在每一個年齡段受教育程度低,更重要的是年齡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到了50或60歲的人,基本沒辦法掌握勞動力市場所要求的技能。從這兩個理由看,年過60歲的中國普通勞動者很難成為現實的勞動力供給,把他列入勞動力供給指標沒有什么意義。因此我們采用了15歲到59歲做勞動年齡人口。
第二個問題是為什么要假設投資增長速度不能像過去那么快。因為我們已經超越了二元經濟發展階段,至少已經離它稍微遠一點了,離新古典經濟增長階段更近一點了,這意味著新古典理論所提醒的報酬遞減現象已經開始發生了。筆者借鑒了不同的學者的估算,自己也做一些。資本的邊際回報率一直在下降,過去幾年的下降幅度格外快(圖6)。如果沒有政府補貼給你“打雞血”,你會愿意在報酬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下再繼續投資嗎?換句話說就算你愿意,你能夠保證能得到盈利嗎,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沒有人為干預的正常情況下,投資增長的速度一定會放慢。筆者并沒有假設它放慢太多,只是從高峰降下來,與前些年比其實還是比較高的。筆者認為這樣的假設還是合理的。在這個假設之下,我們可以估算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是怎樣的趨勢。
潛在增長率下降的政策含義
按照上述假設進行估計,1978年至1995年期間,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是10.3%。1995年至2009年期間,估算的潛在增長率是9.8%,跟現實都差不了太多。在“十二五”期間,即2011年至2015年期間潛在增長率降到了只有7.2%。到了“十三五”期間,即2016年至2020年,平均GDP的潛在增長率每年只有6.1%(圖7)。無論是7.2%還是6.1%,拿到世界上大家也會說是很好的速度。印度實現了6%、7%的增長,就被稱為“印度奇跡”。但是如果說這是中國,人們還覺得不夠快,都認為中國應該更快些。我們“十一五”期間大概是10.5%的潛在增長率,到“十二五”期間一下子降下來,這個起伏似乎很大。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劃分“十一五”和“十二五”的就是2010年,正是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從正到負,人口撫養比從下降到上升的關鍵點,因此它就是一個轉折點,人口紅利消失了,潛在增長率出現比較劇烈的下跌也是必然的。我們面臨著潛在增長率的下降,要看應該怎么認識它,能不能在心理上和政策上做好足夠的準備。
筆者認為,我們目前的潛在增長率是一個更平衡、更協調和更可持續的增長率。筆者的研究是在十之前做的。十沒有要求我們在7%以上,但是,今后如果每年能達到7.2%的經濟增長速度,到2020年人均GDP也可以翻番。2012年經濟增長速度顯得很慢,最后結果顯示出7.8%,其間我們聽到企業的哭聲,聽到投資者的抱怨、投行經濟學家的呼聲,聽到外國人希望我們能刺激經濟增長的勸告聲。都說如果能像2009年實施幾個萬億的投資計劃,經濟增長速度馬上會起來,企業會高興,解決了外需不足的問題;外國人更高興,因為你對他的需求更大了。
潛在增長率7.2%是我們的能力,是能夠保證充分就業的,因此我們不用刺激出額外的需求。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們可以知道一段時間中每年經濟增長速度中有多大的部分或多少個百分點來自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的需求。近十年平均消費需求對GDP的拉動作用是4.5個百分點。內需中的投資需求拉動是5.4百分點,外需即出口需求是0.56個百分點。未來我們指望不上出口,姑且假設它的貢獻將來為零。以往我們對國內投資的依賴程度也太過分了,希望將來能夠緩下來,姑且也把它減掉一半,只剩2.7個百分點。這2.7個百分點加消費需求的4.5個,正好是7.2個百分點。就是說合理的需求拉動作用和潛在增長率是完全可以匹配的,我們不需要人為地加大投資以增加需求。人為刺激出的需求也許能把經濟增長速度拉上去,但是超越了潛在增長率則產生不好的結果。
第一個結論,潛在增長率不應該被超越。當我們說中國經濟要減速,或者更學術化一些講潛在增長率下降的時候,學者跟政府官員往往在一點上可以說是一拍即合。學者就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出很多建議,如加快城市化速度可以產生巨大的投資需求,從而搞很多的建設,中西部發展仍然需要對基礎設施的投入,在中西部“鐵公機”的建設是有需求的。政府也覺得,就學者們提的這些新增長點而言,都有駕輕就熟的手段、有實施的抓手,而且過去干得也很成功。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一點,過去搞區域發展戰略,如西部大開發戰略,目的是為了達到區域間均衡發展。而現在在學者的鼓動下,這個政策一旦變成意圖超越潛在增長率的手段,味道就變了。過去我們嘗試著去占領一些戰略性的新興產業,摸索動態比較優勢,出臺了很多產業政策。對這些新興產業給補貼,給更多優惠政策,刺激這些產業的投資,政府參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但是現在也變成了超越潛在生產率的手段。遭遇金融危機,政府出臺4萬億的刺激計劃,現在我們發現這個政策也能刺激經濟增長,超越潛在增長率。政府熟知這些政策,跟學者提出來的經濟增長點建議也正好合拍。 在市場顯示出資本報酬已經下降的情況下,過度的產業政策,給錢給補貼給土地,給其它的優惠政策,最后的結果是造成包括產能過剩在內的一系列扭曲。
在圖8中,上面這條橫線是中國工業的平均產能利用率。圖中顯示出,有一些產業的產能利用率明顯要低于平均值,產能嚴重過剩。而這些恰恰是過去受到產業政策鼓勵,給予優先發展的產業,比如鋼鐵、汽車、裝備制造業、石油化工、有色金屬等等。我們的產業政策過度使用傾向顯然需要進行調整。
還有一個例子,說明過度實施的區域政策可能導致產業結構偏離比較優勢。用政府引導的方式,把大量的資本投到中西部地區建設重化工業,必然造成了產業的過度資本密集。我們用一個資本勞動比指標來衡量這一點,即資本作為分子,勞動作為分母。這個比率的提高,就意味著產業的資本密集度提高。我們比較了一下,制造業的資本勞動比,目前中部和西部地區已經大大高于東部地區(圖9)。這些發達程度較低的地區資本密集度高于沿海地區,說明其已經偏離自身比較優勢。本來,區域發展戰略應該著眼于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減貧。過度使用這種戰略,就會造成實際增長率超越潛在增長率的不良結果。
上述這些都是已經出現的苗頭。假如學者告訴政府決策者,“十二五”期間潛在經濟增長率是7.2%,“十三五”期間只有6.1%,而政府不喜歡這樣,就會用原來熟知的辦法去刺激經濟增長,超越潛在增長率,眼前的這些端倪就會變成未來現實中的錯誤。在出現減速趨勢的情況下,我們距離犯錯誤的目標就越來越近了,不正確的認識和政策傾向傷害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可能也就加大,離我們想糾正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意愿也就越來越遠了。
日本是一個最好的反面教員。圖10中的曲線部分是日本的人口撫養比。它在下降的過程中,意味著有充足的人口紅利可以獲得。在它下降的20多年間,日本實現了9.2%的高速經濟增長。最后降到最低點,又持續了20年左右處于低點。它的潛在增長率就大幅度跌下來。對此日本民間不甘心,政府也不甘心,就開始用各種各樣的刺激手段,貨幣政策始終寬松,財政政策保持擴張性。日本跟我們很像,不遺余力地實施過區域發展政策、產業政策和宏觀經濟的刺激方案。我們最熟知的就是它刺激房地產發展,結果造成了嚴重的泡沫經濟。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個泡沫終于破滅了,然后,隨著人口撫養比上升即人口紅利消失,日本經濟就陷入到長達20年的零增長。
圖10中顯示出日本在1990年以后每年的增長率是0.85%,是加上了通貨膨脹率的調整,因為它的通貨膨脹率這20年是負的。如果不用調整,它只有0.24%的增長率,基本上就是零增長。所以說日本在兩個意義上是完美的例子,第一個是說它的經濟增長和人口紅利是密切相關的。第二個是說它努力嘗試去超越潛在增長率,但是最后的結果是欲速則不達,不僅沒有真正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反而陷入到了長達20年的停滯,或者叫“失去的20年”。
剛才是一個結論,結論就是潛在增長率是不應該超越的。人們都說經濟學是一個陰郁的科學,它不僅表現在經濟學關心的這些事都比較枯燥,還表現在總是告訴我們一些壞消息。不管怎么樣,人們還是喜歡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再來十年,最多二十年的9%或者10%的增長速度,就理直氣壯地進入到發達國家的行列了。潛在增長率的估算結果卻沒有告訴我們這個好消息。現在我們的潛在增長率是7.2%,幾年以后又會變成6.1%,我們對這個趨勢有沒有辦法呢?因此我要講第二個結論:潛在增長率是可以改變的。
如何提高潛在增長率
當人們在說,未來二十年中國還可以有高速經濟增長的時候,我們需要問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你所指的高速經濟增長是指多少?在世界范圍內說7%甚至6%也可以是高速增長,不一定是指8%、9%或者10%。第二個問題,你想要的高速增長是用什么辦法達到的?用刺激需求的辦法達到更高的增長速度的辦法,我認為是不可持續的,是必然傷害中國經濟的。也就是說,當我們說“潛在增長率是可以改變的”,也包括潛在增長率還可能因為錯誤的政策傷害了生產要素的供給或者生產率的提高而降低。如果像日本一樣失去20年,我們就成了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國家。
如果政策得力,提高了潛在增長率會怎樣?這就是我們要探討的問題。這是正確的選項,但是我們怎么提高它呢?我們也做了一些模擬。我們先從潛在增長率究竟是什么講起。形象地說,潛在增長率就是運動員的體能和人類的極限,是科學所定義的運動員應該跑的速度。運動員的速度受到他(她)的身體能力和人類身體極限制約。而他(她)想超越潛在速度的壓力是巨大的,來自于廣告商、主管部門、外行的社會大眾。結果如何呢?也許可以超越一時,但是受傷的概率一定會高,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他們受傷的頻率到底有多高了。這就是潛在增長率。
因此,就潛在增長率的含義來說,我們關心的就是勞動力供給如何,資本供給如何,生產率能有多快的提高。如果你改變了這些東西,還有可能讓它更好一些。比如說我們從某某近鄰國家,引進一個億跟中國農民工一樣素質,一樣工資水平的勞動力,我們就重新又回到人口紅利了,那么回到10%的增長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事情哪有這么簡單。因此,我們做了一點假設和模擬。
圖11顯示的是不同勞動參與率下的潛在增長率,實線表示的是在前邊做的那些假設下,所具有的潛在增長率。勞動力是負增長,即前面說的15到59歲能夠作為勞動力的人口在下降,但是,如果提高勞動參與率,則可以抵消這個下降的效果。因此我們模擬了一下,假設從2011年開始到2020年期間,我們的勞動參與率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GDP的潛在增長率就變成實線所表示的那樣了,也就是說可以提高大約0.88個百分點。只是這一個因素,即可以改變潛在增長率。
勞動參與率怎么提高?最經常提到而且有關部門也在醞釀的辦法是延長退休年齡。比如本來應該60歲退休,如果延遲到63歲退休,當然就會提高勞動參與率,增加勞動力供給。但是筆者前面說了,我們的勞動年齡人口到60歲上下的時候,受教育程度大幅度下降。這代表人力資本也好,學習新技術、新技能的能力也好,在這個年齡上都大幅度下降,實際上他是不能適應繼續工作的,因為沒有人愿意雇他。強行從法律上把退休年齡向后延,意味著這部分人失業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勞動參與率實際上并沒有提高。目前這條路對中國來說走不通。有人問美國為什么能走通,那是因為美國人在各個年齡段受教育程度是一樣的。
還有一個理論上提高勞動參與率的好辦法,即降低失業率。不過,我們現在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只有4.1%,已經很低了。根據筆者的同事估算,這4.1%其實就是自然失業率。自然失業率是很難再下降的,因為在結構上和摩擦系數上總要有一些失業,所以也沒有特別大的降低余地。真正提高勞動參與率的空間在于戶籍制度改革,即推進農民工勞動力供給的穩定化和充分化。目前,官方用常住人口定義的城市化率是51%。而用非農業戶口人口比例定義的中國特色的一種城市化率,則只有35%,中間有16個百分點的差距,就意味著有1.6億農民工被統計為城市人口,但是沒有得到城市的戶口從而沒有均等地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務。
由于這些人沒有得到充分的社會保障,因此他們就不可能一直干到六十歲或者五十幾歲。因為家里有老人和孩子要照顧,他們可能四十歲上下就退休回家了。他們也不享受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因此他們的勞動力供給是不穩定的,2009年春節期間,中國經濟遭遇到金融危機外來的沖擊,許多農民工就返鄉了,因為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是最早承受沖擊的群體。因此,在現行的戶籍制度下,這些勞動力的供給是不穩定的,他們的勞動參與率是比較低的。雖然他們回去還要勞動,但是對于非農產業的勞動參與是很低的。所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解決這個問題,可以產生一石三鳥、立竿見影的增長效果。
在黨的十報告中,第一次提到要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戶籍制度改革以后,農民工變市民了,很自然他就可以成為穩定的勞動力,該什么時候退休就什么時候退休。因此就改變了勞動力供給的這條線,進而改變了所有經濟增長的要素條件,潛在增長率直接就可以得到提高。這也就意味著,公共政策可以起到替企業家來加大農業勞動力轉移力度的作用,而不是完全靠工資上漲。目前大家為了爭取雇到農民工就只好漲工資,每年農民工工資以12%的速度增長,2011年更高達21%,再漲下去企業家也受不了。農民工轉移得到了戶口,意味著政府在制度上給它更好的激勵,市民化還會加大轉移力度,帶來的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改進以后,也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
此外,農民工得到基本公共服務,有了社會保障,解除了后顧之憂,他們就可以像城市居民一樣來消費。過去他們一個是消費的例外群體,人在城市生活,工資也在不斷漲,甚至跟很多市民掙得差不多,但他們絕不會像市民那樣消費,而是把錢攢起來帶回老家。如果他們能像市民一樣消費,內需中的消費需求會有大幅度提高,我們的經濟增長就變得更平衡、更協調、更可持續了。
很多人要問,既然劉易斯轉折點已經過去了,人口紅利也消失了,還有多大的農業勞動力轉移潛力呢?看上去好像沒有那么大的潛力了,其實不是。所謂劉易斯轉折點,就是指你用不變的工資雇不到人了。2004年以前,所有的老板都是用幾十年不變的工資招農民工,都有人來干。但是從2004年以后,你再拿六百塊錢、八百塊錢招工就沒有人干了。但是它絕不意味著說沒有勞動力了。我們做了一個比較,從目前算起直到2020年,中國處在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門檻跨越的階段上,人均GDP應該落在6000美元到12000美元。我們把處在這個階段上的國家挑出來,它們農業勞動力的比重比我們要低很多,平均要低10個到20個百分點。即按照官方統計,我們現在還有35%的勞動力在務農。我們的研究發現官方是高估了,我們給它降了10個百分點。即使按照我們的估算值,我們也仍然比這些處在6000-12000美元人均GDP的國家高10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今后十年每年降一個百分點,差不多就有800萬的農業勞動力還要轉出來。因此,戶籍制度改革可以繼續挖掘人口紅利,延長過去的人口紅利,提高勞動參與水平。
我們還做了一個模擬,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以后會有什么結果。我們假設,未來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增長率比以前的假設高一個百分點(圖12)。即到2020年之前,我們原來的趨勢是全要素增長率每年增長3%,如果把它變成4%,經濟增長速度也會明顯上升,潛在增長率會增加接近1個百分點,會在7.2%的水平或者6.1%的水平上再加一個百分點。這是非常現實的假設,是提高潛在增長率的一條重要途徑,非常值得我們去做努力。經濟學理論和其他國家經驗顯示,有一些我們過去認識到的或者沒有認識到的途徑,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我們看到的全要素生產率通常有兩條提高途徑,一是技術進步,對中國來說也有很多捷徑可走。我們在技術上是和發達國家有差距的,這給我們帶來一個后發優勢,我們不用在所有的領域都去自主創新,有所為有所不為。當然,這不代表我們不可以獨立自主進行科技創新,而是說我們可以借鑒很多現成的技術。
如圖13所示,瑞士代表的是科技最高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我們和國際上的科學技術前沿有多大的差距。筆者用的這個指標是一個國家被引用的數量做分子,分母是這個國家發表的全部論文數,反映發表的論文是不是科學的,是不是高水平的。如果你發表的不是在技術前沿上,就沒有人會引用,這個比值就是零。世界上最高水平依次是瑞士、美國、英國等等,中國是在較低的水平,相當于瑞士水平的1/5。也就是說雖然我們發表科學論文的總量上來了,但是它的質量并不高,并意味著我們尚未處于科技創新的前沿。這個差距我們當然要趕上,目前存在的這個差距也可以說是后發優勢。發達國家在每一個點上都得自主創新,而我們可以利用別人研究出來的成果,掌握起來就要簡單的多,成本低得多。這種趕超過程中的技術進步,可以算是一條捷徑。
還有一條途徑就是資源的重新配置效應。從圖14中,大家可以看有三種方式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我們以往熟知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是從農業把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轉到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整體經濟的生產率就提高了。但是,隨著剩余勞動力的減少,勞動力轉移速度減慢,從這個過程獲得的全要素生產率相對會越來越少。接下來你會發現在二產內部,每個行業之間還是有生產率差別的。如果你能把生產要素從生產率低的行業轉移到生產率更高的行業,還能帶來資源重新配置效應。更進一步,在一個行業中,企業之間的效率也是存在差異的,有的企業在全要素生產率上持續進步,有些企業則是靠政府補貼才能茍延殘喘,近似僵尸。在這種情況下,你讓僵尸企業死掉,讓有生產率進步的企業去得到更多的資源,甚至兼并其它的企業擴大自身規模,最后的結果整體經濟的效率則會更高。
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潛力我們遠遠沒有開發殆盡。一項研究表明中國企業之間的生產率的差距非常大。比如,我們行業內企業間的生產率差距,用不同的指標表達都比美國高。如果同一個行業中,企業之間生產率差距非常大,這就意味著你沒有把生產率低的企業淘汰掉,也沒有讓生產率高的部門把其它的企業資源拿來擴大它的自身規模。因此就很自然的說,如果我們達到更好的配置,比如說達到美國的水平,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可以提高30%-50%。還有一項研究,是以美國為代表進行的。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企業之間進入和退出、成長和死亡,這種創造性毀滅過程,所能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的進步,占到全部生產率進步的1/3到一半。
上述兩個不相關的研究,得出的可以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數量級卻是一樣的,結果這么巧合與一致,說明我們還沒有把這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途徑的機會加以利用。最樂觀的一種思維方式,就是看到我們哪個地方差,就說明那個地方我們有巨大的潛力。因此未來讓企業生生死死成長消亡,可以期待獲得巨大的全要素生產率的來源。為此我們需要改革。為什么現在我們的企業該死的不死,該壯大的不能壯大,因為是有各種各樣的歧視和準入壁壘。筆者并不只是說歧視非公有經濟,更多的是歧視小企業,歧視新成長企業,甚至地方政府會人為的挑選贏家,官員們總是覺得政府能判斷誰有發展潛力。
篇(11)
共同富裕公平優先。四中全會提出走向共同富裕,意味著降低貧富差距成為主要使命,將讓增長惠及更多低收入階層。預測將會有更多的公平類政策出臺,分別對應保障市場公平競爭、促進要素公平交易、加強收入公平分配三大類。
小政府與大市場。保障市場公平競爭的核心是重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過去中國經濟是投資驅動、政府主導,大政府小市場,而未來則應逐漸過渡到小政府、大市場。其中財稅改革將重新定義政府的財權和事權,行政改革將放開政府的行政管制,國企改革將打破國企壟斷,而司法改革則為所有經濟主體的公平競爭奠定基礎。
資本品價格趨降、勞動力價格趨升。過去中國的資源品、土地、資金和勞動力價格均存在人為的管制,而未來對要素供給以及價格的管制將逐漸放開,而其價格將反應各類要素本身的供需狀況。過去資源品、土地、資金的供給被壟斷,導致價格虛高,而勞動力價格被低估,未來其走勢或恰好相反,資源品價格改革、、金融改革有望降低資源品、土地和資金價格,而戶籍改革或將提升勞動力價格。
降息周期開啟。2013年政府試圖高利率去杠桿,但日本經驗表明高利率或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而2014年以來由于房價下跌,央行已重新開啟降息周期。從年初回購利率封頂,到年中的回購利率下調,再到年底的存貸款利率下調,均預示降息周期已逐步展開。
經濟去杠桿。產能過剩、PPI通縮下制造業仍將去杠桿,人口紅利拐點下房地產及居民部門難以加杠桿,政府部門是加杠桿主力,但難以完全對沖,預計2015年GDP增速降至7%。
金融加杠桿。而觀察美國去杠桿經驗看,在經濟去杠桿的同時,金融在加杠桿,體現為股市、債市的同時上漲,而美聯儲的零利率政策以及貨幣量化寬松則為金融加杠桿提供了資金來源,而這一模式正在日本、歐洲上演,未來或在中國重演,未來央行降息量寬均將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