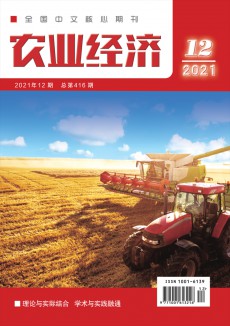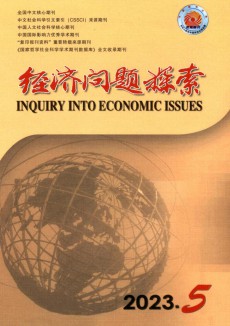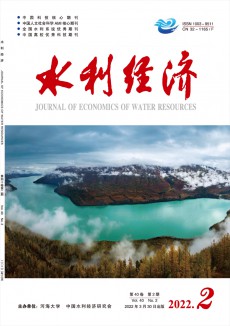淺談自然災害對經濟的影響
時間:2022-07-05 08:56:58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篇淺談自然災害對經濟的影響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淺談自然災害對經濟的影響:自然災害對吉林省經濟增長的影響
摘要:自然災害對吉林省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大,自然災害損失與國民經濟損失的變化成正比例關系。自然災害損失高的年份,國民經濟損失也相對較高,自然災害損失低的年份,國民經濟損失也相對較低。自然災害對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具有較大的負面影響,給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困難,不利于整個經濟系統的正常運行。若能夠采取有效的防災減災措施,降低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和影響范圍,總損失能夠大幅度的減少,吉林省的經濟也能夠更加快速的發展。
關鍵詞:自然災害;災害損失;經濟增長;投入產出模型
我國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尤其是最近幾年,地震、干旱、洪澇、泥石流等自然災害頻頻發生,造成的損失非常嚴重。自然災害對經濟的影響不僅限于直接損失,更重要的是間接損失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目前,我國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來分析自然災害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對自然災害造成經濟損失的計量方法的研究也不多見。對災害造成的損失進行科學的分析和測算,可以避免和減少因人為的主觀臆斷而造成的決策失誤,為制定防災減災政策提供客觀、科學的依據。
一、吉林省主要自然災害
吉林省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特征決定了吉林省自然災害種類多、范圍廣、程度深、危害大,每年干旱、洪澇、地震、風雹、低溫冷凍、山體滑坡和泥石流、森林和草原火災、病蟲害等各類災害均有不同程度發生,其中旱災、水災、風雹災和霜凍災是吉林省的主要自然災害。
吉林是干旱發生較多的地區,也常是重旱區,干旱主要出現在春、夏季節,以春旱居多。春旱影響春播作物播種、出苗及幼苗生長;夏旱則影響農作物正常生長發育,甚至造成減產。水災主要發生在每年夏季主汛期,吉林省中部和南部地區暴雨和冰雹天氣時有發生,三江平原地勢低洼,因為排泄不暢,容易產生漬澇,遼河下游和松嫩平原是受澇次數較多的地區。“西旱東澇”是吉林省的旱澇分布特點。東北地區緯度較高,大陸季風氣候明顯,各年的天氣氣候情況變化較大。有些年份作物生育期內會遇到低溫冷害天氣,熱量不足。作物不能正常成熟,造成減產,最容易遭受低溫冷害的作物是水稻和高梁,其次為玉米和大豆。霜凍主要是秋季的早霜凍危害大,這期間作物尚未成熟、收割,容易受凍而減產。春末至初秋期間的降雹也可對農作物造成危害,在春小麥成熟期及玉米、高梁等作物抽穗開花期如降較大冰雹對作物危害較重。
二、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
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包括直接經濟損失和間接經濟損失。直接經濟損失是指自然災害直接造成的物質形態的破壞,不含任何中間環節和間接的經濟損失,一般可以用市場價格來計算。間接經濟損失是指災害發生時或發生之后除可直接計算的直接經濟損失之外所造成的損失,如因自然災害使企業停減產造成的損失,或者因暴雨洪水導致農作物減產欠收而引發市場糧食價格上漲引起消費支出增加造成的損失。間接損失主要包括間接停產損失、中間投入積壓層損失和投資溢價損失。間接停產損失是指由于經濟活動的關聯性,生產單位、行業和部門有著緊密的投入產出連鎖關系,一個企業的停產會間接地影響有投入產出關系的其他企業的產出,即使后者的生產功能并未受到災害的直接破壞;中間投入積壓層損失是指由于生產的停滯,造成材料和半成品的積壓增加,這種積壓的增加造成資金占用增加的機會損失;投資溢價損失是指災后的恢復過程中需要動用沒有災害時可用于生產性投資的資金加以彌補,這種由于財產補償引起生產性投資減少所產生的機會損失稱為投資溢價損失。[。’
民政部曾會同國土資源部、水利部、農業部、國家統計局、地震局、氣象局和海洋局等部門對2009年全國自然災害損失情況進行了全面會商和核定,結果表明:2009年以來全國各類自然災害共造成了約4.8億人(次)受災,死亡和失蹤1528人,緊急轉移安置709.9萬人(次);農作物受災面積4721.4萬公頃,絕收面積491.8萬公頃,倒塌房屋83.8萬間,因災直接經濟損失2523.7億元,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帶來了嚴重影響。2005年,吉林省遭遇了較為嚴重的水旱兩災,大暴雨引發的洪水使河堤決口、損壞鐵路、公路、輸電線路,損壞房屋12.5萬間,絕收面積達到66萬公頃,轉移安置人口9.7萬人。2009年,吉林省遭遇了較為嚴重的旱災,受災面積244萬公頃,糧食產量同比下降13%以上,部分地區減產三至四成,糧食質量也有所下降。
三.自然災害損失的評估
自然災害損失的評估主要是對間接損失的評估,本文使用投入一產出模型對其進行分析計算。
1.農業損失的評估
投入產出模型是根據投入一產出原理建立的一種經濟數學模型,投入是指從事一項經濟活動的消耗,產出是指從事經濟活動的結果。對于自然災害損失而言,主要是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的損失,本文運用產品均衡投入一產出模型評估總產出的損失,在利用投入一產出表進行實際分析時,考慮的問題要更復雜。由于自然災害對農業的影響最大,且農業直接經濟損失的統計數據相對于其他產業損失較為容易搜集和計算。因此,我們借鑒相關研究,以農業為例,建立災害損失評估模型,分析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
假設災害發生之前的經濟系統是一個運行良好的系統,并假設系統的結構比例關系在災害發生之后沒有發生變化,本文按照這種結構比例關系來分析災害所造成的損失,以吉林省統計局2007年編制的42部門的投入一產出表來計算農業受自然災害影響的總損失。農業損失既包括了最終產品的損失,又包括了間接經濟損失。因此,本文將農業損失看成農業部門的總產品的損失,并假設其他部門的最終產品不變,根據2005年至2010年吉林省農業統計年鑒中農業直接經濟損失的數據,利用投入一產出模型計算出吉林省2004—2009年農業間接經濟損失和農業總損失,計算結果見表1。
2.受農業損失影響的各部門總產出損失的評估
根據整理后的投入一產出模型,我們計算出受農業損失影響的各部門總產出損失,計算結果見表2。通過上表可以看出,農業總損失對其他各部門總產出的影響是不同的。以2008年為例,農業總損失對食品制造業及煙草加工業的影響最大為7.6億元,占除農業以外其他產業部門總損失的24.2%;其次是化學工業的損失為6.7億元,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的損失為3.2億元,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的損失為2.2億元、分別占其他產業部門總損失的21.4%、10.3%和7%。這主要是因為受自然災害影響造成糧食、水果蔬菜和煙葉等產品產出下降,進而使食品制造業及煙草加工業受到一定程度損失。因農作物產量的減少,以農產品作為原料、燃料的產業也受到間接影響,如石油加工業、煉焦業及核燃料加工業等。通過上表也可以看出,農業災害損失對公共管理、社會組織、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的影響很小或沒有影響。
3.自然災害造成的總損失
和其他產業部門相比,農業受自然災害的影響最大,災害造成的損失也最為嚴重,但農業是我國的第一產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它的地位決定了農業對其他產業的相關影響非常大。嚴重的自然災害可以造成農作物大面積減產或絕收,進而會對以農副產品為主要原材料的工業及服務業等相關產業產生直接的影響,并波及到城鄉居民的日常生活水平與質量,進而影響整個經濟的正常運轉。因此,在本文中假定自然災害造成的總損失為農業總損失與受農業損失影響的其他部門產出損失之和,計算結果見表3。
四、自然災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
自然災害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對原材料、中間品、生產設備、廠房、基礎設施等有形資本的損毀,還通過推遲當期消費,增加強迫性儲蓄,從而降低社會總需求,影響社會總產出水平等方式來抑制經濟增長。在分析自然災害損失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中,本文主要應用哈羅德一多馬模型進行分析。
為了分析災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將災害損失分為需要重置的損失和不需要重置的損失兩類。需要重置的損失是在受災后需要恢復重建部分的損失,不需要重置的損失則是在受災后不需要恢復重建部分的損失。需要重置的損失將使本來可用于投資其他項目的資金用在災后恢復重建上,對經濟增長會造成一定的影響,而不需要重置的損失則沒有。本文假設所有的災害損失都是需要重置的,即總損失就是重置損失,全部積累均轉化為投資。
設第t年災害經濟損失中需要重置的部分為Lt,若沒有災害發生,假設恢復重建的資金Lt可以全部用于其他項目投資,則經濟增長率將變為式(1):
用資本形成總額代表第t年總投資,即第t年的新增資本存量,所需數據來源于2010年吉林省統計年鑒,自然災害損失數據來源于表3。為了使計算口徑一致,在計算實際經濟增長率時要消除價格變動的影響,將2003—2009年各年的地區生產總值、資本形成總額和自然災害損失額全部轉化成以2000年的不變價所表示的換算值,以便于在計算國民經濟損失時進行橫向比較。根據上面的公式計算出的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2004—2009年,受自然災害的影響吉林省經濟增長率平均每年減少0.4%,和平均實際經濟增長率14.1%相比,還比較少,但是如果這種減少持續若干年,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將不容小視。
通過表5可以看出,消除了價格變動的影響,2004~2009年吉林省國民經濟因自然災害造成的平均損失達到了21.43億元,最高年份2009年達到了39.9億元。自然災害損失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最低為0.13%,最高達到了4.53%,平均比重為2.02%。吉林省國民經濟損失與實際自然災害損失變化中兩個明顯偏高的年份是2005年和2009年。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自然災害對吉林省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大,自然災害損失與國民經濟損失的變化成正比例關系,變化幅度也大致相同。自然災害損失高的年份,國民經濟損失也相對較高,自然災害損失低的年份,國民經濟損失也相對較低。自然災害對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具有較大的負面影響,給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困難,不利于整個經濟系統的正常運行。若能夠采取有效的防災減災措施,降低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和影響范圍,總損失能夠大幅度的減少,吉林省的經濟也能夠更加快速的發展。
淺談自然災害對經濟的影響:突發性自然災害對經濟結構的影響研究
摘要:突發性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生活和生產資料損失,通過物質效應、心理效應和破窗效應等渠道作用于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進出口,從而影響到經濟結構;以2007年8月湖南省突發性洪災為例,說明自然災害對湖南省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進出口所產生的實際影響,同時印證所提出的作用機理。
關鍵詞:突發性自然災害 經濟結構 作用機理 湖南省
一、引言
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少數國家之一。據統計,在2010年全世界導致死亡和失蹤人數最多的十大自然災害中,有三起發生在中國,其中兩起為突發性自然災害。頻發的突發性自然災害給人民群眾帶來物質損失,還影響到宏觀經濟的發展。因此,正確認識突發性自然災害所產生的經濟影響,以提高應對能力,已經是實現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突發性自然災害與經濟增長之間是什么關系,經濟學家對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雖然多數觀點認為災害對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但也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如鐘宏和劉國寧提出,2008年雪災對經濟的影響短暫有限,經濟在災后將迅速回到正常軌道,并且極有可能在一些領域出現報復性增長。由于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有很多,難以得到關于突發性自然災害影響經濟發展的一般結論,更需要進行案例式研究。綜上,現有文獻多數集中探討突發性自然災害對微觀損失和宏觀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較少基于中觀的視角展開論述。本文基于災害經濟學和經濟發展理論,研究突發性自然災害對經濟結構的影響。
二、突發性自然災害影響經濟結構的作用機理
突發性自然災害由于事前難以及時預測,因此一旦發生,社會往往會因為猝不及防而遭受重大損失,并通過一體化網絡對全局帶來影響。災害所造成的損失可分為生活和生產資料損失兩種,這些損失通過物質效應、心理效應和破窗效應等渠道作用于消費、投資、進出口和政府支出,從而影響到經濟結構(圖1)。
物質效應是指突發性自然災害給經濟主體帶來直接物質損失,從而影響到經濟決策和經濟發展。心理效應說的是突發性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物質損失,通過影響到經濟主體的心理狀態而作用于經濟決策和經濟發展。破窗效應則指經濟主體面對自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進行資產更新以最大限度減少損失和促進經濟發展。下文分別具體論述突發性自然災害如何通過上述效應影響經濟結構。
(一)突發性自然災害對消費的影響
突發性自然災害主要是通過影響居民的財富變化來影響消費。對居民來說,發生自然災害意味著生活條件遭到破壞,甚至是人員傷亡。這些都會減少居民財富,進而導致消費水平下降。另外,自然災害會導致災區物價上漲,使居民因實際財富減少而降低消費水平。總之,自然災害在短期內會使居民的消費量下降。然而根據持久收入假說,居民的消費支出不僅僅取決于當前的財富狀況,更取決于其持久收入。因此,居民的消費水平在災害初期下降之后,如果災民得到及時救助,人們預計持久收入不會劇烈減少,加上災后剛性需求,消費水平將恢復并保持正常水平。
(二)突發性自然災害對投資的影響
突發性自然災害對投資的影響包括兩個層次:首先,自然災害會造成生產設備毀損,打亂原有的投資計劃,使投資不能順利進行。同時由于預計到居民的需求短期內會下降,企業也會放緩投資步伐。因此,企業的投資規模在短期內必定會減少。其次,災害發生后為了盡快恢復生產,企業會進行災后重建,增加投資,進而通過產業鏈的作用帶動整個產業的投資。
(三)突發性自然災害對政府支出的影響
突發性自然災害對政府支出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災害造成政府自身的損失,為了正常履行政府職能,政府需要增加支出以彌補自身損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災后重建對財政支出的影響。突發性自然災害造成道路等基礎設施毀損,而基礎設施作為公共產品,只能由政府投資建設。加上部分群眾災后可能無法達到基本生活標準,財政支出也得涵蓋此類社會保障。綜上所述,突發性自然災害將大量增加財政支出。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增加不可能沒有限度,會受到財政收入的制約,且突發性自然災害還會減少稅收。當財政支出接近上限時,總量將基本保持穩定,主要進行結構調整。
(四)突發性自然災害對進出口的影響
突發性自然災害對進口和出口的影響不盡相同:第一,災害導致交通不暢,從而造成物流受阻,進出口無法順利開展。第二,自然災害會破壞企業的生產要素,造成企業生產能力下降,從而減少出口額。未受災害影響的企業此時為彌補國內空缺,將優先滿足國內需求,這也會減少出口。第三,由于自然災害造成災區生產能力下降,導致一些商品供應不足。為了滿足需求,將會增加進口。總之,突發性自然災害將減少出口,對進口的影響則表現為先減后增。
三、突發性自然災害影響經濟結構的案例分析
洪災的數量和造成的經濟損失占我國各種自然災害的1/3左右,造成的人員傷亡更超過一半,同時我國爆發的洪災都為區域性的。本文選取2007年8月湖南省突發性洪災為例,論述其對該省經濟結構的具體影響。
(一)2007年8月湖南省突發性洪災概況
受2007年第9號超強臺風“圣帕”影響,8月19日至24日,湖南省普降暴雨和特大暴雨。暴雨中心永興縣鯉魚塘鎮70小時降雨863.3毫米,比湖南省有歷史紀錄以來最大3天降雨量671.9毫米多191.4毫米,暴雨頻率達千年一遇①。截至23日8時,湖南共有5市440個鄉鎮、336.78萬人受災。
(二)洪災對湖南省消費的影響
洪災給湖南省帶來巨大的直接物質損失,因災死亡2人,直接經濟損失總計達46.92億元。損失直接導致居民財富減少,部分商品尤其是蔬菜的價格出現小幅上漲。這些因素影響了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和預期,迫使消費減少,2007年8月湖南省社會零售品消費總額降到264.7億元。由于洪災持續時間很短,加上災后政府積極組織重建和平抑物價,居民的消費信心和實際購買力得以維持。同時由于剛性需求,社會零售品消費總額在9月份出現大幅上漲,恢復到災前的消費水平,且此后繼續保持較高的水準。
(三)洪災對湖南省投資的影響
洪災打斷了災區企業正常的投資活動,導致1548個工礦企業停產,僅工業交通運輸業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達12.55億元。在2007年8月,湖南省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額僅為307.6億元,創下了5月份以來的新低。洪災過后,湖南省企業積極開展災后重建,增加新投資以恢復生產能力。在2007年9月,湖南省城鎮固定資產投資額增加到389.9億元,比8月份增長了26.8%。
(四)洪災對湖南省政府支出的影響
洪災給災區人民的生活帶來極大沖擊。為了保障災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湖南省民政廳災后向株洲、郴州和衡陽等3個受災最嚴重的市分別下發200萬救災資金、1000床棉被和100頂帳篷。更重要的是,災區的基礎設施在洪災中受損嚴重。如全省損壞提防3230處,損壞輸電線路1050.4千米。要修復這些設施需要大量的政府投資。在2007年9月,湖南省財政支出比8月增加了42.8%。洪災給湖南省帶來的直接經濟損失占湖南當年財政支出的3.7%,根據相關標準,災害對財政的影響較大。
(五)洪災對湖南省進出口的影響
洪災嚴重損壞道路交通這一經濟動脈,導致湖南省進出口物流受阻。截止8月22日11時,造成湖南省2條國道、6條省道和42條縣鄉公路交通中斷。郴州是湖南的“南大門”,也是這次洪災的重災區之一,境內106國道、5條干線公路、23條縣鄉公路中斷交通②。洪災還導致部分出口企業停工,其他企業的部分生產能力轉為滿足國內市場。2007年8月湖南省出口額只有52941萬美元,在9月份進一步下滑到51506萬美元。災后重建大大提升了湖南省的進口額,2007年8月和9月,湖南省進口值連續兩個月超過3.2萬億美元,這也是從5月到11月湖南省進口額超過3萬億美元僅有的兩個月。
四、結論和啟示
本文以2007年8月湖南省突發性洪災為例進行分析,結果表明洪災首先抑制了湖南省的消費和投資水平。但隨著災后重建的展開,消費和投資迅速恢復并增長。洪災帶來的直接經濟損失占湖南當年財政支出的3.7%,對財政影響較大。災害對湖南省進口和出口的影響不盡相同,8月份和9月份湖南省的出口額連創新低,但進口強勁。此次洪災對湖南省經濟結構實際造成的影響,驗證了本文所提出作用機理的合理性。上述結論對救災有諸多啟示:
第一,救災時信心比黃金更重要。分析表明: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降低突發性自然災害所導致的巨大物質損失固然十分重要,但對災后重建工作影響更深遠的卻是心理預期。政府如能在面臨突發性自然災害時展現強有力的災害管理能力,有利于人民群眾塑造對未來良好的預期,將通過心理效應促使消費和投資盡快恢復以步入自我良性發展的軌道。
第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突發性自然災害往往直接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破壞基礎設施,從而抑制進出口和導致財政被動支出。雖然我國政府早已提出要建立公共財政基本框架,但直到現在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支出的比重仍然偏低。鑒于此,政府應切實增加上述支出,以增強抗災能力。當面臨突發性自然災害時,更要及時調整財政支出來滿足救災需要。
淺談自然災害對經濟的影響:以民諺論自然災害對游牧經濟的影響
一、“家有萬貫,帶毛的不算”———游牧經濟本身的脆弱性
北方游牧民族的經濟財富從其生產資料和生產方式來看,牲畜是作為財富的象征而存在的,牲畜的多寡可以代表一家牧民的經濟水平。牲畜作為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根本,如同農作物之于農業民族一樣,它的繁殖好壞直接關系到游牧民族的生存。歷史上常有“牛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的描寫,可見牛馬等牲畜與游牧民族之利害關系。“家有萬貫,帶毛的不算”形象地道出了游牧經濟的脆弱性。
《舊唐書》中有“突厥興亡,唯以牛馬為準”,隨后又記載說“六畜疲羸,人皆菜色”,最后得出突厥不久將亡的結論,果不其然,隨后東突厥被唐所滅。國即如此,以牛馬富,可侵掠中原,而牛馬少,自身難保。《元史?明宗紀》載“天歷二年(1329年)五月,趙王馬札罕部落旱,民五萬五千四百口不能自存”。可見以牲畜作為財富的象征具有很大的風險性,“面對自然災害牲畜的抵御能力極弱,十分容易受到損害,需要快速及時地被轉移”。因此牧民用“家有萬貫,帶毛的不算”來形容游牧經濟狀況下,以牲畜作為財產計算的不穩定和脆弱。如果出現好的年份,風調雨順、水草豐美,牲畜的繁衍也會變得異常好轉,“牲畜上千,血水不干”的民諺很好地解釋了游牧經濟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單一性和脆弱性。
二、“寺院的喇嘛聽鼓聲,草原的牧人看天時”———自然災害的影響
游牧經濟的脆弱性和單一性是與自然環境相統一的結果。“游牧生產依靠于牧草,而牧草的生長要受到季節、氣候、載畜量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這種對于自然條件有極強依賴性的生產方式是很容易受環境影響而波動的。一旦遭遇自然災害,損失將十分嚴重,因此當地有許多民諺都體現了游牧生產者對自然天氣的關注和敬畏。如“寺院的喇嘛聽鼓聲,草原的牧人看天時”“清明節后落透雨,夏秋草茂牛羊肥”“牛蹄窩里水汪汪,天旱日子不會長”“螞蟻搬家上高山,洪水將要到草原”“冬季飛禽忙搭窩,草原一定有厚雪”“戰士抵不過一粒槍,富人最怕一場雪”等。
歷史上常見于北方游牧地區的自然災害有蝗災、旱災、雪災、寒災,史料中也多有這方面的記載。《史記》中記載太初元年(前104年)冬天“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漢書》中記漢宣帝時,匈奴壺衍鞮單于以萬騎擊烏孫,歸來時“會天大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十一”,于是丁零、烏桓、烏孫乘其弱而攻,殺其人、馬、牛羊,加上之前的惡劣天氣,使得匈奴大為虛弱“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原來依附它的周邊部落也四散而去,給匈奴以重擊。到了東漢初年,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太半”。每一次的災難都給匈奴部落帶來了重創。到了唐初,興起于草原的突厥部落也遭遇了同樣的狀況,唐太宗貞觀元年“其國(突厥)大雪,平地數尺,羊馬皆死,人大饑”,貞觀三年“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同年,鄭元壽入使突厥,回奏太宗“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為準。今六畜疲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內炊飯化而為血。徵祥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無幾,突厥果敗”,即貞觀四年(公元630年),由李靖率軍擒頡利,東突厥滅亡。到了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但是北方草原地區自然災害導致的后果仍然不可小覷。《元史》五行志中載“定宗三年戊申,野草自焚,牛羊十死八九,民不聊生”。
其他的北方民族如黨項、回鶻的衰亡也與自然災害緊密聯系,這與游牧民族自身的經濟方式有很大的關聯。游牧經濟產生于北方草原地區,自然環境相對于中原及其以南的農耕區而言,氣候條件相對惡劣,氣溫寒冷、干燥少雨、無霜期短。與之相適應的游牧經濟在此條件對環境的依賴性很強,經不起風霜雨雪等自然災害的襲擊。一旦遇見很容易造成人口、畜產的大量死亡,給牧民的生活、所在部落的生存帶來危機,也給牧民帶來一定的心理陰影,“由于災害的頻繁和劇烈,使畜牧業生產經常受到摧殘,在牧民的思想中便逐漸形成了一個幻覺,總認為自己的牲畜有個難以逾越的界限。”從而產生消極生產的惰性,對于畜牧業的發展和牧民生活的改善十分不利。因此看云、動物的狀態來識別天氣,以保全牲畜的方法,既體現了對大自然的依賴,也有利于牧民面對災害時進行提前預警,采取相應措施,減少災害帶來的損失。
三、“瘦馬怕泥滑,孕畜怕霜草”———畜養條件的限制
游牧經濟對自然條件依賴極強,它對牲畜的畜養條件也有諸多限制。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匈奴“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驘、駃騠、騊驈、驒騱”。而后的史書記載北方草原地區也多放牧這些牲畜,不同的牲畜對牧場環境有不同的需要,因此牧民根據馬、牛、羊等不同的種類進行放牧,以達到游牧經濟效益的最大化。
游牧經濟的主要構成要素包括牧民、草場、牲畜。這三個構成要素中牧民依靠牲畜生存,而牲畜的存活依賴于草場。草場的選擇是游牧經濟發展的首要條件,一旦草場出現丁點閃失,如前文所提到的自然災害,將會帶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這一方面十分重視,“地豐水草,宜羊馬”“隨季節而遷徙,春季居山,冬近則歸平原”,便是順應“今日行,而明日留,便畜牧而已”的游牧生產方式,選擇適當的草場來保證游牧經濟的正常發展。
《內蒙古紀要》中記述了關于草場的選擇:“春季雪融,則居低洼之鄉,以就天然水草,草盡而去,年復一年,都于一定境內,漸次轉移,其傾全力以采索者,惟水與草。至若冬季,霏雪凝冰,低地早已不得水,即草根亦被雪掩無遺,故必追居山陰,冰足以資人飲啖,草根之沒于雪者稍淺,家畜賴以掘食”。選擇好草場之后對于放牧也是有一套要求,根據不同的種類牧民采用不同的放養方法。羊的放養,需要常年跟人,夏季一般放兩次,早上起早放,中午趕回來飲水休息,下午太陽不再正當頭,再趕出去,落山前后再趕回來,冬天則因天氣寒冷,出去得晚,回來得早,且走不遠。駝不需要隨牧,可自由在草原上馳走。牛、馬為散畜,不要人放牧。馬群走得很快,牛群三三兩兩各走各的。馬吃起草來不分晝夜,天熱時尋陰涼,天冷時尋暖處,都不易找到。牛冬季是白天吃草,到了夏季則白天貪睡,夜里吃草不停。牛馬都能自己回家中飲水,方便牧養。《清稗類鈔》中也有這方面的相關記載。此外,對于牲畜的孕育繁殖、患病治療也有相應發達的技術,這些使得北方游牧經濟雖遭受人為和自然的打擊仍能夠發展,這也是我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自身發展中積累的豐富經驗。
四、“伏天雹打一掃光,人和牲畜都遭殃”與“麥在地里你別笑,收到倉里才牢靠”———畜存方式
“伏天雹打一掃光,人和牲畜都遭殃”“麥在地里你別笑,收到倉里才牢靠”,前一句寫了草原牧民的牲畜在夏天的一個日子里,遇上了冰雹,導致了人和牲畜處境困難,后一句寫了農夫在看見麥田里麥浪滾滾,心里樂開了花,但一轉眼就居安思危,認為只有收到倉庫儲存起來的糧食才能安心,在這之前,一丁點的天災就會毀了大好收成。面對自然災害,不同生產方式下的經濟活動,都會受到影響,但仔細深究,便會尋見差異———游牧經濟在天災下,人和牲畜都遭殃,而農耕經濟則是“收到倉里才牢靠”,并未提及有多大禍患的存在,而出現這種差別的原因則是經濟生產方式和儲存對象不同造成的。
游牧經濟是“以游牧的勞動方式,隨季節的變化而進行的有規律的循環往復經營畜牧業———四季輪牧為主的一切經濟活動”。游牧經濟以輪牧為其生產的主要方式,而這一生產方式將受到自然條件和畜養方式的影響,導致游牧經濟具有不穩定性和相對局限性,容易因為突如其來的風災、雪災等自然災害而導致牲畜大量死亡,牧民生活陷入饑饉。如《隋書?突厥傳》中記載沙缽略可汗時的一段話“種類資給,惟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饑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形象地描繪了由于這種“靠天吃飯”的牧養方式,使得人民處于茍且之中。同時這種以活的生物作為生產、生活的依賴對象,即儲存對象,本身就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例如草場的退化、天災的到來、牲畜的繁殖、戰爭的劫掠等一系列非常規因素的影響,都將會導致牲畜的大量死亡、失蹤。
相對于游牧經濟的這種不穩定和多變性,農耕區的經濟則相對穩定。首先,體現在其生產方式的穩定性。生產方式的穩定性表現在生產對象的固定性,在固定的農業耕作區內栽種適合該土地生長的植物,收獲糧食。這種生產方式同樣會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但相對較小,在自然災害較淺的時候,可采用灌溉等人為手段幫助農作物生長,而災害較重的年份,可吃上年的余糧,若來得及,也可“虎口奪糧”,影響并不會很大,當然若遇上“丁戊奇荒”這樣的年份,是很可怕的,但相比牧區還是會好一些。因為“自然災害對農業的危害只有在農作物生長期內才能發生,而且自然災害的打擊一般危害不到多年累積的財富,只能危害到當年的農業生產”,而游牧經濟相對農耕經濟這種時段性、季節性的生產方式,明顯地會呈現出連續性生產方式的缺陷,一經掐斷,恢復將變得困難。其次,儲存對象易于存儲。以植物種子作為存儲對象,方便保存,易于放置,即使有災情,一旦生產條件具備,又可恢復,若生產條件更為優渥,會比災前的生產規模更大,極易生產力的恢復。再次,游牧經濟的移動性導致其經濟活動單一。一旦畜牧業受損,便無他業進行緩和,而農耕經濟下,農業經濟的穩定促使手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一個地區遭災可以從其他地區進行征調,當然這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很大的關聯,游牧部落在其政權強大時,可通過與中原互市等方式進行補缺,一旦政權衰落則只能是徒看天災奪去人口、牲畜性命,部族衰敗。
不同的地理環境養育不同的人,并創造出各異的文化類型。司馬遷用“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一語道出游牧經濟的特點。也正是由于游牧經濟這一生產方式,使得歷史上北方草原顯得格外生機勃勃,先后興起了眾多游牧民族,呈“一個前仆后繼式的連續的過程”。雖然游牧經濟的形成是對地理環境的適應,但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單一的生產方式現正在加以改進,并輔以相關產業的發展,如毛紡業、皮革業等。同時加大對牧區的科技投入,提高畜養手段和防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使游牧經濟發展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一定的抵御風險能力。
本文作者:馬晶 單位:內蒙古大學
淺談自然災害對經濟的影響:論自然災害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為了確定災害的經濟效應,StéphaneHallegattea和PatriceDumasa[5]詳細探討了災害對生產力的影響。考慮到如果一個災難迫使必須重置一部分資本,那么新的平均生產率將會比以前高;最樂觀的情況是所有的資本置換均體現最新的技術。現實情況是,首先,當災難發生時,生產者必須盡快恢復生產,不能承受長時間生產中斷的小企業尤其如此。在貧窮國家,人們需要盡快維持生計,采取最新的技術意味著調整適應企業的組織和培訓工人,這在大多數情況下需要時間。因此,生產商有強烈的動機盡快恢復生產,而不考慮是否采用了最新的技術。其次,在大多數情況下,有些資產仍然可以使用,或以低于重置成本的價格維修。在這種情況下,生產者可以節省部分資金。第三,假定一個最新的技術生產力在不斷發展,災后的重建可能會使研發中斷或者擠占研發資金,從而減緩技術進步。因此,為了更加貼近現實經濟運行情況,應在實證模型中增加技術革新和追加投資的因素。通過建模和實證分析,StéphaneHallegattea和PatriceDumasa的結論是,短期重建的種種約束從深度和廣度上對災難的消極后果影響的持續時間較長。從長期來看,這些制約因素不發揮任何作用,災害不影響長期增長速度;而當社會提供重建資金的能力較低時,災害與長期增長速度是負相關的。在后一種情況下,短期約束將會創造“貧困陷阱”,進而影響到長期,從而阻止了經濟的發展。因此,不管有沒有生產力效應的影響,整個社會的風險抵御水平是首要的。當社會有較高的生產水平和風險抵御水平時,可以避免災害發生后的“貧困陷阱”,并避免對長期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但是災害并不能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因為后者只取決于外生的技術革新。
發展中國家的情形與發達國家不同,自然災害對經濟的影響也有不同的特點。IlanNoy和TamBangVu[6]利用越南各省面板數據,用Blundell–Bond廣義距估計的方法建立面板數據模型,分析了自然災害對越南經濟增長的影響。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災害變量對GDP增長率在災難等級的測度上沒有顯示出格蘭杰因果關系,嚴重的災害會導致經濟增長率降低,但是有時卻會促進短期經濟的繁榮。總的來說,災害的影響在不同的地區呈現出差異,而這些差異是與中央政府的支持顯著相關造成的,即那些有更多機會獲得重建資金的地區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MarkSkidmore[7]認為,自然災害風險將會增加家庭儲蓄的預防性動機,從而抑制消費。上述研究認為自然災害既能造成損失也會帶來一系列復雜的經濟效應,如強制性的新資本替代、新的需求和經濟機會等;但總的來看,災害的危害程度高低依賴于社會生產水平和風險抵御水平。對于不發達經濟而言,長期負面影響會導致“貧困陷阱”。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利用可獲得的數據,研究1995~2011年17年間自然災害與中國經濟增長間的關系。
一、計量模型與數據
1.計量模型選擇
經濟增長通常被認為是實際總產出的持續增長或人均實際產出的持續增長。根據《新帕特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經濟增長定義為以不變價格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8]凱恩斯認為,社會總需求是由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政府購買需求和進出口需求構成,有效需求變動會引起國民收入變動,影響社會總產出和經濟增長。由于凱恩斯理論建立在人口數量、資本數量和技術進步不變的前提下,因而只適用于從流量的角度分析短期經濟波動問題。索洛認為,經濟增長率等于資本和勞動的增長率與其產出彈性的乘積,長期經濟增長是由技術進步推動的,而技術進步是經濟理論所不能預見的外生變量。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則突破了索洛經濟增長理論的局限,把技術進步內生化,認為長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即勞動投入中包括教育、培訓等形成的人力資本的提高,而物質資本的積累也包括研發、創新等活動形成的技術進步。[9]自然災害不僅具有自然屬性,還具有社會屬性,[10]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的消耗和破壞會增加自然災害發生的風險。對于某個地區來說,自然災害通常是偶發的,而對于我國全國范圍來說,自然災害的發生必然為常態。如干旱災害,對于某個城市、村莊干旱災害的發生具有偶然性和周期性,而對于全國范圍內來說,干旱災害基本上每年都發生。其他自然災害如地質災害、地震災害等也有這一特征。自然災害對國民財富造成損失,給社會生產帶來損害和浪費,但同時又增加了新的需求,迫使人們重置資本,會產生一些技術創新和改良,如地震災害過后人們會增加建筑的抗震性能,對此可能展開研發、使用新技術等。因而從宏觀經濟層面考慮,本文認為可以把自然災害損失內生化,和資本存量、勞動存量放在一起,以度量其對宏觀經濟增長的影響。綜合以上考慮,本文對Cobb-Douglas生產函數進行拓展,把自然災害直接損失內生化引入模型。由于自然災害不僅對當期經濟產生影響,而且對后期經濟也會有波及影響,災后重建項目往往會持續2~3年,一些重大自然災害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災后重建期更長,故而自然災害對經濟增長的后續影響往往持續更長時間。本文取自然災害影響的持續期為5年,而把災害損失的1期滯后到4期引入模型。
2.指標說明和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1995~2011年間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檢驗,考慮數據的可得性和指標的代表能力,產出Y用GDP表示;勞動力投入N用每年的勞動力就業人數表示;由于不存在資本存量數據,用歷年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代表資本投入K;自然災害損失S用歷年自然災害直接損失總額表示。所有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1995~2012年)、《中國民政統計年鑒》(1995~2012年)、《中國勞動與就業統計年鑒》(2012年)。為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以1995年價格為不變價格,產出Y、資本投入K、自然災害直接損失S采用GDP平減指數進行價格縮減。
二、實證分析
使用eviews6.0軟件,方程(2)的最小二乘法(OLS)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估計結果表明,直接損失除了一期滯后之外,t值均不顯著,而且p值很大,不具備解釋能力。考慮到時間序列滯后變量之間可能會存在多重共線性以及自相關,對模型進行修正。首先消除自相關,使用廣義最小二乘法引入AR(1)過程,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表2的計量結果表明,模型F值和變量t值均顯著,只有LNS(3)項的p值略大,為11.51%,其余均在1%、5%和10%水平上顯著,可決系數和調整后的可決系數均達到0.99以上,勞動、資本變量系數的符號符合經濟意義,且檢驗結果沒有顯示出存在有自相關和多重共線性,可見調整后的模型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三、結論
我國自然災害的“生產力效應”和資金約束帶來的“貧困陷阱”是有可能同時存在的。盡管Albala-Bertrand關于自然災害積極意義的觀點受到很多批評和質疑,但在我國還是有現實意義的。首先,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我國國家宏觀調控的力度比較大,尤其在大的自然災害面前,各種救濟能夠及時到位;其次,我國的經濟增長多年來一直呈現出投資拉動的局面,短期內不會有很大的改變;再次,政府購買和投資一直在國民經濟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當某個地區的災害情況迫使必須重置資本時,我們就有可能以一個更高的生產率的經濟來補償災害的損失。因此,自然災害的“生產力”效應是可能存在的。StéphaneHallegattea和PatriceDumasa完全基于西方經濟體制,采用“理性經濟人”效用最大化的觀點分析問題,忽略政府和社會救濟機構的重要作用,并不完全適用于我國的實際情況。但是他們所提出的短期約束將會導致“貧困陷阱”,進而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速度這一觀點對我國有一定現實意義。根據我國的現狀,社會生產力水平和自然災害風險抵御水平還不高,對于大的自然災害,政府投入救災力度大,經濟恢復速度非常快;而對于一些常發的、規模范圍較小的自然災害,政府投入力度和社會關注程度較小,則會造成區域性貧困。例如我國的某些貧困地區,自然災害頻發正是導致其難以脫貧的重要原因。因而如何改變現有的救濟模式,擴大自然災害保險的投保力度和范圍,從而把災害風險適當地轉移到全社會共同承擔,是我國減災防災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從自然災害產生的過程和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來看,正是經濟的粗放發展導致了環境惡化,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對于存在相對過剩經濟的社會中,內需相對不足,自然災害在損失社會財富的同時又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當資本充足時則會在短期內刺激經濟繁榮;反過來說,如果存在短期的自然災害激勵下的經濟繁榮,正說明了當期的社會經濟存在相對過剩。總的來說,自然災害以損失現有財富為代價的拉動需求,無論對經濟增長起到了激勵作用還是阻礙作用,都實質上是經濟的非健康發展。
作者:賈美芹單位:中州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