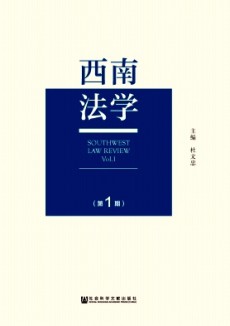民法典問題探討大全11篇
時間:2023-07-04 16:21:21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民法典問題探討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回顧一下民法法系的經典之作的誕生歷程也許會有所啟發。1804年《法國民法典》即《拿破侖民法典》是在拿破侖執政時、在其主持下,制定并且通過的。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不少法史方面的論著都會詳細介紹。拿破侖這個大資產階級的代表為了使民法典草案能夠獲得通過,甚至清洗了法案評議委員會。民法典并不是完全吸收羅馬法的產物,而是吸收了西方的自然法傳統精神,同時兼顧了當地的習慣。民法典歷經200余年,至今有效。期間官方兩次發起全面修訂或者重新起草民法典的動議,但是皆以失敗告終。拿破侖曾預言他的民法典是不可戰勝的,確實如此。而德國民法典的產生過程則更為戲劇性。19世紀初,德國法學家即開始呼吁制定民法典,但是,德國民法典一直到20世紀才正式誕生。差不多過了100年,有人說是因為以薩維尼為首的歷史法學派“阻撓”的結果。但是,正是因為探討和論戰進行的比較充分,德國民法典才成為民法法系的另一部經典。
從經典民法典的經歷中,當下的中國法學界尤其是“民法學界”是否該冷靜一下?著急啥呢?記得有位學者在山大作講座時說,有些人急于作中國的“民法之父”,有些人動輒“我的民法典”,也許這樣的事情是有的。學者的心理不同于政治家的心理,學者的成就也不同于政治家的成就。即便是民法典被通過了,起草者也無法貪天之功,自己去確認與民法典的“親子關系”,民法典也不是“他的民法典”。政治家就不同,拿破侖民法典是拿破侖親自起草的么?尤士丁尼法典也不是那個皇帝本人做的工作啊。學者的本分就是傳播思想,推動這個進程。民法典在中國的坎坷,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的,這個背景不轉換,法典的命運就無法改變。而背景的轉換、變遷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是一個歷時的存在。學者著急是沒有用的。
就現在的草案本身而言,已經成熟的無可挑剔,就剩下“臨產”這個最后步驟了么?恐怕不必然吧。甚至有人說,民法典草案就是翻譯、抄襲。這種說法顯然值得商榷,因為在法律的發展中,這叫做“法律移植”,是有科學根據的;但是,法典草案本身是否充分關注了當下中國的實際情況呢?是以法典改變現實還是以現實去改造法典,實際上是民族習慣如何進入法典的問題。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都是充分關注了本民族的固有文化資源、充分關注了本民族的習慣法。眾所周知,即便是中華民國時期制定的民法典,也充分照顧了當時中國的習慣,進行了大規模的民事習慣調查。現在的民法典草案進行這樣的工作了么?或者是我孤陋寡聞,或者是其工作沒有大張旗鼓。網上的征求意見倒是有的。整個來看,民法典的起草是學者工作的結果,立法機關在其中折中平衡。民法典草案是學者或者說是學界的草案而不是公眾的草案。將來能否普及呢?這也是個問題。
弗里德曼說:法典背后有強大的思想運動。[3]在中國民法法典化的背后,有這個思想運動、它強大么?它的輻射程度超出了法學界,影響到其他領域了么?思想運動肯定是有的,但是并不強大。學者本身關注的是什么?思想運動只是局限于法學領域本身,其他領域只是在看熱鬧,仿佛此事與其無關。普通老百姓就不用說了,也許有的人會很奇怪,老百姓還會思想?如果老百姓不會思想,不關心此類事情,只能說明此事的群眾基礎不夠牢固,說明法學界的工作做的遠遠不夠,尚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就這一點來看,民法典草案的生效也該緩行。
薩維尼的那句話更有震撼力:法典是民族精神的體現。照此觀點,中國的民族精神是什么?法學界已經探討明白了么?中國的民族精神體現在法典的何處?中國現在還沒有市民社會,只是處在一個萌芽狀態——當然,有人說中國已經存在市民社會。中國的社會基礎是什么?當下中國還是一個國家強于社會的總體性社會。在這種社會前提下搞民法典就會面臨社會本身帶來的阻力。當去年北大的鞏獻田老先生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以后,能夠聽到的法學界的聲音,非學術的漫罵多于理性的分析和理性的反思。中國的法學界連這個大前提都沒有解決,即使物權法草案勉強通過,也會在未來的實施過程中面臨尷尬。其中,最難處理的恐怕還是政府的公共權力于與公民的財產權的沖突以及國有企業資產的流失問題。
“法理文庫”叢書中,有一本書叫做《法典的理性》,這個題目倒過來就是“理性的法典”。我們期望中國有一部理性的民法典,充盈著中華民族的智慧和精神。也許這只是夢想,也許夢想也會變成現實。但這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而是充滿艱辛的過程。
--------------------------------------------------------------------------------
篇(2)
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并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而是在他們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民法典的制定離不開對歷史上存在的相關法的繼承。同時,由于我們身處一個日趨“國際化”的以開放特征的世界,我們周圍有許多比我們更為發達的國家,所以民法典的制定需要對域外法律的進行借鑒和移植。這些都已在法學界達成共識,而真正值得關注和研究的是怎樣繼承和移植,才能有利于制定一部符合我們國家實際情況,又能適應時展,與國際接軌的民法典。
一、繼承中的本土與西化之爭
法的繼承,是指法在演進過程中,新法有選擇,有批判地吸收或沿用舊法中合理、適當的因素,使之成為新法的有機組成部分的法律現象。法的繼承的來源有兩個,一個是國外的,被譽為人類共同文化結晶的那些成果;另一個是民族的,即本國歷史上存在并得以傳承的。無論是國外的還是民族的,只要是合理、適當的,都應當積極的加以繼承。但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是立足本土資源還是基本采用國外的法律制度,卻存在著不小的爭議。
近年來,從中國傳統文化去探討中國現代法治建設的問題,日漸增多,充分體現了其時代特色的話語霸權。我們也不妨從法律文化的角度來探討我國民法典制定中的繼承問題。誠然,我們不能忽視中國傳統的具有根深蒂固的社會基礎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觀念和法律體系。往往這種法律觀念和法律體系對法治的推行的影響遠遠大于外來法律思想的影響。悠久的歷史產生了深厚的傳統,而傳統則塑造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人的理性思維、道德判斷、價值觀念和理想追求,都是植根于他們所身處的文化傳統的,似乎不存在著任何超越和獨立于傳統的關于理性和道德的絕對的、客觀的標準。沒有了傳統或者脫離了傳統,我們便沒有可能進行思考和對事物賦予意義。[1]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對中國現代法治建設的負面影響: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強調國家權力,忽視個人權利;傳統法律文化要求個人服從集體,漠視個人自由;傳統法律文化維護等級觀念和等級秩序,忽視平等。這些都是與現代法治文明不相符合的,更是與民法自由,平等,權利的價值理念直接相悖,格格不入的。試想,連基本的價值理念基礎都不符合法的繼承的要求,又如何在其上構建民法的大廈呢?再則,從具體制度層面,中國傳統法律歷來重刑輕民,清末法制改革之前,沒有專門的民事法律,中國古代歷史上的諸多法典其實質都是刑法典,與民事有關的法律條文都零散的包含在刑法典當中,其調整手段也是用刑法的調整手段,所以更不可能從制度層面對本土資源加以繼承。所以無論從價值理念還是具體制度層面,中國民法典的制定立足本土法律資源都是站不住腳的,中國民法典的制定應當全面吸收西方近代的民法價值理念和制度構架,從而確立自己的民法體系。
也許有人會說,以西學為基礎的民法典,將會喪失我們的優秀的民族傳統,完全體現不出中華民族的特色。然而,民法典的制定需要的是理性的精神,而不是盲目的民族自豪感的沖動。不可否認,偉大的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作出過自己卓越的貢獻,中華文明在世界上有獨一無二的歷史地位,但在近代法律文明上,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我們的貢獻微乎其微。對外國法律文明的繼承與移植并不是數典忘祖,而是為了民族的更加繁榮蒼盛。近現代日本的法律文明也正是建立在明治維新時期對外國法律全面繼受的基礎之上的。耶林在其著作《羅馬法的精神》中所說的那段話是民法人耳熟能詳的:“外國法律制度的接受問題并不是一個 國格問題,而是一個單純的適合使用和需要的問題……只有傻子才會因為金雞納樹皮并不是在他自己的菜園里生長出來的為其理由而拒絕接受。”[2]要融入世界,要與時懼進,承認自己的不足,比盲目的高呼口號更符合法律的理性精神。
在民法典草案的制定過程當中,有人提出要求法律能夠反映改革開放以來實踐成果,吸收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東西,有人還提出要注意調查民間的傳統習慣,這些提醒都是非常中肯和必要的。法典都肩負著反映時代的使命,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無不如此。但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國度,在社會經濟生活發生日新月異變化的潮流中,選擇和體現特點務必慎重。務必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和論證分析,萬不可為特色而特色,草率貼標簽。還是聽聽德國人自己的經驗之談:“BGB(德國民法典)生效以來的一百年中,誰都強調自己的特點,自行其是,終于人人自危。因此,在經過這百年大亂后的今天,我們并不覺得BGB沒有德國特色是BGB的缺點。”在中國制定民法典草案的討論中,特色的發掘和光大是否有必要尚難定論,但經濟生活現實的某些實踐活動被“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寫進法條,卻在以往的法律法規中屢見不鮮。比如《民法通則》里的“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機關、事業單位法人”、“聯營”之類,此類法律術語和概念“特”倒“特”了,但連民法的基本語法都不符,結果破綻百出,不堪運用。更糟糕的情形,是將所謂“中國特色”作為自己不愿改變的陳規陋習的幌子。那樣的特色,就真該徹底摒棄了。
二、 移植中的兼容并包與擇一而從
這是移植當中的另一個問題,答案確乎是肯定的,因為理性的立法畢竟不同于感性的山盟海誓。即使從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來說,博采眾長兼容并包也是當然的抉擇。但問題似乎又并非想象的那么簡單。面對令人眼花繚亂的選擇,“學誰”以及怎樣學,可能比“學還是不學”更難決定。好比做菜,把所有好吃的東西都一鍋燴了,根本不講究材料搭配和烹飪技巧,弄出的東西未必讓人咽得下口。世界上民法典移植成功的例證里,表面上的吸收借鑒其實往往掩蓋著骨子里的專一。迄今為止的歷史表明,英美法的推廣主要是依仗殖民勢力而非引進國的自主選擇,這和大陸法的情形截然不同。之所以如此,除去文化上的原因不談,一般認為是由于制定法主義的大陸法較之判例法的英美法而言,其規范的抽象化、體系化使得內容上的全面把握較為便宜,因此容易被接受。而大陸法的移植中,不同流派的選擇也頗耐人尋味。法國和德國均屬大陸法系,但卻是大陸法系里不同法律派別的成員。日本先效法法國,后改學德國,雖然變來變去,但始終未脫大陸法系,而且始終有個確定的主要跟蹤對象;最終形塑為以德國五編制為基礎框架,同時融合了德國和法國民法的概念及制度的法典。我固然同意這樣一種說法,即,不能以大陸法尤其是德國法的體系來考慮中國民法典,應該盡量容納英美法中好的東西。或者,更直接點說,不能迷信德國法、德國體系。但是,任何移植都必須考慮所扎根的土壤,英美法乃建基于特別的法官產生機制、法官的較高素質以及獨特的陪審團制度的法律體系,脫離這些因素簡單照搬,移植的東西便會成為無本之木或者橘化為枳。雖然英美法的某些規范和法律思想具體來看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作為整體,鑒于其特殊的結構,其實是不適宜為新制定的民法典作榜樣的。[4]法律的借鑒絕非將法條或制度照搬過來即可,以判例法(case law)和法官法(judge made law)為特色的英美法與以所謂civil law作范本的大陸法之間并不能實現直接的對接。這個道理應該不是太復雜,但好像偏偏沒人在乎。比如,研究英美法的相關制度時,一個最基本的前提是,英美法乃判例法系,其法律淵源乃至審判方式均不同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大陸法系。在學說上甚或在具體審判實踐中,借鑒某一項理論或某一種方法來作出解釋或者判斷固然可以,但這和直接將其變為成文法上的規定是完全不同的。舉個例子,我國合同法中大膽引進了英美法的根本違約制度,但是,是否構成根本違約,“最終是一個由法官解釋合同并依其裁量權加以判定的事項”,[5]由于這些制度在英美法中可以透過卷帙浩繁的判例加以具象,因此在其理解及適用上不會成為問題。但是如果把依靠判例才得以存活的制度或者規則“開創性”地轉正為成文法的條文,而且不作構成上的細化,那么實際操作中的疑惑就難以避免,何為“根本”違約成為現在困擾法官的一道難題也就不足為怪了。雖然合同法確立了判定是否構成根本違約的標準是“不能實現合同目的”,而究竟什么是“不能實現合同目的”,如何區分根本違約與非根本違約,仍然是司法實踐中面臨的問題。
英國經濟學家杰文斯(1835-1882)曾在他那個時牢騷說存在一種“權威的有害影響”,這就是,當思想被人們普遍接受之后,經過一段時間便會在公眾的頭腦中固定下來。新的從業者必須投入時間和精力去學習現行的技術或思想,并且在某一種操作程序中獲得一種既得的滿足。盡管這是一個自然的進步,但所接受的思想可能會變成教條;由這些教條主義而產生的智力僵化,以及對相反觀點的不寬容,會阻礙思想的進一步發展。[6]這樣的情形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實際上,對慣用的法律制度的懷疑以及對經典的逆反,很大程度是來源于對“權威的有害影響”的恐懼和矯正。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百花齊放才凸現其理論價值和實踐功用。但懷疑須建立在事實之上,而逆反更可能是一種可怕的感情用事。
參考文獻:
[1] 陳弘毅。法治、啟蒙與現代法的精神[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1998.169.
[2] 轉引自(德)Ko茨威格特,H·克茨。比較法總論[M].潘漢典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4(中譯者序)。
[3] (德)弗蘭克·閔策爾。求大同:德國民法典立法的成果和錯誤。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1期。
[4](德)克勞斯-威廉·卡納里斯。歐洲大陸民法的典型特征[M].鄭沖譯,載孫憲忠主編:《制定科學的民法典:中德民法典立法研討會文集》,法律出版社2003.3.33.
篇(3)
一、各國模式
民法總則就是統領民法典并且民法各個部分共同適用的基本規則,也是民法中最抽象的部分。民法典作為高度體系化的成文立法,注重一些在民事領域中普遍適用的規則是十分必要的。傳統大陸法系國家大都采取潘德克頓體例,在民法典中設立總則。也有一些大陸法系的民法典中沒有設立總則,在民法中是否應當設立總則以及其內容應當包括那些,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為了盡快制定一部體系完整、內容充實、符合中國國情的民法典,首先必須討論民法典總則的設立問題。
綜觀大陸法系各國民法典編纂體系,具有代表性的不外乎羅馬式與德國式兩種。一是羅馬式。該體系是由羅馬法學家蓋尤斯在《法學階梯》中創設的,分為“人法、物法、訴訟法”三編。這種三編的編纂體系被法國民法典全盤接受,但法國民法典剔除了其中的訴訟法內容,把物法分為財產及對所有權的各種限制和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由于采納了此種體系,法國民法典沒有總則,缺少關于民事活動的一般原則。有關民法的一般規則、原則體現在學者的學理中。瑞士、意大利等歐洲大陸國家民法、以及受法國法影響的一些國家的民法典也不采納總則編的設置或僅設置宣示性的“小總則”。二是德國式。總則編始于18世紀日爾曼普通法對6世紀優士丁尼大帝所編纂的”學說匯編”所做的體系整理;該體系最早被胡果(Hugo)在1789年出版的《羅馬法大綱》一書中采用,最后由薩維尼在其潘德克頓教程中系統整理出來,并為《德國民法典》所采用。因為總則的設立,進一步增進了其體系性。因此,許多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民法,都采取了潘德克頓體例。?
然而一些學者對總則的設立提出異議,否定設立總則的理由主要是:第一,總則的規定是學者對現實生活的一種抽象,更像是一種教科書的體系。而法律的目的不是追求邏輯體系的圓滿,而是提供一種行為規則和解決紛爭的準則。而且總則的規定大多比較原則和抽象,缺乏具體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第二,總則的設定使民法的規則在適用上的簡易性和可操作性反而降低,把原本統一的具體的生活關系割裂在民法中的各個部分。在法律適用時,要尋找關于解決某一法律問題的法律規定,不能僅僅只查找一個地方,所要尋找的有關規定,往往分處于民法典的不同地方。這對法律的適用造成了麻煩。第三,由于設立總則必須要設定許多民法共同的規則即一般條款,但在設定一般條款的同時必須設立一些例外的規定。但哪些規則應當屬于一般規定置于總則,哪些規則應當作為例外規定,一般規定和例外規定的關系是什么,在法律上很難把握。
二、設立民法總則的理由
盡管民法典總則的設立遭到了許多學者的非難,但德國民法典設立總則的意義和價值是絕不可低估的。我認為,從法國民法典未設總則到德國民法典設立總則,本身是法律文明的一種進步。在我國民法典制訂過程中,對是否應當確立總則的問題,也有不同看法。有些學者主張我國民法典應當采用“松散式”或“匯編式”模式制訂,從而無需設立總則。但大多數學者都贊成設立總則。我認為民法典設立總則是必要的,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總則的設立增強了民法典的形式合理性和體系的邏輯性,可避免重復,使法典更為簡潔。因為民法典的內容過于復雜,條文過多,通過總則的設定,可以避免重復規定。德國馬普研究所的卓布尼格教授即認為,設立總則的優點在于:總則條款有利于統領分則條款,確保民法典的和諧性;總則條款有助于減少分則條款,從而加快立法步伐;總則條款有利于民法典本身在新的社會經濟情勢面前作出必要的自我調整。總則的設立使各個部分形成一個邏輯體系,將會減少對一些共性規則的重復規定,有利于立法的簡潔明了。盡管沒有民法總則并非不能形成民法典,但沒有民法總則,法典的體系就必然會淡化、削弱。除了商事特別法以外,民法的內容本身是非常豐富的。如果將一些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從共同適用的規則中抽象出來,形成為總則,那么民法的內在體系將更為嚴密,否則,將是散亂的。不可否認,民法總則并非適用于各項民事制度,但只要它能夠適用于大多數民事制度,那么它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價值。總則的設立使民法典形成了一個從一般到具體的層層遞進的邏輯體系。
篇(4)
論文摘要 論文以自然人的人格權為視角,以人格權獨立成編的可行性與必要性為線索,集中探討了學界對于是否應在民法典中單獨設置人格權一章的各類看法,并對其爭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文認為通過對人格權所保護的對象進行重新定義的方式,將人格權所保護的人格權益理解作是民事主體對其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譽、隱私、信用等各種人格利益的穩定狀態所享有的排除不法侵害的權利,便能夠化解人格權法獨立成編在法理與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矛盾。
論文關鍵詞 人格權 獨立成編 穩定狀態 可分離性
一、問題提出
近年來在民法與司法實務界,對人格權的探討與強調愈發普遍與具體,但最為基本且爭議巨大的還是人格權是否應該獨立成編這一問題。《民法典草案》中單獨設置第四編“人格權法”來較為詳細的規定人格權,為人格權的立法構建了初步的框架。不少學者認為加快人格權法的制定,將其作為未來民法典的重要部分,不僅是對傳統大陸法系民法典體系的發展與完善,也是構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重要需要。也有一部分學者站在否定的立場上,認為人格權獨立成編存在理論上的漏洞和技術上的障礙,因此不宜將其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于此,筆者擬從人格權獨立成編的可行性與必要性兩方面展開論述,介于篇幅限制,僅以自然人的人格權為視角進行探討。
篇(5)
《物權法》頒布之后,《侵權責任法》的起草已經提上日程,公平責任的取舍和立法模式,牽涉到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責任構成、責任形態和賠償數額的確定,是不能回避的理論問題。根據筆者的觀察,不但學者難以就公平責任的概念、理論和取舍達成基本共識,實務中也存在適用標準和范圍不明確的問題。[1]我國《民法通則》第132條的規定是比較法上的孤例,在立法史上類似的立法例也不多見,那么公平責任到底是如何成為我國侵權法上獨具特色的規定,本身就值得認真考證和反思,這也是從立法解釋層面探究該條適用范圍的基礎。本文試圖對公平責任的來龍去脈作初步的考察。
一、公平責任的源流與類型
公平責任的源流可溯及到1794年《普魯士民法典》第41-44條對兒童和精神病人的侵權行為,基于公平或衡平的特別考慮可以構成責任的充足理由。這種受自然法觀點所影響的理論認為,某個窮人不能承受由某個萬貫家財的精神病人對其造成的嚴重的人身傷害的損失,稍晚的1811年《奧地利民法典》1310條作出了類似的規定。[2]從各國體現公平原則的立法例來看,廣義的公平責任條款根據實際的作用,可以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首先是特殊侵權責任類型,即在特殊侵權行為類型中適用依據公平原則減輕賠償責任,適用范圍受到法律明文規定的列舉性限制。這是主流類型,各國立法例主要適用于在受害人不能從對無責任能力人負有監護責任的人那里獲得損害賠償的情形。如源于1881年《瑞士債法典》第58條的現行1911年《瑞士債務法》第54條[無行為能力人的責任]第1款規定:“法院可以依公平原則判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承擔部分或者全部因其造成的損害賠償責任。”[3]《德國民法典》第829條[出于合理理由的賠償義務]規定:“具有第823條至第826條所列舉的情形之一,而根據第827條,第828條的規定對所引起的損害可以不負責任的人,在不能向有監督義務的第三人要求賠償損害時,仍應當賠償損害,但以根據情況,特別是根據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合理要求損害賠償;而不剝奪其為維持適當生計或者履行其法定撫養義務所必需的資金為限。”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第2047條[無行為能力人導致的損害]第二款規定:“在負有監護義務之人不能賠償損害的情況下,法官得根據雙方當事人的經濟條件判定致害人給予公平的賠償(參閱第2045條)。”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187條第3、4款規定:“如不能依前二項規定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被害人之聲請,得斟酌行為人及其法定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行為人或其法定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前項規定,于其它之人,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之行為致第三人受損害時,準用之。”
其次是減輕賠償責任類型。本類公平責任的實質,是依據公平原則,在特定情況下對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減輕,如《埃塞俄比亞民法典》第2099條(衡平的權力-1.不知過犯)規定:“(1)如果導致責任的過犯是處在不知其行為的過錯性質狀態的人實施的,在衡平需要時,法院可減少授予的賠償額。(2)在這一問題上,必須考慮當事人各自的財務狀況和過犯的行為人的賠償損害責任的后果。”《俄羅斯民法典》第1083條第3款規定:“法院可斟酌致害公民的財產狀況,減少其賠償損失的金額,但損害由其故意行為所致時除外。”《蒙古民法典》第394條第1款規定:“除故意致人損害的情況外,法院在確定損害賠償時,可參斟酌加害人的財產狀況減輕其承擔的責任。”
最后一類是一般侵權責任基礎類型。該類的主要特點是規定了具有普遍適用性的公平責任條款,條文自身就可以單獨作為承擔侵權責任的依據,我國的《民法通則》第132條就屬于這種類型,因此也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篇(6)
一、知識產權法典化的模式之一
將知識產權制度納入民法典是二十世紀制定的一些民法典的獨創,如《意大利民法典》、《越南民法典》、前《蘇聯民法典》等民法典中分別規定有知識產權制度。而在傳統民法典如《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等法典中均未將知識產權制度納入其中。那么,意大利、越南等國的做法是否獲得成功了呢?我們不妨從其具體規定展開討論。《意大利民法典》于1942年頒布,它在第五編《勞動》一編中將《智力作品權和工業發明權》與企業勞動、公司、入股、企業、競爭、合作社等制度相并列。《智力作品權和工業發明權》一章中規定了著作權、工業發明專利權、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權三節。在上述三節中,該法僅用了20個條文極其簡略地列舉了上述權利的客體、權利的取得方式、權利的內容、權利的使用等內容。由于內容過于簡略,該法不得不用3個條文分別規定,有關上述權利的財產權行使、存續及取得方式適用特別法的規定。為此,意大利又分別頒布了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商業秘密法、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法等專門法律,上述法律條文眾多,內容復雜,如意大利1981年著作權法的條文就達206條之多,其內容涉及著作權制度的方方面面。對于《意大利民法典》的這一體例,其立法者解釋說:“就商號、標識與商標、智力作品權與工業發明權、競爭等內容而言,它們無疑是具有智力勞動的性質,是勞動法律關系的重要部分,自然要置于勞動編之中。”[1]
對于《意大利民法典》的立法例,筆者認為它存在明顯的缺陷。第一,知識產權的產生過程并不必然是勞動過程。例如,某人將自己的姓名作為商標(如“張小泉”牌剪刀)使用,這種商標的產生很難說是一種勞動;其次,該制度所協調的關系并不必然是勞動關系。它所要解決的主要是民事主體如何取得知識產權及其如何行使該權利的問題,并非解決知識產品的創造者與其所屬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問題,何況在多數情況下知識產品的創作僅僅是個人的行為而非企業的行為,因此將該關系解釋為勞動法律關系無疑是牽強附會。第二,該法典的立法模式與效率價值不符。首先,該法典有關知識產權制度的規范不具有可操作性。例如,該法典第2577條第1款規定,“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和確定的效力內(參閱第2581條),作者享有以各種形式和方式發表作品并對其進行經濟性利用的排他權。”那么,作者究竟享有哪些權利呢?該法典并未規定,因此在實踐中當事人及司法者不得不去查閱著作權法來了解上述權項,那么這種立法模式對當事人和司法者而言幾乎毫無利用的價值。其次,既然該國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等法律用了極為詳盡的條文來規范知識產權制度,那么該民法典又重復作出規定,豈不是多此一舉?這不僅產生了重復立法的問題,而且造成了立法資源及司法資源的浪費。再次,這種設計是否真的解決了知識產權的司法問題呢?顯然沒有,因為其內容極其有限,而知識產權的法律規范又極為廣泛,民法典顯然不可能包羅萬象,對此,意大利的學者們也產生了同感,認為這部法典正“面臨著一定程度的危機,它那井井有條的體系有時似乎不再能成為大量新法律的、組織上的參照系。”[2]綜上所述,該法典有關知識產權編的設計并不成熟。
越南是另一個在民法典中規定知識產權篇的典范,其民法典中單獨設立了《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權》一編,其知識產權編規定了著作權、工業所有權及技術轉讓三節,共計81條。有關著作權的規定比較詳細,有關工業產權的規定則比較簡略。另外,自該法典頒布后,該國于1989年頒布的《工業所有權保護法》及1994年頒布的《著作權保護法》自1996年廢止。那么,這種立法例是否成功了呢?從立法技術而言,筆者認為它的設計依然是無效率的。首先,由于廢除了《工業所有權保護法》及《著作權保護法》,所以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規范僅能適用民法典中的相關規定。然而,民法典中有關著作權制度的規定有35條,主要規定了著作權保護的客體、內容、主體、鄰接權等制度,基本能滿足實踐的需要。但是,工業所有權部分僅有25條,卻要對專利權、商標權、原產地標志權、商業秘密權等權利進行規范,實在是力所不及,所以其條文過于簡略而無可操作性。由于這些缺陷的存在,該法典不得不在第788條另行規定:“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商標、注明商品產地等權利由國家主管部門頒發保護文本予以確立。其它工業產權也可根據法律的規定確立。”可見,工業產權的確立還必須遵循國家主管部門頒發的保護文本的規定。所以,民法典不是一個能包羅萬象的法律,其有限的容量不可能對知識產權制度做出面面俱到的規定。如果說該法典有關知識產權編的設計是失敗的,絲毫也不夸張。
除上述國家之外,俄羅斯、荷蘭等國也都嘗試了類似的做法,但尚未見成功。
筆者認為,我國在解決該問題之時,既應考慮到我國已有的知識產權立法現狀及國外的相關立法經驗,同時也應考慮到知識產權制度自身的特殊性,注意協調好知識產權制度與民法典之間的關系問題。
從現行立法來看,我國于1986年公布的《民法通則》在第5章《民事權利》中將知識產權與物權、債權和人身權并列。“知識產權”一節用了4個條文在原則上規定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發明權應受到法律的保護。其優點是概括性強,但未將一些新產生的知識產權如植物新品種保護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等權利納入其中。另一方面,我國知識產權的專門立法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十分迅猛,目前已頒布了多部單行法,內容廣泛,涉及各個領域,其條文也十分詳盡,可操作性較強。近年來,由于社會經濟、科技的迅猛發展,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經常發生變化,其內容頻頻修訂。例如,著作權法于1990年頒布,在實施不到十年的時間又進行了修正;商標法1982年頒布,1993年即作了修正,2001年又作了修正;專利法1984年頒布,1992年修正,2000年第二次修正。
結合知識產權制度的特點,筆者認為,我國未來在設計民法典時不應將知識產權制度單獨設為一編。其理由如下:第一,知識產權制度的法律規范具有其特殊性,不同于傳統的民事制度,很難用普通的民事規范予以調整。其次,知識產權法的調整規范比較特殊,其制度不僅包括諸多的民事規范,而且包括為數眾多的行政法規范和刑事規范,因此其法律規范的性質十分特殊。在民法典中規定了一些保護知識產權的行政規范和刑事規范,將會影響民法典的體系美。第二,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其法律又常常修訂。較之有形財產制度的規范性、系統性而言,知識產權立法可謂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舊的法律頻繁修訂,新的法律次第產生,難以形成系統的完整的體系。與此同時,一些為有形財產法律制度所不能調整的權利逐步進入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視野并成為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此而言,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具有開放性,其范圍也不斷擴大。例如,計算機域名是最近幾年才產生的新鮮事物,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已在考慮如何來保護域名注冊人的利益,因此域名權有可能被作為一項新型的知識產權而得到保護。此外,知識產權的標的多為創造性智力成果、識別性標記或資信,它們極易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及新技術更新的沖擊,極易受到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因而知識產權的法律制度不斷修訂更迭,處于極不穩定和“支離破碎”的狀態之中。[3]例如,法國在1793年頒布了《作者權法》,1957年為了與《伯爾尼公約》相協調,遂對原法作了修訂,1985年在著作權法中又增加了有關鄰接權保護的規定,1992年為了適應新技術發展的需要,法國再次對原著作權法作了修訂,增加了有關計算機軟件方面的規定。如果將這樣一個頻頻變動的法律置于相對穩定、系統化的民法典中,無疑會極大地損害民法典的穩定性和權威性。第三,從目前國外的立法實踐來看,盡管有一些國家試圖在民法典中規定知識產權制度,但不是無功而返就是事倍功半,這種失敗的立法例不值得我們借鑒。第四,從我國的現實立法來看,我國目前已制定有相當完善的知識產權單行法律法規,它們在解決知識產權糾紛時已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們沒必要放棄這些相對成熟的法律而去另起爐灶。如果在民法典中另立知識產權編,無疑是立法資源的極大浪費。或者,即使我們草率地將現行的知識產權單行法規不加修改地納入民法典而作為知識產權一編,也不能解決問題,因為這一方面會造成單行法規與民法典內容的重復,另一方面也會使民法典的內容顯得過于龐雜零亂,破壞了民法典的體系的穩定與和諧。
二、知識產權法典化的模式之二
既然將知識產權制度納入民法典中未獲得立法者所期望的成功,那么,人們為什么仍然要孜孜不倦地嘗試知識產權的法典化呢?
首先,知識產權制度的法典化是法律系統化、體系化的要求。羅馬皇帝優士丁尼在解釋其編纂《學說匯纂》的動機和理由時曾經指出,“我們發覺我們全部的法規,好象是從羅馬城建立以來,從羅慕洛斯時代以來的法規都傳給了我們,這所有的法規的如此的混亂,這種狀態漫無邊際,已經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圍。”[4]所以,法律法典化后可以使法律系統化,使其“結構嚴謹并富有表達力。”[5]在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中,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已不下十余件,這些法律、法規的內容十分龐雜、零亂,其規范有進一步修改的必要。例如,我國目前盡管已頒布了《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等法規,但這些法規僅為行政規范,其權威性不及法律,且其內容也需要進一步完善。還有,盡管我國早在1990年頒布的《著作權法》第6條就指出,“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保護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但時隔多年,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保護辦法仍未制定出來,所以,在知識產權法典化的過程中對法律的不足進行適當的修改,正是一個不錯的時機。
其次,知識產權的制度的法典化是解決現有知識產權制度內在矛盾的一種理性選擇。近年來,有關知識產權權利沖突的案件頻頻發生,如有人將他人的商號作為商標予以注冊,而商號的管理機構與商標的管理機構并不相同,且商號的保護范圍與注冊商標的保護范圍又相差甚遠,因此二者之間常常發生權利的沖突。還有一些知識產品如外觀設計既可能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又有可能取得外觀設計專利權而受到專利法的保護,還有可能注冊為圖形商標而受到商標法的保護,但各部法律所規定的保護標準又不相同,因而會造成保護上的差異。[6]
因此,在知識產權法典化的進程中,人們可以采取適當的措施來解決上述矛盾,如將商號的管理機構與商標的管理機構相統一,制定合理的規范來解決知識產品的重疊保護問題。
那么,除了將知識產權納入民法典之外,還可通過制定單獨的知識產權法典的辦法來實現法典化的目標。在這方面,1992年法國頒布的《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一個成功的先例。法國于1992年7月1日頒發92-597號法律將當時23個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單行立法匯編成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法律部分),從而形成了世界知識產權領域的第一個法典。在該法典頒布后的6年間,法國又先后12次對法典進行了修改和增補,使其知識產權立法始終處于世界各國的前列。其翻譯者指出,盡管在法典頒布前法國經過200多年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已形成了門類齊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但是法典的制定使上述相對獨立和零散的知識產權各部門立法“匯集成了一個內容豐富的有機整體,充分體現了法典這種立法形式結構清晰、邏輯嚴密的優點。”[7]該法典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文學和藝術產權,包括著作權、鄰接權、數據庫制作者權;第二部分為工業產權,包括行政及職業組織、工業品外觀設計、發明及技術知識的保護、商標及其他顯著性標記的保護等內容;第三部分為在海外領地及馬約爾屬地的適用。其中,第六卷的技術知識的保護是指制造秘密、半導體布圖設計和植物新品種的保護,第七卷的其它顯著性標記是指原產地名稱。該法典共計17編51章441條,它幾乎囊括了所有的知識產權制度。
《法國知識產權法典》的頒布得到了學者們的高度評價,其優點可概況如下:一是它的體系和諧,系統性好,法典較好地處理了知識產權內部各部門立法之間的關系。由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對象種類多,容易交叉,法典十分注意劃分各個保護對象的界限,避免產生內部的沖突,如法典第L。511-3條規定,同一保護對象同時被視為新外觀設計和可授予專利的發明,且外觀設計的新穎性的組成要素與發明的相同要素不可分的,該保護對象只能依有關發明專利的規定進行保護;法典第L。511-1條規定,侵犯他人公司名稱或企業名稱,全國范圍內知名的廠商名稱或牌匾、受保護的原產地名稱、著作權、受保護的工業品外觀設計權、第三人的人身權、尤其是姓氏、假名或肖像權、地方行政單位的名稱、形象或聲譽等在先權利的標記不得作為商標使用和注冊。但法典從藝術的統一性出發,同時又承認同一作品可以享受著作權和外觀設計的重疊保護。二是該法典能夠較好地處理知識產權法中的特別規范與一般民事規范之間的關系。由于知識產權屬于無形財產權,《法國民法典》的很多規定不能直接適用于此,因此該法典便規定了大量的特別規范來解決上述問題。例如,為保護作者權益免受侵害,《法國知識產權法典》第L。131-1條對契約自由作了大量的限制,規定全部轉讓未來作品的合同無效;為了維護交易的安全,該法典第L。512-4條、L。613-9條、L。714-7條規定工業品外觀設計、專利及商標權利的移轉或變更不能像有形財產那樣通過交付而發生所有權的移轉,其移轉時非經在注冊簿上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另一方面,除了例外規定外,一般法的普遍原則在知識產權制度中通常適用。三是該法典的規定可以較好地解決民法典的穩定性與知識產權制度的易變性之間的矛盾。由于將知識產權制度置于民法典之外,因而知識產權制度的特殊性、知識產權法規的修訂及知識產權內容的更迭僅會對知識產權法典產生影響,而對民法典影響不大,所以這種處理方法的優點十分明顯。
我國目前正步入民法典制定的關鍵時期,如何協調知識產權制度與民法典之間的關系問題是多數學者所關注的主要議題之一。既然將知識產權制度納入民法典在多數國家已被證明為是一種失敗的決策,我們沒有必要重蹈覆轍。從目前的一些立法例來看,筆者認為《法國知識產權法典》的這種做法仍然是一種不錯的選擇,對我國未來極具參考價值,我國未來在立法時可采取該立法模式。不過,《法國知識產權法典》的立法例并非是完美無缺的,已有學者指出,“1992年頒布法典時基本上只是將當時的知識產權各部門法規匯集到一起,體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獨立。”[8]所以這一法典與普通民法典、刑法典的根據區別在于其缺乏一個適用于具體制度的普遍規范。對此,我國已有學者提出,可以在知識產權法典中設立一般性規定[9],筆者也認為這種規定頗有必要,因為它可以統攝整個知識產權制度,使之成為一個相對統一的、和諧的整體,而不致于僅僅像《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那樣僅是一個法規的匯編,且這樣做可以增強法典的內在凝聚力。至于法典的結構,筆者認為可分為一般規定與具體制度兩大部分,在一般規定中應當規定知識產權的概念、范圍、主體、客體、侵犯知識產權的歸責原則等條款,在具體制度中應當在對現行單行法律法規進行修訂的基礎上規定各類知識產權的保護制度。
注釋:
[1]費安玲:《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之探討》[J],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頁。
[2]費安玲、丁玫譯:《意大利民法典》[C]的《前言》,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
[3]參見Philippe Malauie et Laurent,Cour de Droit civil,Les biens,CUJAS,1992,Paris,P56,轉引自尹田:《法國物權法》[M],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頁。
[4]C.Deo Auctore,1.轉引自[美]艾倫。沃森著,李靜冰、姚新華譯:《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頁。
[5][美]艾倫。沃森著,李靜冰、姚新華譯:《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頁。
[6]李明德:《外觀設計的法律保護》[J],載《鄭州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5期。
[7]黃暉譯:《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法律部分)[C],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8頁。
篇(7)
人格權法的完善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新型人格利益的出現,使得人格權法在保護各種人格利益時受到立法瓶頸的約束,從而引起立法、司法和理論界對人格權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問題更加關注。人格權法在民法典中的編排體例因各國的歷史、文化、法律傳統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不論選擇何種立法體例去規制人格權,在理論上都應從以下兩個層面去解讀:第一個層面從比較法上考察各種立法體例及其存在的價值。第二個層面是從法學理論層面探討人格權在民事權利體系中的地位,從而據此推斷出人格權應權利化。
比較法上考察人格權的各種立法體例
將“人格”在主體制度中給予保護。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第九條規定“所有法國人均享有民事權利。”①在制定《法國民法典》之初,受到自由、平等的人權觀的影響,該法典中并無“人格”一詞。法國學者認為,人格權是自然人主體的應有之意,因此人格權在法學主流中也就失去其應有的地位。
將“人格”在侵權行為法中給予保護。《德國民法典》第二條規定:“有權使用某一姓名的人,因他人爭奪該姓名的使用權,或者因無權使用同一姓名的人使用此姓名,以致其利益受到損害的,可以要求消除此侵害。如果有繼續受到侵害之虞時,權利人可以提起停止侵害之訴。”德國學者是以將待決案件進行匯總并歸于某項規則的方法來對已出現過的人格權放入債法的侵權法中進行保護。
人法中涵攝人格權法模式。《瑞士民法典》在人法篇中單設“人格權”一節,該法典不僅首次對人格權進行了完整的權利保護,而且民法典的編纂人胡貝爾在提出一般人格權概念的同時,又對一般人格權的侵權行為給予立法保護。
人格權法在總則中獨立成章模式。1994年,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首次設專章對人格權進行法律確認并給予立法保護。該法典將人格權、物權、債權等民事權利給予同等保護,這代表了當代學者對人格權法的重視和對民法理念的新認識。
通過對不同時代的各國民法典關于人格權的立法體例的對比,我們可以歸納出立法對人格權規制的軌跡:第一,不作抽象規定和具體列舉—作出抽象規定—給予具體列舉;第二,主體制度中給予保護—侵權行為法中給予保護—對人格權進行積極的宣示性規定。從對立法軌跡的歸納和總結,我們可以看出,立法者對于人格權法在民法典體系中給予越來越高的評價,這也是現代社會發展和法學理念對立法者和民法典編纂的要求。
理論上探討人格如何上升為獨立的權利
權利是人與外在于人的事物在法律上的連接。羅馬法上的人格是指一種內在化的資格,而今天的人格權概念將現代社會擴張后的多種人格利益包括其中,是一種外在化的人的價值。人格的權力化能否在現今的民法典中應然的規制出來,必然要探討如何解決權利塑造過程中的各種障礙。因此,我們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人格與人格權之間存在何種關系?理清這個問題有助于我們清晰地認識到今天所探討的“人格權”中的“人格”不是羅馬法上的主體資格;對“人格”須采用“權利的保護模式”,那么這兩者之間究竟應用何種紐帶進行連接。解讀了這兩個問題后,可使我們看清人格權是否是一種獨立的民事權利,可否取得獨立的地位。若是一種獨立的民事權利,那么就應在民法典中取得與其民事權利相同的立法地位。
人格的權力化:從人格到人格權。人格概念中的民事主體資格底蘊“人格理論產生于古羅馬時代,其基本價值用于區分自然人的不同社會地位”②,是“組織社會身份制度的工具”③。17、18世紀的啟蒙運動推動了人格與人的倫理性之間的關系在立法上得到了新的重視。1894年《普魯士一般邦法》的頒布使這一理論得到了法律上的確認,該法典第一條規定:“人在市民社會中只要享有一定權利,便被稱為法律人格。”
由此可見,羅馬法上的人格在主流歷史解釋中始終只是一種資格。在古羅馬,人格是處理市民社會的主體資格問題,具有對內和對外兩方面的作用。在對內的社會關系中,并不承認所有的社會主體都是城邦居民,他們的身份被分成特權、常態和受歧視三種,只有特權、常態兩種身份的擁有者才具有人格。在對外社會關系中,人格用來區分一個市民社會與其他市民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康德將羅馬法上的人格進行倫理學解釋,使人人都變成了persona,均享有人格。在此基礎上,人格又被抽象為權利能力。因而,在歷史的流變中羅馬法上的人格(民法上的權利能力)并沒有改變其性質,其只是一種資格。
人格權的概念。多內魯斯是人格權概念的創始人,他把權利分為對物的權利(物權)、對他人的權利(債權)和對自己人身的權利(人格權),其中人格權又包括身體完整權、自由權、榮譽權等④。王利明認為:人格權是指主體依法所固有的以人格利益為客體的,為維護主體的獨立人格所必備的權利⑤。
從本質上講,權利是特定利益與法力的結合。而人格權這一權利的特定利益是客體:人格。但這里的“人格”并非是羅馬法上的“人格”(羅馬法上的人格是一種法律抽象,是法律所賦予的一種資格),而人格權客體的人格是人的各種利益,包括生命、身體、健康、名譽等等,是人格權的標的,是一種事實上的人格。由此可知,羅馬法上的“人格”是一項民法上的法律技術,指民法上的人生而具有的權利能力,而人格權的客體的“人格”是現實生活中的人的各種利益。羅馬法上的“人格”作為現代民法中的權利能力因其與主體資格不可分離,屬于主體范疇;而以人格利益為客體的人格權則屬于主體所享有的權利范疇,是一項實實在在的權利,不可與具有主體資格的“人格”,即權利能力相混淆。
人格的權利化:人格的保護模式。通過對人格與人格權概念的解讀使我們認識到人格是以人的倫理價值為基礎的。那么,如何將“倫理人格”上升為“權利”,用人格權進行塑造,進而將倫理人格納入“權利保護”的軌道。這是解答人格權法是否可以獨立成編的前提。若“人格”無須用法律進行規制,且亦無上升為“人格權”的現實需要,那么“人格權法”也亦無制定之必要。
通過對法律概念的邏輯學分析后,我們可以得出對“人格權”的法律保護有兩種模式。第一,權利保護模式。若一項事物是在主體之外的,以主體自身無法得出主體對該物的擁有,那么法律便以“權利”作為連接主、客體的紐帶。第二,主體保護模式。若一項事物是在主體之內的,通過對主體自身的保護便使該物得到了保護,此時,主客體發生混同,權利保護模式便喪失應有之意。
人之本體保護。康德將權利劃分為“天賦的權利”和“獲得的權利”,人格被視為“天賦的權利”,即與生俱來的自由與平等;物權、債權、親屬權被視為“獲得的權利”,屬于民法確認的對象。⑥《德國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雖都有條文對人格受到侵害給予保護,但都是作為主體資格進行保護的。這是由于傳統民法理論認為“內在于人”的人的倫理價值不可進行權利的保護,否則會打破傳統民法理論體系。
人格權的權利保護。傳統民法采納了“本體保護”模式對人格進行保護。但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人的倫理價值不斷擴張并伴隨著各種新型人格利益的出現,使得本體保護無法滿足現實生活的需要。
19世紀,美國學者布爾蒂斯在《法學評論》上首次提出隱私權的概念。德國法學家柯思奈在《肖像權論》中規制出了完整的肖像權保護法。⑦由于“人權運動”的發展,人的倫理價值已擴張到知情、信用、生活安寧等新興的人格利益,“主體保護”模式已無法涵蓋所有內容。由于這些新興的人格利益并不附屬于人本身,因此,若將他們分開并不會使我們對人之存在本身進行否認。因為由人存在這一法律事實,并不會得出知情、信用、生活安寧等人格利益的必然存在。
隨著社會的發展,現有法律已無法對人格利益進行全面的保護。因此,只有將其視為外在于人的各種價值進行權利的保護,用權利將人與各種要素連接起來,使其成為權利的客體,從而使民法典按照統一的法律邏輯體系對“人格權”制度進行實體法的全面保護,使法律在滿足現實生活需求的同時以實現民法典的工具理性與立法價值。
【作者單位:寶雞文理學院;本文系“寶雞文理學院科研計劃項目”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ZK12066】
【注釋】
①梁慧星:《中國民法經濟法諸問題》,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年,第56頁。
②尹田:“論法人人格權”,《法學研究》,2004年第4期。
③徐國棟:“‘人身關系’流變考”,《中國民法百年前瞻與回顧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④徐國棟:“尋找丟失的人格”,《法律科學》,2004年第6期。
篇(8)
時下,關于中國民法典制定的問題已引起學術界與政界的廣泛關注。體現的階段性成果之一就是徐國棟教授主編的《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在此書中,提出了所謂的物文主義與新人文主義對抗的問題。徐國棟教授在其文中主要就梁慧星研究員設計的民法典大綱從結構安排上發出了“見物不見人”的抨擊。無論其核心觀點的立論、論證正確、妥當與否,其就人格權法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問題,卻給了我們一個非常重大的提示,因為如何設計、安排人格(權)法正是“物文主義”與“新人文主義”爭論的一個焦點。本文就此問題提出若干粗淺看法,以就教于大方。
一、人格權法在民法典中設計的幾條思路
(一)大陸法系國家民法典中關于人格權法的幾個典型立法例
人格權是一個漸次發展、不斷完善且愈來愈受到重視的一個權利類型。因此,關于人格權法在民法典中的規定,因民法典制訂時間、采取的結構體例不同以及對人格權重視的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立法例。
《法國民法典》承繼羅馬法傳統,采三卷結構。第一卷:人。其中分為十一編,分別規定了民事權利、法國國籍(第一編之二)、身份證書、失蹤、婚姻、離婚、親子關系、收養子女、親權、未成年、監護及解除親權和成年與受法律保護的成年人。第二卷:財產以及所有權的各種變更。其中分為四編,分別規定了財產的分類、所有權、用益權及役權等。第三卷:取得財產的各種方式。其中分為二十編。分別規定了繼承、侵權行為與準侵權行為等。《法國民法典》在最初公布的時候,僅在其第九條規定:“所有法國人均享有民事權利。”據此,有學者分析,《法國民法典》對具體人格權不作規定,在立法者看來是不存在人格權問題。[①]后由1889年6月26日法律改為第8條,“所有法國人均享有民事權利”。由1970年7月17日第70-643號法律將第9條規定為:“任何人均享有其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權利。在不影響對所受損害給予賠償的情況下,法官得規定采取諸如對有爭議的財產實行保管、扣押或其他適用于阻止或制止妨害私生活隱私的任何措施;如情況緊急,得依緊急審理命令之。”隨著人格權日益受到重視,《法國民法典》依1994年7月29日第94-653號法律在第一卷人中增設了第二章:尊重人之身體。其于第16條規定,“法律確保人的首要地位,禁止任何侵犯人之尊嚴的行為,并且保證每一個人自生命一開始即受到尊重。”第16-1條至16-9條則規定了權利的具體內容。而關于人格權的保護,則由1382、1383等條加以規定。可見,法國法上人格權法是依附于人法的。
《德國民法典》所采體系是潘得克吞學派在注釋羅馬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潘得克吞學派極其深邃的、精確而抽象的理論的產物,它極其重視用語、技術和概念構成方面的準確性、清晰性和完整性。這個體系把民法典分為五編:總則、債權、物權、親屬、繼承。《德國民法典》將人格權的主體部分依附于侵權行為法,這是《德國民法典》創設的立法例。在《德國民法典》中,在總則部分只設第12條,即對姓名權加以規定,而在侵權行為部分,于第823條規定了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和自由權,于第824條規定了信用權,第825條規定了權。德國法對人格權的上述規定,是頗有其特點的,除了對姓名權的規定具有具體的內容外,其他關于人格權的規定都沒有具體的內容,只是規定當這些權利受到侵害時的法律保護方法。可見,這種立法例很難說人格權法在民事立法中具有獨立的地位,與法國法相比,其是將人格權法依附于人法而改變為依附于侵權行為法。《日本民法典》在總的體例上和關于人格權法的規定與德國法相似。《日本民法典》也分為五編:總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依1948年1月1日正式施行《改正民法一部分之法律》,《日本民法典》設置了第一條之二,“對于本法,應以個人尊嚴及兩性實質的平等為主旨解釋之。”其它有關人格權之規定僅在“侵權行為”一章中規定身體權、自由權和名譽權。
《瑞士民法典》共分為四編:人法、親屬法、繼承法、物權法,另有《瑞士債務法》。在《瑞士民法典》第一編人法中設了“自然人”和“法人”兩章。第一章“自然人”中設“人格法”和“身份登記”兩節。人格法共27條,其內容包括:(1)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第11條;第12條);(2)具備行為能力的條件與成年年齡(第13條;第14條);(3)限制行為能力的事由及效力(第16條及以后數條);(4)親屬及其類型(第20條;第21條);(5) 籍貫和住所(第22條及以后數條);(6) 人格的保護(第27條以后數條),這一部分規定了保護人格權的一般程序以及一些具體的人格權(如自由、姓名、名譽等);(7)人格的開始及終止(第31條及以后數條),規定權利能力的起止問題;作為權利能力終止的一種方式,這一部分規定了宣告失蹤。意大利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的體例編排基本一致,在序編以后,第一編為“人與家庭”,包括瑞士民法典中的人法編和親屬法編。第二編也是“繼承”。第三編為“所有權”。第四編為“債”。現行的荷蘭民法典也基本上采取了這種設計結構。第一編為自然人法和家庭法,第二編為法人。第三編為財產法總則,第四編為繼承法,其后各編是關于財產法的具體規定。
世界上單獨將人格權法列為單編的為數不多。烏克蘭民法典草案即為著例。[②]它包括如下7編:(1)總則;(2)自然人的人身非財產權(亦即我們所言的人身權);(3)財產權;(4) 知識產權;(5)債法;(6)家庭法;(7)繼承法。在法典草案的第二編中,用了47個條文規定了自然人的生命權、健康保護權、消除威脅生命和健康之危險權、醫療服務權、對自己健康狀況的知情權、個人健康狀況的保守秘密權、患者權、自由和人身不受侵犯權、器官捐贈權、家庭權、監護和保佐權、體弱者的受庇護權、環境權等為確保自然人的自然存在所必要的人身非財產權;另外規定了姓名權、變更姓名權、自己姓名之使用權、尊嚴和榮譽受尊重權、商譽之不受侵犯權、個性權、個人生活和私生活權、知情權、個人文件權、在個人文件被移轉給圖書館基金會或檔案館的情況下文件主人的受通知權、通訊秘密權、肖像權、進行文學、藝術、科技創作活動的自由權、自由選擇居所權、住所不受侵犯權、自由選擇職業權、遷徙自由權、結社權、和平集會權等為確保自然人的社會存在所必要的人身非財產權。這兩類人身權共計32種,大概是目前世界上關于人身權的最完備規定。其特色一方面在于將人身權法獨立成編,并緊列總則之后;一方面則在于其拓展了人身權的范圍,打破了在自然人權利領域憲法與民法的嚴格分工。
我國《民法通則》在第5章民事權利中列第四節為人身權,與第一節財產所有權和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第二節債權、第三節知識產權并列,以“權利宣言”的方式凸現了人格權法的獨立地位。《民法通則》中第98-105條正面規定了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等人格權。并在第6章民事責任中規定了人格權的民法保護。可見,我國民法通則從主體享有的權利出發,賦予了人格權法以獨立的地位,這是其所具有的進步性之一。[③]
可以看出,人格權法在各國民法典中規定的內容與形式皆有差異。究其原因
,大致有二:其一,人格權是一個隨著人類文明發展而不斷被“發現”的權利,因各國民法典制定的時間不同,對人格權的認識亦因此而有不同,囿于民法典的既有格局,各國民法典只有采取將人格權委之于相關制度規定的權宜之計,其最直接的后果在于各國法不得不以大量的判例填補民法典中人格權類型與保護之空白,由此造成了人格權法的“脫法典化”狀態。——此點正是我們所應著力避免的。其二,各國法上對人格權法位置之安排受制于民法典之整體結構。一般說來,在采用人法前置立法體例的民法典中,如法國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大都沒有總則,人格權法沒有獨立的地位,一般都被規定于人法之中。而在采物法前置立法體例的民法典中,如德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一般都設有總則,人法的范圍與前者相比為窄,人格權法無法列入其中,大多只能依侵權法來對權利加以類型確認與保護。
(二)我國學者對人格權法在民法典中設計的幾種觀點
有學者認為應單獨規定人格權。為保障人身權與財產權,突出民法以人為本的立法思想,作為與財產權居于同等重要地位的民法中的另一大類權利即人身權也應單獨規定。該學者指出,將人格權歸于主體制度中固然有其合理之處,但也應看到主體的人格與人格權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主體的人格是指人作為主體的資格,是人行使民事權利、履行民事義務的能力,是指民事權利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人格權中的人格是指人格利益,是權利的內容,具體地講是人身健康、生命安全、名譽、肖像、隱私等人格利益,不是指主體。同時,該學者認為對人格權的規定不能全委之于侵權法。因為人格權需要由法律來列舉確認,才能成為侵權法保護的對象。侵權法只能起到保障的作用而不能起到確認權利的作用。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也需要通過建立人格權法制度來形成一種開放的體系,不斷擴大人格權保障的范圍。[④]
有學者認為,人格權法不設專編,將民法通則第五章第四節關于人格權的規定納入總則編自然人一章,并認為,所謂人格權,是自然人作為民事主體資格的題中應有之義,沒有人格權,就不是民事主體。其二,人格以及人格權與自然人本身不可分離,并且如果人格權單獨設編,條文畸少而與其它各編不成比例,且對人格權的尊重和保護重在內容而不在于是否單獨設編。此種思路乃貫徹法典的設計應以生活自身和法律概念的邏輯性和體系性為標準,而非以重要性為標準來設計人格權法。[⑤]
有學者認為,如德國式民法典為“見物不見人”,應高舉“新人文主義”大旗、以制度的重要性為標準來凸現結構之含義,建構以人為中心的民法體系。[⑥]該學者認為,應在學理中用人的“主體性要素”的概念(指人之所以作為人的要素或條件)來涵蓋人格、人格權以及與它們相關的問題,以純化“人法”的主體法特性。因而,在立法上應將人格權的規定納入人法之中。用有如瑞士民法典“人格法”的上位概念來解決人格與人格權同規定于民事主體制度之中的矛盾。自然人的權利能力、行為能力、籍貫、住所、身份登記等,與人格權一道都屬于與人格相關的問題,“出于便宜的關系,由人格法一并調整。”[⑦]
實際上,上述學者的主張可大體上分為兩種觀點。一種是王利明教授認為的人格權法應獨立成編;另一種觀點是梁慧星研究員、徐國棟教授認為的人格權法沒有必要獨立成編,應將其納入人法之中。第二種觀點內部的不同之處僅在于徐老師認為對人格權的理解應該更廣一些,涵蓋以人的主體資格為保護對象的人格權,以統攝于“人法”的主體性質所要求的“主體性要素”之下。
二、關于人格權法在民法典中設計的理論反思
縱觀各國立法例與我國學者的觀點,大致可分為三種觀點:其一,應將人格權法歸入民事主體制度之中;其二,應將人格權法委之于侵權法;其三,應將人格權法單獨成編。如何進行頗為理性的選擇,使得我們不得不進行如下的理論反思:
(一)人格權法能否納入民事主體制度之中?
法律上的人格有三種含義:其一,人格是指具有獨立法律地位的權利主體,包括自然人與法人。在這一意義上的人格概念,經常與主體、權利主體、法律主體、民事主體等民法概念相互代替。此時之人格乃是人格權的承載者,是人格權存在的前提。其二,人格是指作為權利主體法律資格的民事權利能力,在此意義上的人格概念,經常與民事權利能力或權利能力概念相互代替。此種意義上之人格,乃為人格權的存在基礎。其三,人格是指一種受法律保護的利益,包括人的生命、身體、健康、自由等,為了區別于其他受法律保護的利益如財產利益,又稱為人格利益。此種意義上之人格,乃為人格權的標的。[⑧]前兩種意義上的人格,或是主體本身,或是成為主體所要求的,可以說乃屬民事主體制度規制無疑。而第三種意義上的人格則因自民事主體產生即屬其專屬享有,因此與民事主體制度的關系很難厘清。可能正是在此意義上,才有學者認為應將人格權與民事主體制度(人格)一并規定。可以看出,因人格權為民事主體所專屬,具支配性、排他性,且與民事主體“同步”,于此意義言,將人格權法納入民事主體制度的思路頗有道理。但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人格權與民事主體制度不宜規定于一處。理由如次:
首先,將人格權納入民事主體制度之中,會混淆人格與人格權概念,造成事實上人格與法律上人格模糊的狀況。人格在民法中如上文所述,可在三種意義上使用,但第三種意義上的人格與前兩種意義上的人格,則屬不同的概念范疇體系。人格在前兩種意義上被使用,可被概括為具有獨立法律地位的民事主體和作為民事主體必備的民事權利能力。這種人格概念的最基本特征是從法律上直接賦予或由法律抽象,因此我們將其稱之為法律上的人格。人格在第三種意義上被使用,它是表露在事實層面上的人之作為一個人所必備的要素,這是作為權利客體的一系列利益的總稱,它在性質上及構成上不同于與法律主體和權利能力等值的法律人格。因此它是一種事實人格。“法律人格與事實人格是性質各異的兩個概念,法律人格關乎民事法律關系主體地位的確定,在民法體系上屬于民事主體范疇;事實人格作為人格權的客體,則是民事權利體系中的內容。”[⑨]
其次,人格權與民事主體制度表征不同的范疇體系。其一,民事主體制度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是法律關系的主體的確立問題,而人格權則是作為民事主體之間產生的一種相互尊重對方人格尊嚴的訴求,經由法律確認與保護之后而體現的“人之為人”本質要求的一種狀態。即,人格權者,必為一定法律關系之中的人格權,其與他方之人格上義務相對,乃為表征主體間法律關系之范疇。“這樣的主體間的關系制度,在邏輯上與主體資格制度沒有聯系。而且,人格權的某種缺損狀態也不會影響民事主體資格,而只是影響到民事主體的具體的人身利益問題,舉例來說,政治家的隱私權受到限制,這并不影響政治家在民法上的主體資格。”[⑩]誠如斯言。并且,我們認為,將人格權規定于民事主體制度之中,將無法合理解釋為何人格權的類型越來越多而現代民法中民事主體資格幾乎未見變化的原因。其二,在民事主體制度中,自然人、法人之住所、權利能力、行為能力等皆為強行性確認規范范疇;而人格權乃為任意性授權規范范疇。前者無侵犯可能;后者為民事權利類型之一,必涉權利的保護問題。
再次,將人格權納入民事主體制度規定之中,會導致法典劃分標準的偏差與內部的不和諧。正如有學者謂,民法典的結構和編排,不能以所謂重要性為標準,只能以邏輯性(生活本身的邏輯和法律概念的邏輯)、體系性為標準。[1
1]就邏輯性而言,將主體享有的權利與主體本身規定于一處很難謂邏輯嚴密。況且,以人格權與民事主體密不可分立論,[12]也難謂邏輯性正確。蓋因為,無論按梁老師的七分法,還是按徐老師的兩分法,其在基本認識上都毫無疑問地承認民事權利可分為財產權、人格權、身份權之分類,但為何獨人格權被納入民事主體制度之中,只余財產權、身份權等支撐民法典中民事權利的架構?為何物權、債權、親屬權等是按權利的性質而設置于法典之中,而獨人格權是以與民事主體密不可分為標準?且無論親屬權(身份權)也與民事主體密不可分了——劃分法典各組成部分的標準不統一,難謂邏輯性周全。就體系性而言,民法中以財產權與非財產權(人身權)為基本分類,如將人格權納入民事主體制度,民事權利的體系在形式上就會形成一個大的空缺,從而導致體系性無從體現。其結果可能會使通過民法典來梳理民事權利使之類型化的努力大打折扣。
復次,將人格權納入民事主體制度,不利于人格權的保護。人格權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而不斷發展著的權利類型。與民法中其它權利類型相比,其產生較晚,較不完備,如隱私權的確立不過為20世紀初之事即為著例。同時,隨著人主體意識、權利意識的覺醒以及科技發展使人格利益受侵害的便宜度的增大,使得人格權必須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囿于民事主體制度中必會阻礙新型人格權類型的承認,從而不利于人格權的確認與保護。同時,因當代社會中包括隱私權、權、生活安寧權、聲音語言權及意思決定自由權[13]等人格權益的迸出,如不在制定民法典時就人格權作以周密規定,將會遺留下一個只能靠大量運用判例形式創設新的人格權類型的此現在可以被有效避免的后遺癥。
最后,將人格權納入民事主體制度之中,很難制定出一部能體現時代特色的民法典。制定于200年前的《法國民法典》幾乎沒有關于人格權的規定;制定于100多年前的《德國民法典》也僅在侵權法部分提及了人格權的保護;制定于90多年前的《瑞士民法典》在人格權立法上的貢獻之一無非就是明確提出了一般人格權的概念。因此,套用百多年前的民法典結構而制定出的中國民法典充其量不過是屬于二十世紀的,能為異軍突起的人格權創設一個獨立地位的民法典才是尋求體現新時代特色、統領世界民事立法潮流的民法典的必由之路。在這方面,烏克蘭民法典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
(二)人格權的規定能否由侵權法概括完全?
《德國民法典》開創了將人格權的規定由侵權法調整的先例。在《德國民法典》中,明定的人格權類型有姓名權、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自由權、信用權、權;第823條集中規定了人格權的保護。后經法院造法,創造性地解釋第823條中的“其他權利”,在判例中承認了若干具體人格權和一般人格權。這種局面是與當時的立法技術和對人格權重視的程度息息相關的。這雖然在人格權的保護效果上與正面規定人格權幾乎殊無二致,但亦有下列兩點弊端存在:
其一,侵權法難以發揮確認權利的功能。侵權法是人格權民法保護的重要方法,但其涉及的都是對人格權如何保護的問題,對于新的權利類型承認之功能因其制度本旨所限,發揮之余地必將不大。正如物權法之于物權一樣,其不只是保障物權的法律,更重要的是確認物權的法律。“通過確認權利,使權利具有穩定性,進而在交易中增加財富,這是確認權利所獨有的功能,是保障權利所不能代替的。”[14]通過人格權的正面規定,一方面可以使人們明確民事主體所享有的人格權益,有助于廣大公民、法人運用法律的武器來捍衛自己的人身權益;另一方面則可從權利性質的角度厘清此人格權與彼人格權的界限,為侵權法的保護提供理論上的支持。
其二,侵權法并非是人格權保護的唯一手段。在人格權的民法保護中,除損害賠償須委之于侵權法之外,尚有人格權保護請求權的存在。如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18條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另有如《瑞士民法典》第28條的規定。此外,尚有財產法上不當得利請求權適用之余地。[15]由此可見,侵權法不能完全承載人格權的保護。
總之,我們認為,民法就是一部權利法,是一個在私的領域的“權利宣言”,用正面確認權利及反面保護權利的方式無疑是該“權利宣言”的最佳表現形式。
三、關于人格權法在中國民法典中的具體設計
(一)體例設計
結合上文的論述,我們認為,人格權法應在民法典中單獨成編。理由如次:
首先,人格權獨立成編是總結先進立法經驗的需要。我國《民法通則》在民事權利一章中單獨規定了人身權利這一節,這是一個重大的體系突破,也是其他國家民法典難以比擬的立法成果,是先進的立法經驗。同時,實踐也證明民法通則這種規定對公民、法人知法、守法,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利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人格權獨立成編是順乎歷史發展規律、展時代特色的需要。人格權是一個不斷壯大的權利群,從各國民法典的修改與補充就可以看出此點。如《法國民法典》的修改與補充即體現所謂“無則有之”及“有則增之”的趨勢。甚至出現了烏克蘭民法典草案中包括遷徙自由權、結社權等非民事權利在內的32種人格權。由此趨勢而言,我們所要制定的民法典就應該充分規定人格權,使之成為一部充滿時代氣息,以維護人的權利為己任,以人文關懷為中心的“權利書”,單獨設編最能體現此點要求。
再次,人格權獨立成編是權利宣示與保護的需要。人格權單獨成編,有如民法通則一樣正面規定若干人格權,如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權、生活安寧權等等,有利于人們明確自己所擁有的人格權利、所能選取的法律武器。同時,用有如構成要件式的規定可以厘清人格權保護的范圍與界限,這種類型化的努力也有利于對權利的保護。蓋因為如法律僅加以簡單的規定,“在我國靠法官的判決來保護這些新型的人格權,是講不通的。”[16]
最后,人格權獨立成編是法典邏輯性和體系性的要求。在民法體系中,是以權利性質的不同來作為區分各編的基本標準的。人身權作為與財產權相對應的權利,無論從其實質上還是從形式上都應在民法典中占有一席之地。
對于有學者認為人格權法由于條文較少不宜單獨成編的觀點,我們認為,這種說法雖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民法典的制定首先考慮的應是邏輯性和體系性,只有在不損害邏輯性、體系性的前提下,才可以顧及協調性問題。以形式上的協調性來犧牲整部民法典的邏輯性和體系性、破壞整部法典精神的一以貫之性,實在是得不償失之舉。
至于人格權法在民法典中的具置,因與整部民法典所采用的結構體例有關,故其位置不好確定,但我們原則上認為,人格權法應作為獨立一編,置于總則之后,以凸顯人格權法的重要性。
(二)內容設計
如人格權單獨成編,由于其條文較少,建議原則上在該編內不分章節,但如果在人格權法中規定精神損害賠償,則建議可分章節(容下文詳述)。
建議此編首條用描述性語言規定人格權的涵義。涵義中應明確人格權之于人之價值、人格權的性質等,鑒于人格權乃為“天賦人權”,[17]用封閉式的定義有違其本質,因此建議用描述性語言形成一個人格權的開放體系。
建議第二條規定人格權的享有主體。明確規定自然人(包括合伙等)、法人享有與其本質相適應的人格權。
建議第三條規定一般人格權。一般人格權概念的提出,是近現代破除“法典萬能論”、賦予
法官自由裁量權運動的結果。可以說一般人格權的出現,是人格權發展歷史中最為重要的一步。因此我國民法典對此應予以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的“人格尊嚴權”[18]和“其他人格利益”已見一般人格權的端倪。這一立法成果可被我們批判地吸收。在此條中,應明確規定一般人格權內容包括人格獨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人格尊嚴(人格獨立為其前提;人格自由為之本質要求;人格平等為其保障;人格尊嚴為之核心)。由于一般人格權體現的是人格權具有無差別性的最本質要求,因此,本條亦可以人格權的內容待之。
建議第四條規定人格權上保護請求權。人格權為絕對權、支配權,自當如物權一樣生“物(人格權)上請求權”。[19]此條中應明示或隱蘊此種請求權的行使不以過失為必要,受害人僅須證明不法侵害即可獲救濟。[20]考慮到物權請求權中返還原物請求權與人格權性質不符,建議規定兩種人格權保護請求權:妨害防止請求權和妨害除去請求權。并侵權損害賠償責任中的財產損害賠償與精神損害賠償(撫慰金),構成本條。具體條文擬定如下:“人格權受侵害時,權利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的危險時,可請求防止之。前款規定,以法律有特別規定時,始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撫慰金。”
建議第四條以下規定各具體人格權。為從立法上厘清此人格權與彼人格權的界限,應以構成要件方式說明各個具體人格權。建議規定如下業已經立法和司法實踐檢驗的已較為類型化的具體人格權,包括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須注意在名譽權的保護中有恢復名譽這一保護方法)、隱私權、自由權、信用權、權等。為與前條呼應,建議在每一個具體人格權內容之后規定何種情形受害人可要求撫慰金。
建議具體人格權之后的數個條款應規定胎兒與死者人格利益的問題。目前學術界對胎兒、死者人格利益保護(尤其是后者),爭論還很大,存在“權利保護說”、“近親屬利益保護說”、“家庭利益保護說”、“法益保護說”及“延伸保護說”等諸多學說。[21]在制定民法典之時,應在進行理論甄別的基礎上,擇取一種學說將其作為法律根據。并應明確規定該請求權的行使主體、范圍等問題。另外,對于法人是否有延續人格利益的問題、如何進行保護的問題也應在此處明確。
建議該編最后數條規定人格權的保護方法,包括民法上的保護(主要是侵權責任)及可援引公法救濟之條款。至于精神損害賠償究竟應放入侵權責任之中還是人格權之中,殊值研究。從侵權責任的后果角度而言,應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侵權責任之中。因為侵權責任的后果主要是損害賠償,而損害賠償應當包括侵害財產權的賠償、人身傷亡的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這三種損害賠償可以共筑一個侵權責任承擔方式的完整體系,使得邏輯嚴密。但將精神損害賠償放入人格權法中也不無道理。一方面,該制度主要保護的是人格權,而不是財產權;另一方面,對特殊權利的侵害應當實行特殊的救濟方式,救濟應當是與權利始終在一起,只有完整的救濟方式才能使民事權利產生出應有的效力。對物權侵害有物上請求權與之對應,對合同侵害有違約責任予以救濟,從此意義言,將精神損害賠償放在人格權法中也不無道理。[22]我們認為,該問題不僅與人格權法自身有關,至為重要的是該問題與整個民法典的結構體例安排有關。如果侵權法獨立于債法單獨成編,為純化侵權責任,自應將精神損害賠償置于侵權法之中,僅在人格權法部分簡單提及。如果侵權法不獨立成編,我們認為,則可依王利明教授之建議將精神損害賠償歸于人格權法調整,并置于該編最后位置規定。但此時,人格權涉及到人格權的一般規定、人格權的保護、一般人格權、具體人格權以及精神損害賠償等諸多不同層次問題,建議分章節將之清晰化、條理化。
[①] 梁慧星:《中國民法經濟法諸問題》,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頁。
[②] 資料來源于徐國棟主編:《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10版,第168頁。
[③] 雖然我國《民法通則》并不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民法典,但其理論的創新、結構體例的安排無疑會對民法典的制訂起到一定的啟示作用,因此本文將其作為一種立法例來加以討論。
[④] 王利明:《論中國民法典的體系》,載于徐國棟主編:《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⑤] 梁慧星:《當前關于民法典編纂的三條思路》,載于徐國棟主編:《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9-13頁;《中國民法典大綱(草案)》總說明。
[⑥] 以此為出發點,徐國棟教授設計了他的民法典草案的基本結構:序編:小總則;第一編:人身關系法;包括第一分編自然人法,第二分編法人法,第三分編親屬法,第四分編繼承法。第二編:財產關系法;包括第五分編物權法,第六分編知識產權法,第七分編債法總論,第八分編債法各論。附編:國際私法。
[⑦] 徐國棟:《兩種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義對物文主義》,載于徐國棟主編:《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75頁。
[⑧] 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03-104頁。
[⑨] 姚輝:《人格》,摘自civillaw.com.cn.
[⑩] 薛軍:《理想與現實的距離》,載于徐國棟主編:《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205頁。
[11] 參見梁慧星:《當前關于民法典編纂的三條思路》,載于徐國棟主編:《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9頁。
[12] 此密不可分性,按梁慧星老師的說法是指,“人格權是自然人作為民事主體資格的題中應有之意,人格以及人格權與自然人本身密不可分。”(參見梁慧星:《制定民法典的設想》,載于《現代法學》2001年第2期。)但由此立論,似有否定法人人格權之嫌。
[13] 參見王澤鑒:《侵權行為法》(第一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38-139頁。
[14]王利明:《論中國民法典的體系》,載于徐國棟主編:《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19頁。
[15]參見王澤鑒:《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28頁。
[16]王利明:《論中國民法典的體系》,載于徐國棟主編:《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19頁。
[17] 王小能 趙英敏:《論人格權的民法保護》,載于《中外法學》2000年第5期。
[18] 在此解釋中,將“人身自由權”與“人格尊嚴權”相并列。我們認為,人身自由權僅為人格自由“物化”(具體化)的形式之一,因此屬一種具體的人格權,其不能與人格尊嚴并列。“人格尊嚴權”之稱謂排除了所謂人格法益,與人格權之“天賦人權”性質不符,應稱為“人格尊嚴”。
[19] 在我國《民法通則》之中,傳統大陸法系國家民法典規定的物權(人格權、知識產權)請求權被納入侵權責任的承擔之中。由此導致受害人尋求救濟的唯一途徑就是證明侵權責任的成立。此既不能防止侵害的發生(因侵權責任的成立必要求損害的事實存在);也不利于受害人權利的快捷且有效的救濟。此問題涉及對我國民法上的侵權責任本質的認識與民事權利保護體系的構建,筆者將另文探討。關于此問題的相關探討,可參見張農榮:《侵權行為、歸責原則及侵權責任構成辨正》,載于楊立新主編:《侵權法熱點問題法律應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1月版。姚輝:《關于
人格權的兩個日本判例》,載于《人大法律評論》2001年卷第1輯。鄭成思:《侵害知識產權的歸責原則與“侵權四要件”》,載于《判解研究》2000年第1輯。吳漢東:《試論知識產權的“物上請求權”與侵權賠償請求權——兼論《知識產權協議》第45條規定之實質精神》,載于《法商研究》2001年第5期。彭誠信 傅穹:《物權的自我救濟》,載于《法制與社會發展》1999年第6期。
篇(9)
在民法總則中納入環境規范中的一般化規范,提取環境規范中的公因子內容。民法總則作為對民法分則各部分提取公因式的產物,是高度抽象化的結果。目前《民法總則草案》共分為n章,包括基本原則、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組織、民事權利、民事法律行為、、民事責任、訴訟時效和除斥期間、期間的計算、附則等。從部分條款來看,該草案納入了部分環境規范的條款,具備鮮明的時代特征。其中,第七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保護環境、節約資源,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該條文在民法學界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反對論者認為該條款的加入徒然增加了民法典的不當負擔,屬于應當刪去的條款,也有觀點認為此類無害條款不會對整個民法典產生損害,可予以保留,并不會發揮規范作用。實際上,在民法典中的基本原則部分加入環境保護的基本原則,不僅宣示了民法典的基本價值取向,對日后所產生的環境相關糾紛同樣具備重要的指導價值,應當在未來的民法典中予以保留。此外,該草案第一百六十條第(五)項增加了修復生態環境作為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從責任端融入了環境保護的規范因子。
盡管《民法總則草案》在前兩個條文中納入了一定環境保護規范的內容,但是在實質體系上仍然存在諸多缺失。首先,在民事主體與客體部分,未能反映環境法律主體與客體內容,仍然停留于主體客體的二元區分層面。從主體層面而言,可考慮納入完全主體之外的非完全主體(準主體),并由此避免將非人物種人類化或者保護不足的困境。在客體層面,環境法客體雖然與民事客體存在明顯區別,但通過類型化的方式仍然可以確定為物與行為,并由此構建起交易客體與權利客體范疇,搭建起完整的環境法律關系鏈條,以回應業已出現的環境交易制度。其次,在基本民事權利部分中,應當納入環境權利的基本范疇,并通過具體規范明確環境權的法典地位。目前,總則草案遵循人格權與財產權的基本劃分思路,并進一步區分為物權、債權、知識產權、繼承權等權利類型,構建了較為開放的權利體系。環境權利作為環境保護的權利基點,應當將其與民法制度進行整合銜接,可采取對現行民法制度中關系到環境法的部分進行生態化解釋或對接,或者對于現行民法制度中沒有的環境規范建立起新的制度回。將環境權作為人格權的一部分,雖然具有財產性內容,但實質意義上更加關涉個人的生存權以及自然地位。通過構建明確的權利條款有助于為環境私法提供請求權基礎,避免保護空自。
妥善處理環境規范與物權法的關系
在物權法中,與現有環境規范存在緊張關系的主要是動物、植物、生態環境等的規范地位問題。譬如,在動物的法律地位問題上,《德國民法典》第90a條規定,“動物不是物。動物受特別法律的保護。除另有規定外,關于物的規定準用于動物。”該條雖然出現在《德國民法典》的總則部分,但其規范對象是動物的法律地位問題。在我國未來的民法典中,即使總則部分不能予以明確涉及,在物權法部分也不應忽略。進一步而言,動物的法律地位問題反映了既有的物權制度與環境資源之間的緊張關系,包括陽光、水、土地、空氣等在內的資源。其一方面關涉到所有權人的福社,另一方面又關系到社會福社。作為物質性的存在形態,環境資源應當在物權規范中予以體現,包括物權法的一般規定以及具體的保護規范。常紀文建議將環境作為特殊的民事權利客體進行規定,并且對一些生態功能具有財產價值的環境資源確認其財產權,將其視為動產囚。
妥善處理環境規范與合同法的關系
篇(10)
居住權為羅馬法上人役權的一種,其出現晚于地役權。包括用益權、使用權、居住權和奴畜使用權四種。用益權(usus fructus)指無償使用收益他人的物而不損壞或變更其物本質的權利。[②]使用權(usus)指權利人在個人需要的范圍內,對他人的物按其性質加以利用的權利。兩者的區別在于用益權包括使用及收益兩種權能,而使用權僅是在個人需要的范圍內使用他人之物。“故關于用益權中收益之規定,于此不適用之。……使用權人不得移轉其權利之全部或一部于第三人。或由第三人行使其權利。則又用益權與使用權之區別也。”[③]由此可見,使用權權利的范圍較用益權窄。居住權(habitatio)是指居住他人的房屋的權利。其產生遠在其他人役權產生之前,最初僅作為受遺贈人享受某種利益的事實,在人役權的規則形成以后,判例上為了維護遺囑自由的原則,尊重遺贈人的意志,對舊有習慣未加改變,造成了居住權與前述使用權的差異,具體表現為,居住權不因使用者不行使或人格變更而消滅并且享受此項利益的人還可以把標的物出租[④]故居住權“即變相之用益權、使用權而已。但其范圍,廣于使用權而狹于用益權。其終止之原因,亦少于上述兩種物權,故雖從此蛻化而成。實亦個別之物權也。”[⑤]由此可見,在地役權和人役權的二元結構體系中,居住權是層層縮小和受限制的用益權,是用益權的下屬概念。
《法國民法典》對于非所有人因居住而使用他人房屋的權利,基本上承襲了羅馬法。該法典在第578~624條規定了用益權,第625~636條規定了使用權和居住權。其中第578條規定了用益權的概念:“用益權是指,如同本人是所有權人,享用所有屬于他人之物的權利,但享用人應負責保管物之本體。” 使用權(第625~631條)為用益權的一種,而居住權則為一種使用權,并適用使用權的規則。因而從性質上講,使用權與居住權是在效力上減弱了的用益權。所以,在法國,居住權被稱為“小使用權”,使用權又被稱為“小用益權”。[⑥]
《德國民法典》在第五章“役權”中規定了地役權、用益權和限制的人役權。 “和地役權相比,限制的人役權強調該權利為某個人利益,即為某一特定的人設定的役權,而不是為了土地的利益;和用益權相比,限制的人役權具有只能在不動產上設立,而且只能為某一特定的人設定的特點。”[⑦]這一權利的主要形態為居住權,即 “將建筑物或建筑物之一部分當作住宅予以使用,并具有排除所有權人之效力”的權利(民法典第1093條)[⑧]
此外《瑞士民法典》在“用益權及其他役權”中規定了居住權,并進一步說明在“本法無相反規定時,居住權適用用益權的有關規定”(第776條第3款)。《意大利民法典》、《澳門民法典》均專門規定了用益權、使用權和居住權。
縱觀歐陸各國近現代民法典,幾乎都有居住權的規定。雖然各國制定民法典時的政治經濟條件和社會、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近現代各國民法典以及它們與羅馬法之間都具有很多共通之處。根據對羅馬法以及近現代各國立法例的考察,筆者認為民法典中的居住權制度有以下共性:
首先,居住權在民法典中的體例安排基本一致。在規定了居住權的民法典中都首先承認地役權和人役權的結構劃分,然后將居住權作為人役權的一種而規定在用益權(或使用權)之后。在具體的法律適用上,居住權更是離不開用益權。如《瑞士民法典》第776條第3款規定“本法無相反規定時,居住權適用用益權的規定。”《澳門民法典》第1416條:“規范用益權之規定,如符合使用權及居住權之性質,則適用于使用權及居住權”等等。
其次,居住權的權利義務設計基本上沿用了羅馬法的規定。從羅馬法開始居住權就具有很強的人身依附性,不得轉讓、繼承和出租,也不可以就居住權設定抵押權以及其他任何權利負擔,從而導致了居住權的封閉性和不可流轉性。近現代各國關于居住權的規定基本上沿襲了傳統,但是也意識到了居住權制度規定的不足,紛紛尋求解決的途徑。如法國法規定可以約定設定權利義務,德國法創設了“繼續居住權”等。
最后,自從羅馬法以來居住權的功能并未發生根本變化。羅馬法設立居住權等人役權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決沒有繼承權而又缺乏勞動能力的特殊群體的生活問題。因為古羅馬時期,只有家長才是民事主體,因此,除可以取得家長權的兒子外,家屬中的多數人不能取得家長遺產的所有權,為使這些需要照顧的人獲得生活保障,羅馬人經常以遺囑將某項遺產的使用、收益權遺贈給他所需要照顧的人,待受照顧的人死亡后,繼承人再恢復其完全的所有權。人役權的這種生活保障功能在的現代民法上仍然沒有多大的改變,主要在供養和撫養以及為自己養老方面發揮作用,[⑨]但無論怎樣,居住權都僅與日常和家庭生活有關,都具有人身性和社會保障性質,只是各國表現方式不同而已。
二、西法東漸過程中居住權衰微的原由
人役權作為一種所有權的負擔,是對所有權的重要限制,隨著歷史的發展,法國、德國、意大利、奧地利和瑞士等國的民法中仍有規定,而日本民法和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卻只規定了地役權,探究其原由對于我國適當做出制度的取舍頗具借鑒意義。1893年日本以《德國民法典》為藍本而制定了《日本民法典》,沒有規定用益權、居住權等人役權制度。臺灣地區民法典雖然以大陸法系各國民法為主要參考,尤其是參照了德國民法、瑞士民法中的制度,也沒有規定居住權。鄭玉波先生認為《日本民法典》未設用益權等人役權是因為“人役一項該國無此習慣,且復有礙于經濟之流通,故僅取地役權。”[⑩]然而,對照《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并非只有人役權制度在日本、中國等國家沒有習慣,屈茂輝認為其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對用益權功能的認識使然。制定《日本民法典》和臺灣地區民法時,用益權主要還是養老的功能,其養老之外的其他功能還沒有得到發展和承認,而日本和中國都是實現家庭(家族)養老制度的,加之普遍缺乏家庭成員之間的平等、獨立觀念,故用益權等人役權的東漸命運只能是“消失”,不為民法所確認。[11]這雖然也有一定道理但日本民法典至今歷經了30余次修訂均未提及居住權,正在修訂中的臺灣地區民法典也沒有意思要增設居住權。[12]即使是上世紀90年代新制定的越南、俄羅斯等國民法典也沒有規定居住權,因而,在西法東漸過程中居住權的衰微必另有原因。
羅馬法時設立人役權是為了照顧某些特定人的利益,旨在解決因嚴格的市民法而無市民資格的人獲得土地利用的問題,[13]其后,法德等國制定民法典時這種需要雖仍然部分存在,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于這些國家是以羅馬法作為藍本而制定本國民法典的,在羅馬法直接影響下,必然表現出制度的歷史慣性和強烈的羅馬法情結。這就使得各國雖然認識到了 “用益權來自于羅馬法,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其無重大的實質性變化,因而不可避免地帶有沉重的歷史負擔。作為孕育于一個鄉土、田園社會(農業社會)的制度,用益權難以適應于一個嶄新的工業的金錢社會。”[14]也看到了其適用范圍有限等眾多缺陷,[15]但是各國還是毫無例外地規定了用益權和適用范圍更為狹窄的居住權。因此,近現代各國民法典中規定居住權更主要的是基于歷史和傳統的原因而非科學的原因。[16]
當日本等東方各國制定民法典的時候,嚴格市民資格的限制已經被打破,封建社會以來的一定家庭成員間的養老育幼義務也得到了現代法律的認可,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國家都遠離了羅馬法的直接影響,能夠以理性的態度來對待居住權制度的弊端,果斷地拋棄了人役權和地役權的劃分,舍棄了居住權等人役權的規定。我國經濟的、歷史的、文化的傳統背景與日本等國相似,是否有必要重新拾起這一古老的、帶有諸多缺陷的居住權制度,確有商榷之處。
三、我國物權法中規定居住權的必要性
由前所述,居住權只有在地役權和人役權二元結構體系中才能找到自己的準確定位,而且也只有在人役權的框架內才能系統、合理地構建居住權制度。縱觀各國關于居住權的立法例,其居住權的具體規范大多需要援用用益權的規定,而后者則擁有龐大的規則體系。比如:《法國民法典》第二卷第三編規定了用益權、使用權和居住權,其絕大多數條款是關于用益權的規定。《德國民法典》從第1030條至1089條用了60個條款的篇幅對用益權作了規定。我國物權法征求意見稿中于第十八章創設了居住權,總共只有8個條文。第二百零八條規定:居住權人對他人住房以及其他附著物享有占有、使用的權利。第二百零九條規定:設立居住權,可以根據遺囑或者遺贈,也可以按照合同約定。根據物權法草案討論會上專家的發言,創設居住權主要是為解決三種人的居住問題即父母、離婚后暫未找到居住場所的夫或妻以及保姆。這三類人的居住問題是否必須通過設定“居住權”來解決呢?
首先,看一下父母的居住權。梁慧星教授認為德、法民法典最初規定居住權是為了解決男女不平等所帶來的養老問題,丈夫死后,妻子沒有繼承權,財產只能歸子女,為了解決母親的居住問題才創設了居住權。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才逐步規定了男女平等,承認了妻子對丈夫的繼承權,母親對子女的繼承權,在這種情況下原來的居住權已失去了實際的意義。而我國很早就確立了男女平等的原則,夫妻之間互有繼承遺產的權利,父母可以作為第一順序繼承人來繼承子女的遺產。同時,還規定了子女有贍養父母的義務,所以在我們的社會中,父母居住不發生任何的問題。這種觀點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父母居住不發生任何問題的論斷稍嫌武斷。當然,退一步講即使出現了父母居住的問題,在現有的法律框架體系內也可以解決。為實現父母養老的功能而保留居住權的買賣,可以由附條件的房屋買賣或抵押貸款來代替,而通過遺囑或遺贈設定居住權可由附條件的遺贈或遺囑所替代,從理論講上它們的效力可能有所不同但結果可謂殊途同歸。而且,從國外和我國的現狀看,家庭的撫養、養老等問題越來越多地由社會福利、社會保險來完成,另外隨著房屋租賃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物權化,使得上述情形發生的可能性不斷降低。
其次,離婚后暫未找到居住場所的夫或妻的居住權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七條中使用了“居住權”的表述,但筆者認為這并不是我們所說的作為人役權的居住權。因為在我國現行的物權法中還沒有確立居住權制度,這里提到的“居住權”應是另有所指。我國以前實行的是公房制度,房子是公房屬于單位,夫妻雙方在離婚時單位自然不會同意將自己的房子分一半給另一方非本單位的職工。出現了這種情況,實務中法院通常會判決房屋歸分房的一方,但另一方有權在原房屋中居住,直至其再婚。這種權利的性質有待研究,有的學者認為“離婚配偶對對方房屋的使用權,其性質亦為一種居住權”[17]筆者認為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如果另一方再婚了,就不能繼續在原房屋中居住下去,即使另一方不再婚,分房的單位一般也不會允許其永久的居住,而筆者前所論及的居住權是一種永久居住的權利,兩者之間有本質的差別。如今,公房制度已被廢止開始逐步推行商品房,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住房,上述“居住權”產生的歷史條件已不復存在了。在現實生活中如果出現了離婚時一方住房困難的案例,法院仍然可以按照先前的做法,判決允許沒有房子的一方可以在原房屋內繼續居住直至再婚,沒有必要再創設居住權。另外,參照國外的立法例,如《澳門民法典》第1648條規定:“基于考慮夫妻中每一方之需要、子女之利益及其他應予考慮之原因,法院得應任何一方之請求而命令將家庭居住之房屋租予該方,而不論此房屋屬雙方共有或屬他方個人擁有。”這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因“一方生活困難”而用“居住權”的方式給予幫助的制度非常相似,據此有人認為我國司法解釋中所說的居住權指的就是承租權。[18]實際上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的規定與《澳門民法典》上的規定并不相同。《澳門民法典》中對于住房困難的一方賦予了對原住房屋的承租權,從字面的意思看來要賦予這樣的權利需要綜合考慮多方面的原因,如離婚各方的需要、子女的利益等等,不僅僅局限于我們國家所規定要“一方生活困難”。也就是說澳門民法中的規定是各方利益綜合平衡的結果,也包含著對住房困難的一方進行幫助的意味。而我國的規定僅限于物質幫助的目的,本來一方當事人就經濟困難,如果將這種離婚后允許沒有住房的一方居住原住房的權利比照澳門民法的規定理解為承租權于設定這一規定的目的不相吻合。筆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第二十七條所指的“居住權”既不是人役權制度中的居住權也不是承租權,僅僅是為離婚后經濟困難的一方進行物質幫助的一種表現形式。因為無論是租房還是買房都是要花錢的,通過為經濟困難的一方或一時找不到住房的一方解決一定時期的居住問題,一方面,為經濟困難的一方節省了開支;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對弱者進行物質幫助的立法目的。
再次,是保姆的居住問題。正如梁慧星教授所說中國幅員遼闊,大多數人口集中在農村,但是可以估計在家庭中使用保姆的只占少數而其中準備給保姆永久居住權的恐怕更是少之又少。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在立法中創設一種新的物權,創設一種新的法律制度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雖然如此,法律不能因為只是少數人的利益而怠于保護,當出現了要給予保姆永久居住的權利時候,也應當積極尋求一種兩全其美的方法,既可以保護繼承人的所有權,也能夠很好的解決保姆的居住問題。比如通過在繼承人的所有權上設定一定的負擔就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
由此可見,居住權的功能可以為其他既有的制度所完成而且本身也并不是實現這些功能的最佳制度選擇。盡管居住權制度的社會需求并不大,如若法律能為人們多提供一種財產處理方式也是有意義的,但是我們也不得不考慮因此付出的代價。首先,從立法成本上考慮,自羅馬法以來,居住權便是一種與其他制度相依而生的權利。[19]就我國現有的法律框架而言,既沒有人役、地役的二元劃分習慣,也沒有用益權、使用權、居住權框架體系,居住權難以假借寥寥數個條文就架構一個詳盡完善的規范體系,我國的物權法沒有必要用很大的篇幅詳細規定一項適用空間狹小,人們對之冷漠的制度。其次,“人役權是無償地將所有權的權能分屬于兩方,其流弊在于妨礙標的物的改良,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從社會的利益看,這種狀態不應任其永續。”[20]居住權固有的缺陷顯而易見,有的學者認為出于社會保障和養老育幼的需要不得已而放棄這些實益。[21]但物權法不是社會保障法,更何況這些“需要”在現有的制度規范內可以得到滿足,因而,從社會整體利益考慮,規定居住權無疑成本過大。
物權制度在本質上是最具固有法色彩的制度,各國因國家、民族、歷史傳統的差異,其物權法往往互不相同。[22]因此在居住權問題上,我們應從我國的具體國情出發做出適當的取舍,既不盲目照抄法、德等國的民法典,也不因為日本等國沒有規定而全盤否定。通過對上述問題的分析,筆者傾向于我國的物權法中不規定居住權。
參考文獻:
[①]孫憲忠:《論物權法》,第423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②]周枏:《羅馬法原論》(上冊),第39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
[③]陳朝璧:《羅馬法》(下冊),第369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④]周枏:《羅馬法原論》(上冊),第40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
[⑤]陳朝璧:《羅馬法》(下冊),第362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⑥]屈茂輝:《論人役權的現代意義(上)》,人大民商法律網。
[⑦]孫憲忠:《德國當代物權法》,第25頁,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⑧][德]鮑爾/施蒂爾納著,張雙根譯:《德國物權法》(上冊),第655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⑨]孫憲忠:《德國當代物權法》,第245~246頁,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⑩]鄭玉波:《民法物權》,第181頁,臺北:臺北三民書局,1992年版。
[11]屈茂輝:《論人役權的現代意義(下)》,人大民商法律網。
[12]王澤鑒:《用益物權?占有》,第13~14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3]高富平:《土地使用權和用益物權:我國不動產物權體系研究》,第6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4]尹田:《法國物權法》,第344~345頁,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5]何勤華、李秀清:《外國民商法導論》,第350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6]陳信勇、藍鄧駿:《居住權的源流及其立法的理性思考》,載《法律科學》,2003年第3期。
[17]錢明星:《關于在我國物權法中設置居住權的幾個問題》,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5期
[18]陳信勇、藍鄧駿:《居住權的源流及其立法的理性思考》,載《法律科學》,2003年第3期。
[19][意]桑德羅·斯契巴尼選編,范懷俊譯:《物與物權》,第150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篇(11)
自法典化運動以來,權利是民法無可爭辯的核心概念。沒有這個概念,將會引起很多困難,對此人們的意見是一致的。[①]在以形式理性和體系建構為特征的近現代民法中,民事權利和法律行為成為民法最基本的工具,若缺少其中之一,傳統民法體系便很難建立。事實上,各國民法典無不以權利為線索來進行體系建構,自羅馬法以來的物權和債權二分法在近現代各國的民法典中發揮了中樞作用,這種權利立法結構至今仍牢如磬石。在權利思維模式下,民事法律關系的興變無疑也是以權利的擴展為標志的,如隨著社會的發展,諸如知識產權和人格權等權利的出現,使民法的觸覺進一步深入現實生活,此一現象仍日益激增。在此過程中,關于民事權利的分析和描述成為人們了解和研究新的民法領域的鑰匙。但由于權利是法律的創造物,因此在法律上必須對權利作出詳細的規定,以獲得正當的定證法基礎。其原因在于,“雖然人們存在著實定法之外的權利,亦即這些權利并不取決于人類的規范活動,但是權利的具體內容卻總是由實定法確定的。”[②]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在采傳統潘德克頓式立法模式國家的民法總則中,僅在權利的行使和保護的相關規定中涉及到權利,除此之外,我們很難在民法典總則中找到關于民事權利的一般界定,至于有關權利的形態和權利沖突解決的相關規定更是付之闕如。[③]通行的做法是,民法總則不規定各種具體的民事權利,而是將其放入各編中予以規定(如物權法規定物權關系,債權法規定債權關系等)。這樣的立法編排模式導致大量新型民事權利缺少與民法典連接的紐帶,不得不以單行法的形式游蕩在民法典周圍。單行法與民法典之間、民法和商法之間以及民法典內部的權利制度之間缺少一個整合的空間和過渡地帶,物權和債權的頑固性擋住了其他民事權利進入民法典的路徑。
上述現象使人們產生了疑惑,民法總則為何對權利的規定力盡微薄?民事權利在技術上的整合是否可行,其限度在哪里?關于我國未來民法典的結構,目前學界已有充分的討論。權利體系問題與日前流行的人法與物法的爭論、以及民法和商法合一原則如何體現等重大理論問題密切相關。基于此,作者擬對傳統民法總則和權利體系進行一番審視和檢討,試提出在我國未來民法典中設立財產權總則編的建議,并闡述其理由和基本構想,以供同仁商榷。
一、 權利一般規范在民法典總則編的地位及其解釋
(一)民法總則中權利一般規定的缺失及其后果
民法總則立法模式肇始于德國的撒克遜民法典,是近代潘德克頓法學的產物。[④]總體來說,民法總則是法學家們基于概念法學的需要,為了得到普遍的、基本的原則和規則,利用非常抽象的推理方法得到的結果。相應地,民法典在結構上遵從先一般后特殊的原則,形成了總則、編、章、節的層次結構,從概念法學“提取公因式”這一特點出發,民法總則必然是概念層次結構的最終一環。依據這種邏輯體系,民法總則包含的是被提取和抽象的一般內容,并且體現為可適用于各編的規則。基于德國民法總則的“優越性”,其后許多國家的民事立法借鑒了這一立法模式,如日本、俄羅斯等國家都相繼采納。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民法典草案起草中,也是以德國民法典為藍本進行設計的,所涉及的問題也主要圍繞德國民法典的相關內容而展開。
盡管如此,民法總則設定的價值還是一直為學者所懷疑。[⑤]在此我們不從法律技術和法律適用上去探討,僅從內容上進行剖析。基于法律調整的是現實生活關系,民法總則的統領性也應著眼于法律關系,亦即真正的總則是對法律關系的各項要素進行最大限度的抽象,從而獲得普適效果。只有這樣,當新的民事關系出現以后,通過民法總則就能順利地進入民法典的調整領域。事實上,從德國民法典的總則編進行分析,它大致也是以法律關系為線索設計的,如法律關系的主體、內容、客體和變動等幾個必備要素,在總則中體現為人、物和法律行為制度,只是法律關系中最重要的民事權利制度卻付之闕如,其他各國的民法總則亦然。僅此一條,民法總則的統領性便令人懷疑。除此之外,人法、、物等制度均似民法的具體制度,并非“提取公因式”的產物,很難說有足夠的統領性,只有法律行為制度當之無愧地成為總則的內容,而成為民法總則的核心制度。[⑥]
權利內容的缺失影響了整個民法體系的統一性和完整性,具體而言,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民法各編與總則多有脫節。民法典主要是以權利為線索展開的,在此基礎上形成物法、債法和人身法等。但我們卻無法在總則里找到物權、債權和人身權對應的權利抽象物,總則與各部分之間沒有真切的聯系,使人產生民法總則僅為規定民事權利以外的法律規則這一感覺。
2、新型民事權利和民事關系很難通過總則進入民法典的領域。如知識產權制度、商事財產權制度只能在民法典之外以單行法的形式游弋;同樣,人格權制度的安排之所以爭論激烈,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總則對此沒有留下空間。在此前提下,甚至知識產權法和商法為民法的特別法這一說法都缺少有力的實體法依據。
3、沒有民事權利的抽象,財產關系法和人身關系法在民法典里無法整合。值得注意的是,總則的絕大多數內容并不適用于人格權法、家庭法和繼承法等人身關系法,我們只能從民法總則中嗅到濃厚的財產法的味道。因此,民法總則是否涵蓋了人身關系,值得探討。在體系上欲解決此一問題,必須在財產法和人身法上進行區分。
4、民法典對于財產權定位的缺失,使學界在新型財產權利的理解和設計上,往往陷入新型權利是“物權”抑或“債權”這一思維慣性的泥淖。以物權和債權來衡量新型財產權是民法理論的一貫作法,權利的“性質之爭”一直是中外法典化國家的通病。
上述四個方面的困境足以使我們對民法總則的內容產生困惑。民法是否存在一個真正完整的、邏輯意義上的總則?就目前各國民法典現狀來看,不采總則的占多數,包括修改過的荷蘭民法典和意大利民法典也未采總則模式。有學者認為,民法總則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總則,分則中的許多內容并沒有能在總則中得到體現。反之,總則的內容也不能一以貫之地適用于分則。[⑦]如就人法而言,我們并不能從其中獲得一種適用于所有民事關系的人的形象,傳統民法的人的形象的設計是否完全適用于親屬法、人格權法甚至商法,存有疑問。如德國學者(Diter Medicus)梅迪庫斯認為:“民法典的人法部分僅僅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人們幾乎不可能從這些規定中推斷出一般性的結論。毋寧說,要研究這些規定,還必須考察我國法律制度中其他具有人法內容的領域,特別是《基本法》的基本權利部分、著作權法和商法。”[⑧]就物的規定而言,不難發現,“物”僅是民事法律關系客體的一部分,只是物權的客體,不能充當整個民事關系的客體。事實上,單獨就“物”作為客體進行規定在價值上、技術
上也是值得推敲的,因為在法律上對物的規定與對物的歸屬的界定是同步的,與法律權利和義務相脫離談客體并沒有實際意義,民法總則中有關“物”的規定實際上全然屬于物權法的范疇。至于民法總則的其他部分也或多或少地存在這種情況,這容易使人產生民法總則是融合抽象制度和具體制度的大雜燴這一感覺。另外,民事權利內容的缺失,使民法里常有的民事權利的界限、民事權利沖突的解決這些重要問題就缺少一個基本規則,而在民事權利日益受到限制以及權利沖突日益頻繁的今天,這一點尤為重要。應該認為,在民法總則中“法律行為”制度是最有價值的部分,人們對民法總則的肯定和溢美之辭也主要集中于此。
(二)傳統民法總則權利制度缺失的解釋
對于傳統民法總則的全面評價可能超出了作者的能力。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事關系內容的缺失對總則的統領性構成了根本沖擊,民法總則在結構體系上并不全然是運用“幾何學方法”采取“提取公因式”途徑而得出的產物,其中多為相對獨立的民法制度規范,與其后各編中的具體法律規范之間并無統領和指導的關系。下面我們嘗試找出傳統民法總則結構形成的歷史因素。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當時德國人基于潘德克頓法學方法,對羅馬法進行創制的途徑和目標是建立徹底的、以形式邏輯為基礎的民法典。在此前提下,真正理想的結果是,民法典為運用法律邏輯對生活事實進行完全加工和制作的產物,歷史上基于生活事實而逐步發育的傳統法律體系將被摒棄。相應地,民法總則將成為人的總則、權利總則、行為總則、民事責任總則和人身關系總則的匯聚,民法具體制度則為人法、權利法、行為法、責任法和人身法等,這些內容對于有機的生活關系具有相當的普適意義。但可以發現,立法者并沒有采取這一理想的模式,而僅是對傳統民法體系進行適當的邏輯改造,即在保留物法和債法完整性的前提下,民法總則只是容納了物法和債法以外的其他規范。也就是說,除了法律行為制度外,德國民法上的人法、、物、時效等制度都主要是沿襲了傳統民法,只是以一般性規范的外在形式包容于總則之中。由于物法和債法則被相對完整地保留下來,因此總則并不能直接對其有所指涉。
考察原因,不能忽視歷史傳統因素。首先從德國民法典制訂時的情形看,自古羅馬法至法國民法典,民法所調整的核心內容是一致的,即民法是以民事權利為中心的法律,民法典必須以權利為線索來構建,關于這一點理論上幾乎沒有爭議。基于羅馬法的核心制度表現為相對完整的物權和債權制度,并已成為一個理所當然的制度預設,德國立法者似乎很難拆解這一堅固的規范群體,無法對于物權和債權既定體系進行有效的抽象和改造,也無法在總則中進行規范。也就是說,無論設立總則與否,物權和債權仍是民法典體系的主干,總則是不能對此有所關涉的。因此,民法總則能夠包容的只能是游離在物法和債法之外的人法和行為法等制度了。
以法國民法典為參照進行分析也可獲得有益的結論。回顧德國歷史上有名的法典化大爭論可知,以蒂堡為代表的法學家曾一度想制訂與法國民法典相似的法典,只是薩維尼以立法技術不足為由阻擋了這一進程,薩維尼所說的立法技術其實就是概念體系,他并不完全反對制訂法典,只是認為缺乏嚴密的概念體系,法典不可能建立。因此,他回到古羅馬法,竭力找出適用于所有社會關系的概念體系,后經學者如溫德夏特等的發展,形成了概念法學。在此基礎上,后來的立法參與者開始嘗試以概念工具對古羅馬法和法國民法典予以改造。但顯然,前面述及的徹底的邏輯改造模式也許超出了德國學者的心理承受力,因為他們的概念源自羅馬法,所以自然不能背叛羅馬法的基本體系,不然自已所運用的概念的正當性將受到質疑。因而立法者在技術上適時地采取了第二種策略,即以概念法學為工具,對法國民法典進行了一番體系化和概念化的改造。但同時一個結構性的矛盾開始顯現:依潘德克頓理論體系,最終必然要有一個總則處于金字塔的頂端,以統領民法典其余各編,而依傳統羅馬法體系,物法和債法這一權利體系已經固定,學者對權利的抽象和物權、債權一般規則的創設受到極大限制。最終立法者通過將人法、物、行為、和時效等內容納入民法總則,完成了潘德克頓學派的使命。[⑨]
從理論基礎看,羅馬法固有的人法和物法結構也給德國民法典打上了烙印,這在民法總則規制的“人—物—行為”結構上表現得至為明顯。在羅馬法中,人法和物法是民法的主干,但羅馬人并不是從權利角度去理解財產,而是從物的角度來拓展,這從羅馬人將用益物權和債權都看作無形物這一規定上可見一斑。法國民法典仍沿襲了這一觀念,整個民法典也可描述為“人—財產”這一結構,其中財產仍是從物的角度去定義的,如債權、用益物權和其他財產權仍被定位為“無形物”。可見,物不僅充當了客體,在近代民法上對物的界定也一直充當著“權利界定”的角色。[⑩]德國民法典也不例外,盡管在理論上意識到民事權利與物是不同的概念,在總則第90條對物的界定中,將“物”限定為“有體物”,意識到了權利與物的區別,但羅馬法“人—物”結構仍未有突破,只不過在此基礎上創設了行為制度,而將法律關系意義上的權利和財產一定程度上仍置之度外。
綜上所述,民法總則中權利制度的缺失是具有其歷史原因的。自羅馬法以來關于財產的“物化思維模式”已根深蒂固,猶如頑固的堡壘,即使潘德克頓學說也無法拆解。與此相對應,物與財產的血緣聯系阻礙了無形財產的擴展,限制了民法科學權利體系的建立,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生動、靈活的以行為為紐帶的生活關系世界。
二、設置民法財產權總則的基本理由
權利制度的缺失對我國目前民法典的體系設計提出了挑戰。但可否在立法技術上對所有民事權利作一有價值的抽象,將之歸于總則,以達到體系的統一?答案是否定的。民事權利本來就是法律關系類型化的產物,種類繁復,相互之間形態迥異(如物權、債權、人格權、身份權、無形財產權等),很難找到相通點。也就是說,權利本來就是關系概念,是法律關系的本體和實質,對權利的描述無異于揭示整個市民成員的生活。如基于權利形態的不同,民法自羅馬法以來發育出了涇渭分明的物法和債法;基于授予權利的社會關系基礎的不同,民法又形成了世人公認的財產法和人身法的分野;基于財產權配置和交易的市場化程度的不同,民法又形成了普通民法和作為特別民法的商法的格局。上述權利關系復雜的程度與民事關系的復雜程度是一致的,在民法總則中任何欲對權利進行本質的抽象無異于僅給民事權利下一定義,操作上的困難和抽象結果的價值不言自明。在這一問題上,總則和權利法律關系出現了兩難:如果制定一些非常一般的規則,那么一般規則的普適性必然受到限制,總則對具體關系的指導作用就很難實現,反之,如果對相對具體的關系進行次一級的較高程度的抽象,那么總則又會有許多例外。人們也許從權利一般制度的困境中,可以最好地理解民法總則是否真正能夠勝任統領民法的任務。[11]
這樣一來,《德國民法典》總則中民事權利制度的缺失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在立法上欲通過一般權利規范的界定來統領所有民事關系并不是理想選擇。但這并不意味著,對于權利關系的整合是不必要的,如果置當代民事權利的擴展于不顧,民法典不僅自身無法完整調整各類民事關系,而且是否可以統領特別法也令人懷疑。應當明確的是,在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間,并非只是兩者選其一,非此即彼,在法典萬能主義和幾何學公式式的方法被打破以后,民事權利的適度整合是民法典在當代的發展要求,這種適度整合是法
律碎裂化和法典功能保持兩者之間的緩沖地帶。關于適度整合對于未來民法典的重大意義在此不談,但對于法典中的權利關系問題,我們認為,設立財產權總則是適度整合的可行方案,對于民法典的體系化和發揮民法典制度的最大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下面擬從兩個方面提示財產權總則設立的必要性。
我們所稱的財產權總則主要是基于下列參照系,而構成財產權總則設計的基本理由。
(一)財產關系與人身關系的結構性分野
目前,關于民法的調整對象為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這一結論已為世界性的學術通說。但是迄今為止,在民法典結構上,卻很少看出這種區分的份量。物權制度和債權制度成為民法象征性的核心內容,而人身法卻大多蜷縮在民法典的最后部分或人法的云隙之間,甚至有時立法上將家庭法和親屬法的相關部分單行立法,不納入民法典。即便如此,這種分離的立法模式并沒能使人懷疑民法典的完整性。但是學者卻不能想象,如果現代民法缺乏法人制度、物權制度或者債的制度,民法典將會出現何種狀況。這似乎揭示出,自德國民法典以來,傳統民法的人法、物法和債法,具有內生的同質性,是在同一語境下對同一類社會現象的概括,從而形成一套穩固的、以邏輯為紐帶的規范群。[12]顯然,這種規范群體現的是一種財產邏輯關系,而非人身邏輯關系。可以認為,構成民法主體結構的概念體系,在近代實際上是以財產法為核心建立起來的,相反,概念法學所創立的概念系統對人身關系并沒有引起相同的重視。然而在學說上,學者卻大多傾向于將財產法的一套概念體系同樣用來套用于人身關系,以致顯得疑慮重重。簡言之,在社會關系多層化、復雜化的今天,能夠構成“民法”這一詞的特殊內涵仍是以財產法規則系統為標志的,如果缺少財產法上的人、行為和權利這一套話語系統,當代民法便會被徹底解構。
值得注意的是,對羅馬法的直接繼承和借鑒,之中貫徹了近代市民社會所要求的人格平等、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則,但在人身關系上則仍保留了大量的封建主義的等級性人格制度和家庭制度。直到上個世紀二戰以后,隨著世界人權運動的興起,各國才逐步進行了人身法的改革。由此可見,民法上的人格一律平等原則實際上是對財產關系主體的抽象,這在各國民法典中是一致的,而在人身關系主體地位的規定上卻存在著相當多的差異,這是因為人身關系與一個民族的道德觀念、民族習慣、文化傳統密切相關,它不是單純由經濟因素決定的。所以在德國民法典中,幾乎完全脫離了家庭法而設計民法總則,家庭法只得退居到一種獨立地位。應該說,財產權與人身權的人格基礎、權利形態和調整手段具有質的區別。基于此,財產權和人身權應是民事權利系統最基本的分類,對于財產法和人身法在體系上應有一個明確的區分,并在民法典上直接體現出來。但實際上,立法者可能基于人人平等這一原則,忽視了此兩部分的人格基礎和運行邏輯互為不同這一事實,所以沒有加以深究。另外,由于民法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家庭法一是民法的基本組成部分,所以在設計近代民法結構體系時,各國民法典并沒有刻意將其與財產法嚴格分開。
從權利體系而言,財產權和人身權成為民法權利系統的基本界限。梅迪庫斯認為,親屬法和繼承法規定了相互之間具有聯系的、類似的生活事實。而物法和債法規則體系則不是基于生活事實的相似性,而是法律后果層面上的相似性。[13]換句話說,人身法的社會倫理性與財產法的形式理性之間是有嚴格界限的。在此前提下,財產權與人身權具有諸多本質差異:就權利形態而言,財產權表現為是一種行為模式和外在資源的分配方式,而人身權主要表現為一種人身利益的認定,這種認定不是以物質載體為基礎的;財產權對所有主體是同等的,而人身權則主要因人而異;財產權可以轉讓,而人身權具有專屬性。近代以來的民法其實圍繞財產關系已形成了一套獨立的主體、權利和責任體系,這種體系的各項制度是同質的,并在整體上與人身法相區別。所以,在設計民法典體系時,應首先正視這一事實,在體系設計上應有嶄新的思路。
(二)民商合一的體現:財產法體系的整合
近代以來,民法和商法關系之微妙,難以言說。雖然在理論和立法上有兩種主張,即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但兩者均缺乏實質意義上的說服力。就民商合一而言,倡導者雖然能列舉出數條切當理由,但無法提出有效的途徑使商法和民法在規則上相通,在立法上商法事實上并不完全顧及民法原理和制度而自行運作。比如,證券和票據的規則在民法制度上就無從歸宿;又比如,關于股權的性質,在民法上也是無法推斷。如果說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那么即使在具體規則上無法體現,至少在總則中也應為其留下一定發展空間。在此情形下,民商合一只能成為一種理論和名義上的解說。就民商分立而言,倡導者也很難抽象出商法獨立于民法的基本理論體系。雖然各國商法學者不乏努力草擬商法總則者,但都收效甚微。細言之,一則是由于商法本身是由相互不大關聯的、獨立的法律所構成,本來就不易從規則上找出共同的總則;二則是由于商人和商行為的本質界定,似乎又是建立在民法中人格假定和法律行為假定之上。至于其他如商業登記和商業帳簿的規定,似乎又是操作規程,不構成總則的本質內容。因此,民商分立之說也是一個理論和名義上的解說。
我們認為,民法和商法的稱謂從規則而言,也不外是調整現實生活中各類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以形式理性為基本特征的法典立法上,兩者的合一或分立,均離不開法律的規則基礎。不可否認,民法和商法的起源和功能有很大不同。然而在現當代社會,在財產占有和運行這一領域內,兩者日趨統一。但在規則上如何使民法和商法融為一體,對大陸法系國家而言,仍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在倡導法典全面性的近現代法國、德國和日本,在民法典之外,仍就保持著商法典這一事實就是例證。[14]
因此,欲真正實現民法對商法的統領和有效的規制,以實現立法的體系化,在規則上必須進行適當的整合。在保留傳統民法概念體系的前提下,對于商事財產關系與民法財產關系在同一層次上進行定位是必要的。關于為何民法財產法概念體系在技術上很難適用于商法,在此試作如下分析。
自羅馬法以降,傳統大陸法系的財產觀點是建立在樸素的財產觀基礎上的。民法的具體財產制度均是以“物”為基點展開的,物與財產占有及流通密不可分。至今,在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民法典中,“物”這一概念是規范財產關系的基礎,脫離物來討論財產是不可想象的。在此基礎上,早期基于物的占有形成“物權”,基于物的流通形成“債權”,已成為大陸法系源遠流長的思維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僅作為一類權利客體的“物”在民法典中始終具有很高的地位的原因。這種情形一定程度上也與羅馬法以來民法所具有的市民社會的品性密切相關。自羅馬法至法、德民法典,民法始終以有形物的占有秩序的規定為其主要內容,這不僅是因為物權和債權制度原本就是欠發達的商品經濟中物的占有和交換的反映,而且還因為物權和債權在市民社會中,不僅體現為一種純粹的財產權,更體現為一種國家治理秩序。[15]近代市民社會法律所對抗的是政府權力這一事實,決定了近代民法只能從最基本的關系入手,確立市民社會中人的最基本權利,這些權利成為社會成員對抗權力的屏障,也成為民法的語言。在此前提下,以物權為代表的財產權與生命、自由一起成為基本人權。但商法的規則卻有另一番語境。西方近代商法只是特殊商人群體的金錢游戲規則,它并不肩負社會變革的使命,也不以確立社會成員的基本人權為已任,這種規則在西歐封
建體制內即已存在。商法一定程度上的價值中立性,導致了整個商法體系并不以權利為語言,也不以概念體系為特征,而僅表現為一系列嚴謹的、務實的操作規范。所以,在傳統民法的權利體系內,商法的財產流通形態大多表現為無形財產的特征,很難用以“物”為基點的民法權利語言進行解說。
因此,自羅馬法以來的民事權利是以最貼近市民生活的財產關系為基礎的,是以民法最基礎的“物”的概念決定的財產權利系統作為社會關系的最基本層次。而商法制度所確立的財產觀則是開放的,多層次的,在商業中,沒有物的介入,僅通過無形的票據、營業權和股權的流轉就能獲得大量金錢財富,這在現當代已成為經濟的常態。所以,我們認為,當代民法和商法的矛盾主要在于民法的財產制度基點過于狹窄,不能涵蓋商事財產形態,事實上導致了民法和商法在規則上很難融合。由于民法的傳統規范體系很難擴展,欲實現民商合一,就須在民法典的設計上通過財產權總則將其財產形態拓展至商事財產,這也是未來民法典整合社會關系和完善立法技術的必要步驟。事實上,在現代社會中,民法和商法的功能趨于同一,近代民法的功能由早期對市民社會基本制度和基本人權的著重宣示,已逐漸蛻變為對高度發達市場經濟中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實際調整,民法典的工具性逐漸增強。而商法這一特殊群體的游戲規則也已全面滲透至社會的每個角落,社會經濟結構在高度發達的市場條件下必將得到統一,因而市場經濟民法和商法財產關系應在同一層面上進行規制。
除了上述參照系以外,設立財產權總則的構想還與現代大陸法系國家立法分散化趨勢相關。當代大陸法系各國基于無形財產的大量出現,在立法上均傾向于對無形財產進行具體立法,而放棄了將之納入民法典的努力。以此為契機,民事立法由普適性向具體性、由系統性向分散性發展成為立法潮流,傳統意義上以概念建構為特征的民法典失去了往日的份量,近代德國民法典所構建的富于美感的概念體系和所蘊含的企圖一統天下的樂觀主義,受復雜的現實生活關系的沖擊而支離破碎。從而,民法典成為維系傳統法律關系和整合新型法律關系的立法工具,民法典的傳統價值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由于傳統民法的概念的基點過于狹窄,包容性非常有限,導致民法總則的統領性先天不足,如果立法上還堅持采取法典化立法模式,那么對于特定領域的法律關系進行整合,強化中間層次的立法系統化,應成為民法法典化的重要任務。
以上的分析一定程度上說明,財產權總則在財產法和人身法、民法和商法、法典化和立法分散化之間,可以起到一個邏輯上的分離和整合作用,作為一個中介性的立法層次,它將有效地緩解原有概念法學體系結構的邏輯困境,也基本上可以消彌財產關系在形態上的分散和對立狀態。尤其在新型無形財產(如知識產權、網絡虛擬財產等)日顯重要,以及在諸如人格權等民法權利對民法結構提出更高要求的情況下,這一整合的意義更為顯著。
三、財產權總則設計的基本思路
(一)財產權總則與民法總則
財產權總則這一立法模式并非作者的創見,在立法上已有現成資料可資佐證,如新近的荷蘭民法典和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民法典就設立了財產權總則。由于兩者均未設計民法總則編,因此財產權總則和民法總則的關系是必須得面對的問題。上文關于民法總則的缺陷已進行了一定的分析,民法總則的必要性已引起了我國一些學者的懷疑。[16] 在沒有采取民法總則立法模式的國家,德國民法典中總則的有關內容在這些國家法典中分散為具體部分的規定,而并沒有引起太大的邏輯上的矛盾,這是因為現有民法總則的大多數內容原本就沒有普適性和統領性,總則只是具體制度與一般制度的混合。但總則設計是否在當代就完全失去了其立法價值?這也是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解決這一問題必須要明確現代民法總則意義和功能的轉變。傳統民法總則在價值理性層面的意義逐漸坍塌,而逐漸演變為一種立法工具意義上的民法總則。上文所述的民法總則均是在概念法學的意義上使用的,是傳統概念體系結構的頂端,它承載著深厚的法哲學和方法論的價值觀,學者對于民法總則的批判也是從此角度進行的,懷疑民法總則實際上也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概念法學的否認。我們認為,既然立法上仍采法典化的立法模式,民法典的形式和結構就應予以關注,在立法形式和結構上,民法總則對于民法典仍不失其積極的意義。應當明確的是,由于民法總則對于最基本的法律關系的內容的規定(主要為權利)的缺失,民法總則的若干基本概念很難適用于無形財產,加之民法總則的統領性因立法分散化趨勢而受到很大限制,從而決定了當代民法總則已不再是潘德克頓法學意義的民法總則,也不是是所謂幾何學公式的最后一環,而只是作為立法系統化和法律關系適度整合的工具存在。也就是說,民法總則在工具層面上仍有一定的意義,應予保留。從立法技術而言,保留總則的主要理由有:
第一,原有民法總則的確包含有一些帶有普適意義的一般規定。如法律行為制度如果不通過總則來進行單獨規定,那么在專門的篇章結構中便無規定的余地,也許法律行為制度是總則存在的最有力的理由。當然其他制度如時效制度、權利行使和權利保護制度、期間、期日等制度也都是一般性的規定,通過民法總則也可以減少立法的繁復。
第二,民法總則從立法系統化角度可以起到整合民事關系的作用。民事關系雖然其性質大體可以界定,但自羅馬法以來,民事關系就顯示出了超越原有體制的特點,法律關系總是無窮膨脹的。[17]民法總則可以通過基本原則(如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序良俗原則等)的規定為普通法和特別法起到一個統率的作用,在此基礎上也可以提供一個法律適用和法律解釋的基點,為司法裁判正當化提供法律標準。
從上述理由可看出,現代民法總則主要是整合民事法律關系的立法技術,尤其總則中規定的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序良俗原則,已成為現代法律漏洞補充的工具,這直接是對傳統民法形式理性的背離。但財產權總則是否放入民法總則中規定,亦即民法總則在規定傳統內容時,是否還應規定財產權總則、人身權總則?
闡述這一問題必須首先在理論上區分民法總則和財產權總則的功能。現代民法總則作為民法的整合工具,體現為對存在于民法各領域內的相關制度進行規定,這決定了民法總則的立法維度是以民事關系要素和民法適用這些具有一定普遍意義的制度規定為特征的,亦即它不可能涉及某一特定類型的法律關系的規定,否則就會影響總則與分則的基本邏輯關系,同時也會影響民法總則這一整合工具的價值。在法典內部,民法總則與分則是上位與下位的關系,對法典外的法律漏洞而言,則是通過基本原則在適用上予以開放。而財產權總則的立法維度有所不同,它不是從法律關系要素和法律適用角度展開的,而是體現為某一類具體法律關系的規定。財產權總則也是法典化中的整合工具,但這種整合是對法律關系內容的整合,是傳統財產關系及財產權利分散化的克服,是擴大民法典財產關系適用范圍的手段,因而它針對的是權利制度,屬于具體制度的立法領域,財產權總則只對財產性的民事權利具有統領性,而不能成為民法的普遍制度。再則,傳統民法總則本來就沒有設立權利的一般規定,現代民法總則也無既有模式可以遵循,因而在民法總則之外,進行次一級的若干具體制度的整合也就成為較為合理的方法。如果民法總則確定的是一般性規范,傳統民法制度如物法、債法等規定的是具體民法規范,那么在一般規定和具體制度之間,設立中間層次的財產權總則可以有效地實現一般性和多樣性的整合。現代社會中的一些財產形式(如無形財產
等)常常在傳統民法上沒有予以規定,既因過于具體而無法在總則中找到法律依據,又因物法和債權等適用范圍過于明確而無法納入民法典中的具體制度,而在民法總則和具體制度之間設立財產權總則,既彌補了總則權利規范的缺失,又發揮了整合財產關系、擴大民法典適用范圍和統領作用的功能。
至于對于人身關系,是否可以比照財產權總則而設立人身權總則,作者持否定意見。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不同,財產關系之所以能夠一定程度上被整合,是與財產主體可以在“交易人”這一假設下統一起來相關的。在財產主體被同等對待的情形下,財產權總則可以集中對財產權利形態從行為模式上進行界定和分類,從而建立較為體系化的財產權利制度,并具有一般適用意義。而人身關系的整合則不僅涉及到人身權,更與人身關系主體的地位密不可分。人身法是以人的角色具體化為基礎的,在許多人身關系中(如身份權),人身權是由人身主體決定的,立法上不能脫離人身而獨立地建立人身權制度,這就決定了人身權總則不屬于權利制度的整合范疇,人身權總則無異于逐個描述具體人格權關系和身份權關系,無法提取適用人身權的一般規范。事實上,傳統各國民法典幾乎也放棄了在民法總則中對于人身關系進行一般規定的企圖,人身法都是自成一體,相互獨立的。因此,既然傳統民法理論對表現為生活事實的人身關系在形式上都不能有所抽象,現代社會想建立人身權總則制度的想法必然也是徒勞的。
因此,民法總則和財產權總則在當代都只能是立法技術化的表現形式,財產權總則的設定是對民法總則法律整合性功能有所欠缺的一個補充,是解決當代法律分散化與法典化矛盾的產物。
(二)財產權總則的內容與立法模式
財產權總則的內容與設計也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財產權總則針對的是平等主體財產關系的一般內容,對財產權各編起著一個一般規定的作用。是否可以抽象出一套適用于所有財產關系的規則呢?當代各國立法早就放棄了建立財產權理想模型的努力,如法典化國家在民法典之外大量存在的特別法便是印證。[18] 實際上,財產法根本無法抽象出一個統一的概念、特征和效力等的理論體系。“當代(財產)權利束互不聯系,沒有共同語言,原來起源于物品所有權概念的法律上的‘財產權’的含義,在法學和經濟學的一般理論中并沒有獲得統一的概念。”[19]也就是說,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矛盾在財產權總則上無法真正彌合。
在此基礎上,一個明顯的結論是,欲通過原有民法典財產概念的適當擴展去統領民法財產權、商法財產權和其他無形財產權的努力是徒勞的。民法上的財產是從“物”的角度來理解和拓展的,帶有深刻的農業社會財產觀的殘余,至今仍決定著民法典的財產體系。而知識產權和商事財產權則直接是從利益的享有和權利的構建角度理解財產關系的,所以在對財產的界定的概念基點上,民法、商法和知識產權法的底蘊大相徑庭。由此,財產權總則不可能采取抽象的方式來規定財產及財產權的一般概念及其特征,而只能通過列舉的方式來進行規定。
目前在國內理論界存有以“財產法”取代“物權法”主張。[20]該主張正確地注意到了傳統民法上“物”和“權利” 不分,以“物”代替“財產”這些民法典所固有的頑疾,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但在立法上如果企圖通過物權法來實現對所有財產關系的調整,顯然會破壞民法典原有的物權和債法體系結構。由于由“物”、“物權”和“債權”等基本概念所構架的民法規范已經形成了穩固的立法模式,所以任何概念上的拓展都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很難有所突破。在理論上必須承認,物法只是調整“物權”的法律、債法只是調整“債權”的法律,基于財產權的特殊性,想在這二者之間通過擴展概念或改變規則以調整無形財產,缺乏技術上和規則上的可能性。由于法律關系的膨脹,單行立法的發展,民商事關系和知識產權法已經形成了分散化的格局,民法典的制定仍是對傳統民法固有概念相關聯的規范進行整理,故應保留傳統民法原有的概念體系,在封閉的規范群里不應過多強調概念的創新。遵循此一思路,這里財產權總則的設定也非概念法學意義上的財產權總則,而是在完整保留物權和債權規范前提下,為知識產權、商事財產權等在財產權總則里留下存在和發展的空間,以起到法典化的整合效果。至于知識產權、商事財產權和其他無形財產,除總則予以一般規定外,仍應由知識產權法、商法和其他單行法來專門規定。這樣,財產權總則既一如既往地統領了傳統民法領域的物法和債法,同時也統領了游離在法典之外的知識產權法、商法和民事單行法的相關規范,物法、債法和單行法的地位一樣,都是對某一類財產權的專門規定。
但為何只有物法和債法能完整地保存于民法典中,而其他形式的財產則需單行立法規定?從民法歷史淵源來看,傳統民法理論和制度經過二千多年的發展,在概念上已形成了一套穩定的體系,這構成了我們當代稱之為“民法”的核心內容。羅馬法建立的一套農業社會的財產權制度帶有深厚的“財產物化思維”的烙印,而對于奉羅馬法為圭臬的近代大陸法系國家,物權和債權作為理解全部財產關系的制度體系被完整繼承下來,從而忽視了近代商事財產和無形財產所表現的其他權利形式的規范特質,法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路徑信賴”現象在此起了巨大的作用。如果當代立法者欲制定一個完全包容性的民法典,其必然的結果是,所有財產關系(包括知識產權、商事權利和其他無形財產權等)都被納入民法典,進行專章規定,從而傳統物法和債法只能作為其中一個部分,而傳統民法從物法和債法提取的概念和原則僅適用于物法和債法,不一定能適用于其他財產權,這樣構成法典有機體的傳統概念體系因不能適用于新型財產權,將面臨全面解體的危險。
(三)財產權總則的具體設計
對于財產權總則在法典中的位置及主要內容,可做如下設計:
第一編 總則
第二編 財產與財產權(財產權總則)
第一章 財產及其分類
第二章 財產權及其保護與限制
第三章 物權一般規則(效力與變動)
第四章 債權一般規則(效力與分類)
第五章 物權、債權相互之轉化
第六章 知識產權一般規則
第七章 其他財產權
第三編 物權
第四編 合同(上編:合同總則;下編:合同分則)
第五編 人格權
第六編 親屬
第七編 繼承
第八編 侵權行為
第九編 民法的適用
從上述關于民法典總的結構編排形式中,可以看出財產權總則在民法典當中的地位。財產權總則在此起到一個財產法律關系的整合作用,在保留傳統民法總則形式及主要內容的基礎上,所謂財產權總則其實處于與民法總則相對應的“分則”地位。通過列舉方式,財產權總則對物權、債權、知識產權和其他財產權的一般規則進行了規定,這種法典上的宣示擴大了民法典的適用范圍,為民商合一建立了一個規則上的依據。同時,通過對財產關系及財產權類型的列舉,也在法律上確立了知識產權和其他財產權與物權、債權相互獨立的地位,在學理和法律適用上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困擾學者和實務工作者關于權利的“物權性”或“債權性”的無結果的爭論。
在技術上,關于“財產及其分類”是財產權總則的重要內容。在這一部分里,應對財產關系及財產進行有效的界定。財產法所調整的市民社會的財產關系有其特殊的內涵,它與人身關系相區分而在民法中使用。但如果僅僅以是否含有財產因素來確定財產關系,導致的必然后果就是,涉及到財產的就是財產關系。實際上,涉及到財產的民事關系不一定可以納入到財產權總則,如人身權利受侵害時,受害人的賠償請求權雖表現為一種財產性,但由于其權利基礎是人身權,
所以在立法上不應將之列入財產關系,而應屬于人身權法調整。盡管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很大程度上在財產手段上取得了統一,但我們認為,法律對各種民事關系的處理結果雖然有相似之處,但法律對其采取的態度和邏輯基礎是完全不同的,它們之間在性質上仍然具有本質的區別,所以在基礎法律關系上進行權利的區分是成文立法邏輯的體現,仍然具有重要意義。[21]
我們將財產界定設計為三個層次:
首先,在財產的界定中,除將傳統民法總則中“物”的基本制度納入其中外,物權和債權是二項最基本財產形式。但在對“物”的界定上,應將“物”限于“有體物”,有體物包含了物理形態上的電、熱、聲、光等,而任何“權利”都不能歸于“物”,不然在邏輯上就無法區分權利與權利客體。現有的民法理論認為,在權利質押和債權轉讓過程中,權利與動產質押和動產轉讓關系中的“動產”處于同一客體地位,這實際上忽視了動產質押和動產轉讓關系中,真正讓渡的不是所謂的“動產”本身,而是“動產的所有權”,也就是說,物本身的轉移過程遮蔽了權利的流通實質。
其次,財產權總則對財產的界定中,還應列舉規定無形財產。對于知識產權應專節規定,因為知識產權在權利體系中獨樹一幟,且在規則上已形成了完整的體系。在“其他財產權”一節中,對于其他無形財產也應有所反映(如脫離物的流通形式的票據、證券、信托財產權等基本形式),并對調整各種財產形式的法律在民法典上予以確認,這樣可以初步消彌民法和商法不能相互統一的缺憾。
再次,在對財產的界定中,還應規定以財產為紐帶的典型的成員權。所謂成員權,是在團體共同占有財產情況下,財產不適于個人所有時,成員只能通過成員權的行使以獲得經濟利益的保障。傳統民法中的所有權理論是建立在個人完全占有有體物這一前提下的,缺乏成員權這一權利形式存在和發展的理論基礎。實際上,諸如股東權、合作成員的社員權、集體組織成員的權利和建筑物區分所有者的共同權利,都表現為一種成員權,并不能完全通過所有權來解釋。細言之,財產所有權是極端個人主義和財產分裂的產物,所有權概念和理論體系無法真正解釋具有垂直結構的財產團體占有關系,所有權與成員權的語境并不相同,因而所有權與成員權是此消彼長的關系。也就是說,財產聚合導致所有權的形態的微弱,而代之以成員權的增強,反之亦然。通過成員權的界定,民法的調整手段可以延伸至團體財產的權利規制上,并且可以使民法與公司法、建筑物區分所有權法、合作社法及集體經濟組織相關法律有機地銜接起來。
基于此,財產權總則在保留物權法和債權法一般規則之外,又規定知識產權和其他無形財產的一般規則,充分體現了財產權制度的統一性。在一般性和多樣性、傳統結構的維持與制度創新、民法典和特別法之間,財產權總則提供了一個平衡點,實現了對財產關系的適度整合作用。
Abstract: The article makes a demonstration of structural flaws about tradtional civil law , from the absence of general regulations of civil rights in tradional civil law code. And it presents a proposition of setting up general rules of property rights in the future civil law code to intergrate the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ivil law code based on rights, the general rules of civil law took no action in setting apart property rights from personal rights, and it lacks the scientific legislative regulation on property rights . Confronting the rapid rising of intangible property , the general rules of property rights can rearrange the property rights effectively and seek a reasonable balance between the command of civil code and specialization of legislation.
Key words: general rule property right personal relation specialization
注釋
[①] 見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頁。
[②] 引自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
[③] 在此需說明的是,在采取民法總則的國家,在總則對諸如權利的行使、保護等都有了一定的規定,但對權利本身都缺少根本的界定。在此我們主要是在這一層意思上來闡述的。
[④] 在民法里設置總則編,最早出現于德國的學術著作。德國學者格奧爾格。阿諾爾德。海澤(Georg Arnold Heise)在其1807年出版的《用以講授學說匯纂課程的普通民法體系大綱》一書中,設立了總則章節。但在法典中正式設置,應自撒克遜民法開始。所以,自普芬道夫、沃爾夫等自然法學家至薩維尼以來,民法一直朝著概念化和體系化的方向發展,在此基礎上,民法總則的產生有其必然性。
[⑤] 如拉侖茨認為,將“總則”抽象出來的做法是否合乎法典的目的,是值得懷疑的。《德國民法典》雖然因此省去了許多重復性或援引性的規定,但在其他地方卻多出了不少限制性和細分性的規定,法律適用并未因此而容易多少。參見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頁。梅迪庫斯也持此種觀點。參見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頁。
[⑥] 梅迪庫斯認為,設立總則編的優點,主要反映在有關法律行為的規定方面。見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頁。
[⑦] 日本學者北川善太郎從技術上對傳統民法總則進行了分析,認為民法總則并未起到民法典規范體系的融合作用,在多樣性與統一性的關系上,民法總則并沒有很好地充當協調和整合的作用。在此基礎上,他提出民法總則欲成為真正的總則,必須對于分則的一般規定抽取出來,列入總則,形成民法真正的總則,亦稱“多樣性的整合”,未來的民法典必然是技術上非常精致和傾向實用的民法典。(參見中日民法典云南麗江學術會議2003年3月28號的會議記錄)
[⑧] 引自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78頁。當然,民法上的人是一個很難界定和描繪的形象,作者認為,民法上的人界定的是一個日常生活的市民形象,既缺乏對家庭關系中的倫理個人的規定,也缺乏真正商人的塑造。
[⑨] 實際上,潘德克頓學說也注意到了對權利的抽象。如溫德夏特在《潘德克頓教科書》里在關于“權利的一般”這一部分是作為總則部分進行論述的。在該教科書里,權利的一般理論包括:權利的概念和種類;權利的主體;權利的產生、消滅和改定(法律行為在此一部分);權利的行使、侵犯和保護。參見indscheid,Dirtto delle pandette (Vol. I), trad. it. Di Carlo Fadda e Paolo Emilio Bensa, UTET, Torino,1925,p.41.可見,理論上該學派也承認總則應將權利作為核心內容,但在立法上卻付之闕如,這說明了傳統羅馬法體系對德國民法典的制約作用。
[⑩] 關于物和權利、財產的關系及引注,可參見馬俊駒、梅夏英:《財產權制度的歷史評析及現實思考》,載《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無形財產的理論和立法問題》,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本文不再贅述。
[11] 民法總則的許多內容莫不如是。如民法的人法似乎更多地適用于財產法,而不太適用于人身法;民事法律行為在人身法中,也表現出諸多例外,我國學者董安生教授認為,民事法律行為有其適用范圍,是否適用于人身法是值得思考的。人身法主要表現為一種法定主義,與行為制度屬于不同的調整方式。可參見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頁以下。其他關于總則結構上的矛盾在此無法一一列舉。
[12] 這一提法是借鑒美國學者艾倫。沃森的相關論述。參見艾倫。沃森:《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李靜冰、姚新華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頁以下。
[13]參見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頁至第21頁。
[14] 目前民商合一日益成為一普遍的立法趨勢,一些原采取民商分立國家也采取了民商合一的法典結構體系。如意大利曾于1865年制定民法典,1822年制定商法典,1942年的民法典則將民法和商法統一;荷蘭原采民商分立主義,自1947年重新編纂民法典以來,商法的內容被分別規定在民法典的各編當中。但是可以發現,民商合一更多地體現為一種純粹結構上的融合,商法部分與傳統民法部分并沒有實質的聯系,在法律適用上與單行立法幾乎沒有兩樣。另外,上述國家民法典中也只有限地容納了部分商法的內容,有些內容仍無法容納。
[15] 如羅馬法早期對物權的規定并不是基于一種權利,而是從自然秩序角度去定義的,物權的分配和界定與市民社會秩序緊密相關。對于近代法國和德國而言,雖然商事活動和商事規則已經形成,但民法卻肩負著實現從封建社會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轉變這一歷史使命,因而近代市民社會的基本秩序和基本權利的建立自然脫離不了對羅馬法物權制度的借鑒。
[16] 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65頁。
[17] 蘇永欽認為,民法的法典化自羅馬帝國的《國法大全》開始,就顯示出了驚人的超越體制的特質。民法的發展印證了韋伯的形式理性學說。只有當民法和體制的其他部分不只是和平共存,而是相互包容,乃至出“社”入“資”,或出“資”入“社”,才可見其形式理性的精髓。參見蘇永欽:《私法自治中的國家強制:從功能法的角度看待民事規范的類型與立法司法方向》,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1期。
[18]臺灣地區民事立法也基本上放棄了盡收所有民事規范于“一法”的想法,通過臺灣地區“民法”第1條關于法源的規定,立法上可針對特定政策目的制定特別民法或特別民事規定,不改變法典內在價值的一致性,而與其共同組成廣義的民法。參見蘇永欽:《私法自治中的國家強制:從功能法的角度看待民事規范的類型與立法司法方向》,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