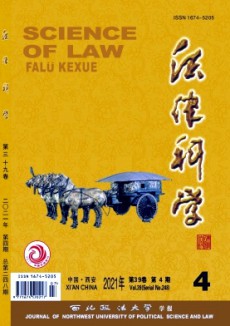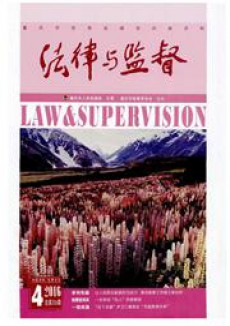法律推理的原則大全11篇
時間:2023-07-14 16:34:10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法律推理的原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道德權利就是作為道德主體的人依據道德所應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對待。道德主體有權作為或不作為,作何種行為,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種行為,必要時借助于一定的道德評價形式(如社會輿論)協助實行一定的道德權益。法定權利是指按照法律規定而享有的包括民事、行政、訴訟等方面的權利。具體而言,就是由憲法和法律明文規定的公民享有的權利,分為實體權利和程序權利。道德權利在被法律明文規定之前,原則上是不具有強制效力的,并且不受法律保護。
二、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沖突的原因
(一)道德具有時代性、地域性。“不同的人可以在同樣的位置看到同樣的結果,同一個人可以在不同的位置看到不同的結果。”這種位置客觀性造成道德的時代性、地域性。例如在我國古代,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被認為是不道德,甚至是違法的。如今的維吾爾族,尚保有近親結婚的習俗,表兄妹之間結婚是不受限制的。顯然,這是與我國當代法律相違背的。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禁止破壞婚姻自由”,現行《婚姻法》第二條規定“實行婚姻自由”,第七條、第十條明確禁止近親結婚,規定其組建的婚姻無效。立法規定的婚姻自由與古代婚姻道德相悖,禁止近親結婚與少數民族“親上加親”的民俗存在差異。
(二)我國法律的不確定性。其一,不同位階與同一層次的法律對權利的配置存在沖突。如在精神損害賠償權利方面,公法和私法的保護力度不同。新《國家賠償法》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在賠償范圍上較為狹窄。相比較而言,我國民法中的精神損害賠償范圍較為廣泛。其次,法律規定比較宏觀、模糊,只是對權利的確認和基本原則的概括。法律要求穩定性,不可能列舉盡所有具體情況下的權利,而法律規定的模糊又易導致司法擅斷,造成同案異判等違背公平正義的結果。
三、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沖突的解決方案
(一)法律與道德推理基礎上的綜合實踐推理
法律推理,是指以法律與事實兩個已知的判斷為前提,運用科學的方法和規則,為法律適用提供正當理由的一種邏輯思維活動。道德推理是以道德現象為研究起點,在現有的道德知識引導下,從“實然”衍生出“應然”的確證過程。法律推理在法律適用活動中,解決法定權利的沖突;道德推理解決道德領域的沖突。在同一案件中,法律推理和道德推理可能會給出不同的解答。
1.由道德向法律推理。只有在獲得法律承認時,道德權利才能具有法律相關性。在具體個案中,從被法律所承認的道德權利開始推理,研究有法律依據的道德推理與法律推理的重要性。如在我國《憲法》第49條中,規定“婚姻、家庭受國家的保護,禁止破壞婚姻自由”,這里承認的就是配偶要求彼此忠誠的道德權利。“包二奶”的行為違背了道德權利,其不具有被法律承認的夫妻關系,故也不具有結婚自由的法定權利。有配偶者與他人結婚的行為是作為犯罪而受法律制裁的,這里的道德推理就重要于法律推理。
2.由法律向道德推理。法律具有道德相關性,法律規定在對個體施加法律義務的同時,也施加了道德義務。個人在主張自己道德權利的同時,可能會違背國家所賦予的道德義務,從而發生道德權利與義務的矛盾,這時涉及到兩者重要性的考量。我國《憲法》第55條規定,“保衛祖國、抵抗侵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公民的神圣職責。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參加民兵組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光榮義務”,明確了公民的道德與法律義務。“沒有國,哪有家”,在保家衛國的道德義務與反對戰爭、殺戮的道德權利之間,后者應被暫時擱置。
3.法律、道德與實踐的綜合推理。道德權利和法定權利有各自的產生基礎,尋找兩者之間的“最大公約數”,那就是實踐。綜合實踐推理,借助與此案例相關的各種利益(法律的,道德的,審慎的,實用主義的)來解決法定權利和道德權利之間的沖突。結合法律與道德的實踐相關性,在具體個案中對道德與法律進行平等考量,沿著道德推理與法律推理綜合的思維路徑,解決具體問題。
(二)道德權利的法律化
美國現代綜合法理學家博登海默指出:“那些被視為是社會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義原則,在一切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具有強大力量的強制性質。這些道德原則的約束力的增強,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規則而實現的。”道德權利的法定化,是對倫理道德的肯定,有利于個體善向群體善的轉化,每一次轉化都是一次道德的進步。具體途徑如下:
篇(2)
作者陳林林,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杭州310008)
法律原則的司法適用是法律方法領域的一個熱點問題,近四十年來持續位居國際法律理論的研究前沿。德沃金和阿列克希為代表的法律原則理論,以基于“規則-原則”二元規范模型的整全性、融貫性和“權重公式”,展示了法律原則適用中“理性化考量”的方法和判準,但被批評為“難以信服”、“基本沒什么價值”。①法律原則的反對者甚至認為,法律方法論只需兩種類型的規范:正確的道德原則和實定化了的法律規則。法律原則既無法律規則在行為指引方面的確定性優點,又不具備道德原則具有的道德正確性優點,所以在法律方法論中并無一席之地。②不過,倘若否定法律原則的規范地位,那么在遇有規則漏洞的疑難案件的裁判中,法律推理是否仍然是一種區別于普遍實踐推理的、“部分自治”的推理模式,也就成為了一個問題。實際上,藉由對規則、尤其是原則之類別的進一步細分,能對法律原則的適用過程――尤其是規則和原則的關系――給出一個更清晰的結構性分析,并回應、澄清對原則理論的一些詰難和誤解。
一、規則的兩種屬性:自主性和總括性浙江社會科學2012年第3期陳林林:法律原則的模式與應用
法律原則理論作為一個系統的規范理論,見諸于德沃金對法律實證主義的批評。通過描述原則在疑難案件中的裁判功能,并藉此確立原則的法律屬性或法規范地位,德沃金意欲否定“法律是一個由承認規則保障的規則體系”這一實證主義的基本信條,并據此重新劃定法律的邊界。在對Riggs v. Palmer案和Henningsen v. Bloomfield Motors案的解讀中,德沃金論證了一種與法律規則全然不同的法律原則。具體說來:其一,規則是以非此即彼的方式適用的。對于個案來說,構成事實要件一旦確認,規則就要么適用(規則生效),要么就不適用(規則無效)。由于原則并未清楚界定事實要件,因此對個案來說,并不存在一條確定的、排他適用的原則。一條原則只是支持這般判決的一個理由,同時卻可能存在另一個更優越、更適切的原則,要求作出不同的判決;其二,原則在適用中含有一個規則所沒有的特性,即“分量”或曰“重要性”。當不同原則之間發生沖突時,法官必須權衡每一條原則的分量并擇優錄用,但這不會導致落選的原則失效。規則的沖突直接涉及效力問題,不予適用的規則會事后失效,并被排除在既定法律之外。③德沃金隨后指出,形式取向的承認規則無法識別出法律原則,因為法律原則并非源于立法者或法院的某個決定,而是一段時期內在法律職業共同體中形成的公正感,需要從形式和內容兩方面入手才能得到識別。④法律實證主義的巨擘拉茲,試圖否認規則和原則之間的“質的差別”,來化解德沃金的批判。拉茲指出,某些貌似法律原則的評價性標準,只不過是法律規則的縮略形式;法律規則在相互沖突之際,也存在分量上的比較。⑤所以,原則和規則的差別僅僅是程度上的,而非邏輯上的。拉茲進而以社會來源命題為分析工具,強調了法律原則的事實屬性。他主張即便法律原則是一種道德評價,那么它也是一種事實存在的公共價值標準。因此,“法律”的內容及其存在與否,仍可以參照社會事實、依據承認規則予以決定,而無需訴諸于道德權衡。⑥
德沃金和拉茲的爭論,表明法律規則和法律原則各自可能存在雙重屬性或二元類別。法律規則作為一種一般化的規范性指示,由事實假設和行為方式或后果兩部分組成。制定法律規則的理由或依據,是道德原則平衡或價值判斷;換言之,法律規則是對各種道德原則進行通盤考慮之后進行理性選擇的產物。法律規則一旦形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遮蔽(opaque)了規則背后的道德理由,即規則的適用不需要法官再行關注設立規則的一系列原則。判斷規則是否可得適用,只涉及理解表述規則的文字,確認爭議事實是否存在,并對照這二者是否一致。⑦當一條規則依賴若干相關的一系列原則的平衡得以正當化后,規則隨后就排除或取代了那些原則――即所謂的一階理由或基礎性原則――直接適用于規則自己所涵蓋的那類事實情形。這就是規則的二階命令、排他性特征的來源。排他性理由最重要的功能,在于排除了理由的通盤考量這個實踐原則,即規則不僅排除了其他理由的適用,而且自我界定為采取特定行動方案的一個理由。規則具有的二階命令、排他性的特征,顯現了規則在適用上的一個屬性,即規則的“自主性”。
規則的“自主性”地位,來源于規則的另一個屬性――“總括性”,即作為一種一般性規范的規則代表的是一些全局判斷,是對各種一階理由或一系列原則進行通盤權衡后所做的行動選擇。規則的總括性特征,讓法官“依規則裁判”時不僅能節約成本,還能減少偏見、避免自行權衡出現錯誤。但要注意到,可錯、偏見與成本,是理性行動所固有的缺陷,作為總括性解決方案的法律規則,本質上仍是一種“次優”而非“最優”的解決方案。因為最優的行動方案至少建基于三個必要條件:一是擁有有關個人處境與行為后果的完整信息;二是發掘出適用于該處境的全部理由;三是對于該理由適用的推理過程是完美的。這些條件的結合,才使得“理性的行動”呈現出“在獲得有關行為人所處實際境況全面、準確的信息的基礎上,找到對行為人的行為最佳支持”這個基本含義。但這是太過理想化的看法,因而無法得到真正的實現。⑧
德沃金和拉茲皆指出,規則最主要的邏輯特征是其“決定性”:當一個具體的事實情形符合規則的適用條件,那么規則就必須得到遵循。自主性意義上的法律規則,是排除一階理由意義上的原則權衡的,或者說,在適用中是怠于或否定對一系列原則的權衡進行持續評估,因此其始終是具有決定性的。對于總括性意義上的法律規則而言,只要法院不改變對道德原則之間的基礎性平衡的認識,那么它同樣是具有決定性的。不過,當法院對基礎性的道德原則平衡的觀點發生變化時,總括性規則就會不斷地得到修正。顯然,較之自主性規則,總括性規則的“決定性”更弱而“內容性”更強。與規則適用中的自主性特征和總括性特征相對應的,是法律原則的理性化模式和最佳化模式。⑨
二、原則的兩種模式:理性化和最佳化
對于個案裁判而言,自主性法律規則必然是有拘束力的。當法官遇到了既有規則未予明確規定的個案時,如果要貫徹一致性和平等對待,那么依據德沃金的理論,法官能采取的合理方法是根據一系列原則――這些原則能最佳地證成一系列相關的、有拘束力的自主性法律規則――來判決案件。如果所有這些法律規則在道德上是正確的,那么法官可以認為,那些為規則提供正當性的法律原則在道德上是正確的。當然,法官也可能認為,某些自主性規則在道德上也可能是錯誤的。在此情形下,法官往往會主張,依據能從道德上正當化那些長期有效的自主性規則的次佳原則是合適的。次佳原則為道德上存疑的一些自主性規則做了最直接的辯護,藉此允許法官在判決新的案子時,能盡量與現行的那些規則保持一致。這種與規則自主性觀念相輔相成的原則適用過程,因為仍然以一致性、可預測性等形式價值(次佳原則)為最優判決目標,被稱為法律原則的理性化模式。⑩
前述分析表明法院(乙)認同先前判決設立的規則R,但支持理由卻不同于法院(甲)。在這種情形中,法律原則的理性化模式和最佳化模式實際是重合的,因為最終的行動方案是相同的。但是,如果純粹基于法律原則的最佳化模式的分析思路,那么法院(乙)應追求個案相關的一系列相關原則的最佳平衡,因此不一定受法院(甲)的判決推理或結論的拘束,盡管法院在原則平衡時仍然要考量到可預測性、一致性等第二位階的原則。換言之,法院(乙)在跨越適當的認知門檻后,可以法院(甲)的判決推理或結論,例如否定作為規則R之正當化基礎的原則C2,修改規則R的事實構件,乃至否定規則R本身。當然,廢棄規則R這樣的重大法律變動,必須基于一些德沃金“整全法”意義上的整體性理由,即視為是錯誤的規則或判決,必然落在不能依最佳化證立予以正當化的那部分既定法律的范圍之內。顯然,基于最佳化模式的法律推理,還內置了羅爾斯式的審慎明智、協調一致的“反思性平衡”:在普遍性的所有層面上做出深思熟慮的判斷,其范圍從關于個人具體行為的判斷,到關于特定制度和社會政策之正義和非正義的判斷,最終達到更普遍的信念。這意味著一條原則的法律地位部分地依賴于一種規范性標準,這個標準要求原則的內容和分量居于道德合理性的適當范圍之內。法官必須訴諸于自己的道德信念和識別力,來判斷這個標準是否得到了滿足。換言之,法官們必須和自己進行道德論辯,而不單單是審查和以往其他人的道德推理相關的社會事實。藉此也再一次表明,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不是純粹基于系譜的,也不可能完全是基于內容或道德論證的,它是獨立于規則和道德原則之外的另一類規范依據。因此在遇有規則漏洞的疑難案件的裁判中,基于法律原則的判決推理,仍然可以顯現為一種區別于普遍實踐推理的、“部分自治”的推理模式。
作為一種司法裁判理論,法律原則的兩種模式是有一定解釋力和說服力的,但也難免于若干困惑。限于篇幅,此處只討論隱含其中的三個基本問題:A、法律原則的規范屬性;B、適用法律原則的司法語境。C、原則適用的方法論。問題A所指的法律原則的“規范屬性”問題,和反對法律原則的學者所提的問題相關卻并不相同。亞歷山大和克雷斯曾強調:法律原則既無法律規則在行為指引方面的確定性優點,又不具備道德原則具有的道德正確性優點,因此在法律方法論中沒有一席之地。前面的論述已指出,法律原則是獨立于規則和道德原則之外的另一類規范依據。但很顯然,法律原則在行為指引方面的確是不同于法律規則。這種“不同”的表面差異是行為指引上的確定性程度,實質差異是某個法律體系中的法律規則既是“行為規范”又是“裁判規范”,但法律原則僅僅是一種“裁判規范”。行為規范和裁判規范的劃分,可追溯至邊沁的理論。邊沁曾以刑法為例指出,“規定犯罪的法律與對犯罪施加處罰的法律,是兩種不同的法律。……它們管轄的行為完全不同;適用的對象也完全不同”。一條“禁止殺人”的規則,既是社會公眾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也是殺人案件發生后法官必須考量適用的裁判規范,并且對于公眾和法官來講,“禁止殺人”都是一條明確的法律規則。相反,一條“任何人不得從自己的錯誤行為中獲利”的原則,盡管也是社會公眾應當遵守的道德行為規范,但一般公眾在社會交往的過程中,并無恰當的能力(例如法律素養或法感)和信息(例如檢索以往判例)――因此也無義務――去識別該原則是否是規范某一具體事項的一條法律原則。不過依據法律原則理論,一旦這類爭議被遞交到法官面前,法官就有義務去識別并適用與個案相關的法律原則;此外,判斷一條道德原則是否是法律原則,取決于法官是否認定其得到了制度歷史的支持,而與社會公眾的認識或判斷無關。換言之,法律規則既是行為規范也是裁判規范,其適用對象既包括法官,也包括生活在某個法律體系中的社會公眾;法律原則是一種裁判規范,它的適用對象僅僅是法官。
“法律原則的適用對象僅限于法官”這一命題無疑會招致批評,因為在適用法律原則進行判決的那類疑難案件中(例如瀘州遺贈案、Riggs v. Palmer),當事人最終顯然受到了法律原則的拘束。不過,這種批評只看到了裁判的表象。以瀘州遺贈案的一審判決為例,納溪法院實際依據《民法通則》第7條“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這一原則,針對遺產繼承規則的效力設定了一條“第三者繼承例外”的新繼承規則。法云“一般條款不決定具體案件”,正是將《民法通則》第7條具體化為個案規則后,法院才否定了遺囑的效力和第三者的繼承權。因此一個補充性的亞命題是,“當法律原則適用于待決案件時,必須先具體化為一條個案法律規則;這條新創設的法律規則必然是可普遍化的,它既適用于社會公眾,也適用于法官”。用阿列克希的“原則間的競爭法則”(Law of Competing Principles)轉述之:當法律原則P1在C的條件下優于法律原則P2,并且,如果P1在C的條件下具有法效果Q,那么一條新規則R生效,該規則以C為構成要件,以Q為法律效果:CQ。
藉此轉換到了問題B:適用法律原則的司法語境。一個已有的共識是,依據“禁止向一般條款逃逸”的裁判紀律,唯有在“規則用盡”的疑難案件中,方得考慮適用法律原則。法律原則的兩種模式和“裁判規范”的定位,都表明原則裁判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司法”,而是一種創設規則的準立法性法律實踐。事實上,德沃金的法律原則理論,引證的就是以法官為中心的普通法司法實踐。離開普通法司法的語境,法律原則理論中的若干關鍵詞――例如“制度性支持”、“先前判例”、“分量”、“”――的內涵就會引發歧義。因此,在司法體制和法官角色存在重大差異的大陸法系,盡管成文法中存在不少概括性條款或原則性規定,但法院是否可以根據最佳化模式進行規則創制并進行裁判說理,始終夾雜著諸多需澄清的問題,諸如法院的地位和功能、法適用和法創制的區分、法不溯及既往等等。
第三個基本問題是原則適用的方法論。法律原則的“分量”、“最佳化”等屬性,從字眼上就表明原則裁判的關鍵,是用法政策式的權衡或類推去獲得判決,其間必然訴諸對相關的不同后果及其可取性所做的比較和評估,即利益衡量。就如麥考米克所言,倘若判決所依據的那些相互競爭的類比、規則或者原則存在于法律之內,并表明判決為既有法律所支持――盡管不像明晰的強行性規則所提供的支持那般明確,那么法官有權作出相關的評估并使之生效。德沃金后期實際也承認,自己是一個整全性意義上的、向前看的結果導向論者。原則理論的支持者阿列克希,則進一步精細化了結果考量式的衡量方法,建構了一個復雜的“權重公式”:W1-i,2-j=(I1×W1×R1+……+ Ii×Wi×Ri)/(I2×W2×R2+……+Ij×Wj×Rj)。不過,所有這些努力――包括法律原則的兩種模式理論――回答了一些問題,卻又制造了一些新問題。
四、結語
哈特認為在法律規則不能給予判決以完全指引的案件中,裁量權的運用是在一些標準和政策指引之下進行的。不過,哈特對這些標準和政策存而不論,并否認其是法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這恰恰是德沃金這樣的法律原則論者所反對的。法律原則的兩種模式為原則裁判提供了一個清晰的結構性分析,還表明法律原則的效力標準不是純粹基于系譜的,也不可能完全是基于內容或道德論證的,它是獨立于法律規則和道德原則之外的另一類規范依據――“裁判規范”。“裁判規范”的定位,保證了在遇有規則漏洞的疑案裁判中,基于法律原則的判決推理仍然是一種區別于普遍實踐推理的、“部分自治”的推理模式,盡管這種源于普通法司法的推理模式在方法論和制度環境上遺留了一些有待澄清的問題。
注釋:
①See Brian Leiter, The End of Empire: Dorkin and Jurisprud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36 Rutgers Law Journal, 2004, p.165.
②Larry Alexander & Ken Kress, ‘Against Legal Principle’, ed. in Law and Interpretation, by Andrei Marm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326, 327.
③Cf.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4.
④Cf.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05-17.
⑤Joseph Raz, “Legal Principles and The Limits of Law”, 81 Yale Law Journal, 1972, p.829-30. 麥考密克認為,原則“實際是一種更概括的規范,是若干規則或若干套規則的合理化結晶”。See Neil MacCormick,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232.
⑥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p.53.
⑦Alan H. Goldman, Practical Rules: When We Need Them and When We Do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07.
⑧T. M. Scanlon,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2.
⑨Cf. 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792.
⑩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795.
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796.
Richard Posner, ‘Pragmatic Adjudication’, in The Revival of Pragmatism: New Essays on Social Thought, Law and Culture, Morris Dickstein ed. 1998. cited from Adrian Vermeule, Judging under Uncertainty: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87.
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796,801.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40.
Joseph Raz, ‘Legal Principles and the Limits of Law’, 81 Yale Law Journal, 1972, p.823.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343.
斯蒂芬?佩里的分析較為繁瑣,下述行文對其進行了概括梳理,Cf. 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801。
[美]約翰?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姚大志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頁。
Bentham,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430 (W. Harrison ed. 1948). Cited from Meir Dan-Cohen, Decision Rules and Conduct Rules: On Acoustic Separation in Criminal Law, 97 Harvard Law Review,1984, p.626.
Cf.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 by Julian Riv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54.
篇(3)
一、實質法律推理的內涵及其在司法活動中的適用范圍
我們應該看到,在司法實踐中,由于法律規范的抽象性與普遍性、成文法的滯后性與保守性、法律語言的模糊性與多義性、案件事實的復雜性與社會發展的持續性,一些問題往往用形式推理的方式難以解決。例如,當案件事實即可適用此規則又可適用彼規則,或兩個規則都不可完全適用,并且這些都可適用或都不可完全適用的規則間又存在相互沖突的情況下,法官就可以而且必須在法定框架內從公平、正義出發,根據立法者制定法律規范的價值理由和案件事實的實質內容而進行價值評價或在相互沖突而又都有一定道理的利益間進行實質權衡推理,這就是實質法律推理。這種推理主要是法官對法律規定和案件事實的實質內容按合法性和正當性原則進行價值評價或者在相互沖突的利益間進行選擇的推理。舉個實例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在眾所周知的“醫生秘密摘取尸體眼珠案”中,該醫生的行為已經具備了“非法盜竊、侮辱尸體罪”的形式要件;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器官移植是應該受到鼓勵和支持的,在相關法律尚未健全的情況下,醫生出于解決患者痛苦以及推動該項事業發展的動機,做出了秘密摘取尸體眼珠的行為,它雖然不合法,但絕不是刑法所要懲罰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不對該醫生判罪處罰,既符合社會進步與社會發展的理念,也符合立法目的與立法價值取向中的合理成分。關于實質推理在司法活動中的適用范圍,美國法學家E·博登海默曾列舉如下幾種情況:
(1)法律沒有提供解決問題的基本原則;
(2)法律規范本身相互抵觸或矛盾;
(3)某一法律規范用于一個具體案件明顯又失公正。
有學者認為上述列舉的適用情況不過全面,指出法律實質推理的適用大體包括如下幾種情況:
(1)出現“法律空隙”;
(2)法律規范的涵義含混不清;
(3)法律規范相互抵觸;
(4)面臨“合法”與“合理”相悖的困境;
(5)法律條款包含了多種可能的處理規定。
實際上,歸納起來,無非是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當案件面臨著“合法”與“合理”相沖突的矛盾,當嚴格適用法律條文會導致不公正的困境時,在選擇作為大前提的法律規則是既要考慮相關的法律規定,也要從社會整體利益,從普遍道德準則出發,加以權衡,選擇好大前提,作出符合法律規定的精神實質或立法意圖的裁判結論;二是當法律自身存在沖突時,需要法官依據法律規則、立法精神,甚至是法理,進行辯證推理,從中選擇正確的判案依據。例如,當民事審判無法可依時(當然不包括刑事審判),法官有時也需要依據公理來推理選擇,而公理在我國主要來源于公共道德、風俗習慣、正義觀念及黨的政策等。正是因為以上特點,實質法律推理有可能成為法官在司法實踐中彌補法律漏洞,實現社會公正,促進司法公正的重要方法。
二、實質法律推理的類型
對于實質法律推理的類型具體又哪幾種,沒有過一致的意見。波斯納就說過,法律推理就是一個“雜貨袋”。羅素干脆把超出演繹邏輯之外的“永遠只帶有概然性的推理”稱為“實質性推”。筆者認為,法官在司法活動中進行實質推理,主要包括以下幾種類型:
(一)歸納推理
歸納推理的邏輯形式是A1是B1,A2是B2,A3是B3……,所以一切A都是B。由于歸納推理是從個別到一般的推理方法,它通過具體的個案,證明某種普通性的東西,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它在判例法體系的國家里被廣泛使用。事實上,在有些情形中,法官會發現沒有任何法規或其他既定規則可以指導其審判工作,但他也許能夠從對一系列早期判例與判例價值所進行的比較推論出有關的規則或原則。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11月21日的《關于人民法院審理的離婚案件如何認定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若干具體意見》,它把夫妻感情已破裂這一判決離婚的法定界限具體化為14條意見,凡符合其中之一的,視為夫妻感情確已破裂。在這14條意見中,有一些就是通過運用歸納推理概括司法實踐中的成功判例的出的。這時候,歸納推理的邏輯形式就可表達為:A1案件被成B符合社會公正的需要,A2案件被判成B也符合社會公正的需要……,因此所有A類型的案件被判成B都符合社會公正的需要。
(二)類比推理
類比推理的思維原理是:把兩個(或兩類)事物進行對比,并根據他們的某些屬性相同,而推測出他們的另一屬性可能相同的結論。用邏輯形式表述為:
A與B都具有屬性a、b、c,A還有一個另一個屬性d,所以B也可能具有屬性d。由于類比推理的形式具有雙重性,是近乎于歸納推理與演繹推理相結合的一種推理形式,所以在司法實踐中,當法無明文規定,即出現法律漏洞時,法官就會先通過歸納總結,尋求最相類似的法律條文來進行漏洞補充,再運用演繹推理將案件事實涵蓋于法律規則之下得出判案的結論。此時,類比推理的邏輯形式就可表達為:M法律要件有P法律效果(大前提),S于M法律要件類似(小前提),故S也有P法律效果,因此M應當作為案件適用的法律(結論)。
(三)當然推理
當然推理,指某些事實雖沒有法律明文規定,但與有法律規定的事實相比,更有適用該法律規范的必要。這種推理亦即法律中所謂的“舉重明輕、舉輕明重”。如,公園禁止折花,而禁止伐木摘果,自不待言;禁止牛馬通行,則較牛馬更大的象,更不待論。當然,當然推理,首先要認真考察立法者的目的。例如:我國《刑法》第170條規定,“以營利為目的制作、販書、畫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處罰金。”顯然,法律條文中沒有關于制作、販穢影片的明文規定,但依立法者的意圖看,制作、販穢影片較之前者,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因此更屬禁止之列。法官運用當然推理時還會受其本人價值觀念、情感因素以及周邊環境等的影響。
(四)直覺推理
當法官憑自己具備的知識和經驗對案件的結論作出自覺或情緒的判斷(司法感知),然后回溯到選中的法律條文并采用不同的解釋方法解釋該條文,為預先感知和判斷得出的結論“給出理由”,或者說檢驗此判斷是否正確。在能夠給出理由或者認為判斷正確的情況下,將該法條作為下一步司法推理的大前提,否則就予以排除。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直覺推理的過程,它是一種經驗方法的法律推理。直覺推理的邏輯形式可以表述為:如果直覺是M,那么,在能夠給出理由時M就是真的,反之M就是假的。這里,推理的作用就在于為下一步的司法推理提供大前提或者排除其作為大前提(當M為真實時為大前提,當M為假時不是大前提);它的特殊性在于不能單獨而要與其他解釋或推理方法配套使用;它的價值在于提高法律推理的效率,即在憑直覺迅速選定相關發條后,通過對發條的直接解釋或推理解釋,為這個選擇提供理由或為否定這個選擇進行論證。
三、正確運用實質法律推理,進一步實現和促進司法公正
所謂司法公正,是指法官遵循正當的法律程序,運用法律公正地解決訴訟所涉爭議事項,并在社會公眾面前樹立起公正的形象。公正是司法活動的靈魂和歸宿,不求公正的司法,毫無實際的意義;損害公正的司法,其危害不亞于違法犯罪行為者本身。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動的一條基本原則,是維護公民合法權益的需要,是司法主體最起碼的倫理要求,更是建設法治國家的迫切需要。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做到司法公正,那么這個社會其他任何形式的公正就不再有保障,人們的合理預期就無法得到實現,公眾則會對這個社會失去信心,進而可能引起社會的動蕩不安和政局的不穩定。世界各國的司法實踐證明,正確運用實質法律推理,能進一步實現和促進司法公正,這是由法實質推理的性質決定的。
(一)實質法律推理是一種論證性思維活動,具有理性特征,有可能成為實現司法公正的基礎。實質法律推理不僅為各法律領域和法律部門中實際的法律論證提供了法理學的抽象基礎即一般理性思維方法,而且還為審判提供了目的性標準,使訴訟成為一種理性的(而不是專斷的、情感的)、辯論(而不是默想的)思維活動。至于作為司法推理直接成果的判決結論,則可以將其視為建立在法律理由和正當理由基礎上的理性產品。無論是利用直接理由還是最終理由,實質法律推理的結論都要創造出新的法律理由。其中,運用直接理由的司法推理創造出適合于個案的特殊法律理由,應用最終理由的司法推理則創造出新的法律原理或包含新的法律原理的判例。從評價的角度看,不同的法律理由依正當性、權威性和有效性的程度而具有不同的份量。當出現若干法律理由時,需要根據它們的份量作出取舍。也就是說,法官在作出裁判時,應當為其裁判結果提供充分的理由,這個理由不僅表現為論證本身能夠自圓其說,而且其說理本身也要在裁判中得到最大化的體現。換句話說,實質法律推理的過程就是論證裁判結果,在多種利益相沖突時,法官要尋求最大權益的合法化,或者說要追求法律、政治、經濟和社會四個效果最大限度的和諧統一,這就必須提供充分的理由和根據才能使人們接受其裁判結果。而在以上四個效果中,法律效果體現的是法律的內在價值,政治、經濟和社會效果體現的是法律的外在價值,一個好的裁判應當實現法律的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的和諧統一。法官要實現上述目標,就只有通過實踐推理中的論證說理才能檢驗案情事實歸納得是否正確,才能說服當事人、人、辯護人和社會公眾接受法官的觀點。例如,審理案件時,在雙方當事人提交的證據發生矛盾難以認定案件事實的時候,我們首先要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民事以及行政證據規則規定的原則精神,從舉證責任的歸屬入手,評價負有舉證責任的一方是否盡到了充分提供證據的責任義務,如果該當事人沒有充分行使舉證的責任,則應當由其承當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在刑事、行政訴訟案件中,由于“無罪推定”和行政機關必須證明其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特殊性,除非巨額財產和行政侵權賠償案件,一般不能采取優勢證據原則。但在民事訴訟案中,如果對方當事人的反駁也構成一種主張或由于其他原因雙方當事人都負有舉證責任,則應當根據優勢證據原則作出價值評判。
(二)實質法律推理是一種有目的活動,具有實踐性的特征,有可能成為實現司法專橫的手段。之所以說實質法律推理是有目的的實質活動,這是因為:
第一,它涉及人的行為,事關案件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
第二,它涉及行為目標,需要推理主體在多種行為決定方案之中擇定達致目標的最佳方案。其直接目標就是依據有實踐信息明確爭端雙方的權利義務,間接目標則可能是解決糾紛,也可能是維護個人權利、實現社會發展目標等。
第三,它本質上是一種行為選擇,而行為選擇的靈魂則是價值與目標判斷。無論是法律漏洞的填補、規則歧義的消除、抽象規則的具體化還是推理的后果評價,都需要推理主體借助于價值論和目的論評價在多種可替代性的規則解釋方案中作出選擇。
以價值判斷與利益權衡為核心的行為選擇之所以不會成為法官的個人專斷,法官之所以不被認為是純粹的強力機構,人們之所以在對它還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合理期待,就是因為法官群體大體上受到實踐理論的約束,以具有普遍性的社會規范來作為法律推理的證據,克服情緒化的因素對法律推理的影響是實質法律推理過程與結論大體上具備一定程度的客觀性,實質法律推理作為法律職業者實際地處理自身與世界之間關系的活動。法律推理作為一種實踐推理活動,“既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又是一個非常個性化的過程。說它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是指任何行為的選擇都是存在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任何行為最終都必須與他人發生關聯,都必須接受一定的社會評價:說它是一個個性化的過程,是因為行為的選擇最終是由行為者自己做出的,根本上取決于對自身行為目的的認識和把握”。也就是說,法官個人行為目的的達成,離不開主體間最低程度的合作,社會評價也對實質法律推理構成了重要限制與約束,即使是以國家政治權利為依托的法院也不能置當事各方的評價于不顧而一意孤行。在實質法律推理中,法官總是尋求盡量減少被視為專斷和非理性的意志的干擾。比利時哲學家佩雷爾曼提出:“實質法律推理不是一種形式的闡釋。而是一個旨在勸說和說服那些它所面者們的論辯,即這樣一個選擇、決定或態度是當前合適的選擇、決定和態度。根據決定所據以作出的領域,在實踐性論辯所給出的理由,‘好的’理由,可以是道德的、政治的、經濟的和宗教的。對法官來說,它們實質上法律的因為他的推理必須表明決定符合他有責任適用的法律。“法官的任務,就是運用法律推理的方法,依照法律制度努力促進的價值,使法律的精神與文字協調一致。”
(三)實質法律推理是尋求價值衡平活動,具有正當性的特征,這是有可能成為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徑。
法官進行實質法律推理時應當考慮到社會正義,公共福祉,公序良俗等價值取向,考慮案件的具體情況,考慮社會安定與穩妥的需要,兼顧社會的公正要求和道義原則,最終在相互矛盾的規定和推論中作出選擇和決斷。在法學領域,因為法律是一種社會規范,其內容為對人的行為的要求、禁止和允許,所以法律推理的核心主要是為行為規范或人的行為是否正確或妥當提供正當理由。法律推理所要回答的問題主要是:規則的正確含義及其有效性即是否正當的問題,行為是否合法或是否正當的問題,當事人是否擁有權利、是否應負法律責任等問題。美國新自然法學家德沃金認為,法律的正當性的主要來源是法律的整體性。所謂整體性包含兩個原則,即立法的整體原則和審判的整體性原則。它要求法律“盡可能把社會的公共標準制定和理解看作是以正確的敘述去表述一個正義和公平的首尾一致的體系。”當然,德沃金的“整體性”概念的內涵十分深刻,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律的一致性,但是它確以法律的一致性為基本條件。而實質法律推理的目的是尋求價值衡平,是為了解決因法律規定或案件事實的復雜性引起的疑難問題,為法律適用提供正當一致的理由。因此,在審判實踐中,實質法律推理必須對多種因素進行全面、綜合的考察,往往綜合運用演繹、歸納和類比等推理方法,并通過多樣化的推理規則獲取符合法律和事實辨證發展規律的正當性結論。
法律推理通過對正當理由的探索,“有助于鞏固社會組織制度所需的智力內部結構,在此制度內爭論表現為論證和反論證,而不是使用暴力的威脅。”通過法律推理,對判決結果給予具有說服力的理由,是法治型法律制度的一種強制性要求。法治社會的審判合法性或正義判決的要求,使審判人員在將法律條文、事實材料和判決結論三者結合起來的過程中,負有為判決結論提供理(法律理由或正當理由)的法律義務和道德義務。司法人員如果逃避這種法律推理的義務,就會導致草菅人權和司法腐敗。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律推理就是“說理”,法制發展史就是用法律推理代替刑訊逼供和擅斷的歷史。
(四)實質法律推理是法官在司法過程中分析和解決法律問題的邏輯方法,具有職業化的特征,這是有可能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條件。“司法腐敗”是當前司法改革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如何抑制乃至消除“司法腐敗”?人大監督、“違法審判責任追究”、“督導員制”、“審判紀律處分”等都是一些有益的方法。但是,怎么樣將上述方法與司法獨立協調起來,如何避免對法官這種特殊職業群體行業的行政化管理,則是尚未完全解決的一個復雜問題。法治社會的實現要通過法律職業者的職業化努力。通過長期的、各種形式的法律教育、法律職業者運用共同的法律語言、法律思維、形成一種符合法治社會要求的理性思維方式,這對在法律職業內部弘揚正氣、公正司法、公正執業,具有更為長遠的意義。法律推理是制作具有約束作用的判例體系的理論武器,而通過先例約束法院和法官,使下級法院受上級法院判例的約束,上級法院受自己判例的約束,就是在司法職業內部建立了一種自律機制,這是在制度上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方法。法官隊伍職業化,是法官獨立的重要標志,也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條件。要真正實現法官獨立或職業化,不僅要有適合于法官職業化的司法制度模式,而且還要有適合于法官職業化的法律思維模式。
篇(4)
他們得病的原因是基于這樣的事實:他們所飲用的檸檬汁中含有大量的石碳酸,對檸檬汁瓶里殘留的檸檬汁進行檢查,結果顯示:檸檬汁中含有大量的石碳酸混合物。原告丹尼爾斯夫婦隨后控告了檸檬汁的生產商和出售檸檬汁的酒店老板,需要對他們的人身損害,醫療費以及生病期間的應得收入的損失進行賠償。
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會作這樣的演繹推論:
(A)在任何情況下,如果由一個賣給另一個人的商品有缺陷,即與其使用性能不符合,但在普通檢測中又不明顯,那么賣出的商品未達到商品質量要求。
(B)在本案中,由一個人賣給另一個人的商品有缺陷,即與其使用性能不符合,且在普通檢測中又不明顯。
(C)所以,在本案中,銷售的商品未達到商品質量要求。
如果用符號來表示命題形式,則上述推論形式簡化為;
(A)在任何情況下,如果p,則q,
(B)在本案中p,
(C)所以,在本案中q.
從邏輯的角度上說,這是一個有效的論證形式。然而在這里我們并不主要關心其邏輯推演的真,而關心其,也就是關心:在法律的實踐中有效的論證形式的邏輯應用。論證是有效的從而使得如果前提是真的,那么結論應該是真的成為必要,但邏輯本身不能建立或保證前提的真實性,它們是否塌實是一個全憑觀察和實驗的。讓我們因此重新考慮論證,以明自在什么背景下,它的前提應該保持真。
正如在格蘭特一案中所陳述的那樣,(A)前提已有一個對“商品質量問題”條款的含義作出符合法律目的的權威性解釋,因而(A)已有了一個真實的法律前提。
小前提(B)怎樣呢?前提(B)是真的,僅當以下各點是真的:
(ⅰ)一瓶檸檬汁屬于種類商品;
(ⅱ)這瓶檸檬汁是由一個人賣給另一個人的;
(ⅲ)一瓶檸檬汁中有一種帶有缺陷的石碳酸混合物;
(ⅳ)這是一種在普通檢測中不能發現的缺陷。
從案件實際情況看出(B)前提也是真的。
選擇這樣一個簡單案例作為的起點的一個優點是,四種假設的每一種都面臨著它的不容置疑的真實性。但值得說明的并且以后再繼續提到的一點是,萬一在檸檬汁中出現的毒物象稍稍不著色的檸檬汁,情況會怎么樣呢?那么就會出現這么一個問題:實際案件中的“證據材料”是否是法律上所表述的象前提(A)命題的 “可操作的事實”的真實事例?那么作為一種關于實際例子的辯護主張,(B)前提的真實性可能是值得懷疑的。
由此可見,證據的程序是這樣一種確立的程序。一些反映證據事實的命題是為法律目的而被看作是真的。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被確定的關于法律推論的討論既是一個關于“如果p,則q;p,所以q,”的形式的邏輯有效性的討論,又是一個由前提都給出判斷標準的適合法律目的的真實的討論。
二、有效的邏輯推理與實際的審判行為
通過對論據的一系列分析得出一個結論:由于賣方(即酒店老板塔伯得夫人)未能履行其責任,使買方(丹尼爾斯夫婦)蒙受了損失,賣方有賠償買方的義務。這是通過可靠性很強的演繹推理得出的結論,應該說是準確無誤的。法官也就必須根據法律和推理作出最公正的判決。法官有義務做出他應有的判決,他為履行其義務而做出某種判決并不意味著他通常做出或將要做出甚至已經做出那樣的判決。不論從自然上講,還是從心講或邏輯意義上講,一個人并未按他理應做的事去做而做出有背其責任義務的事來,這些都是可能的。因此說,人的行為往往并不由邏輯推理來決定,而是由所選定的動因或其他決定。而如果這些是正確的,又將決定我們選擇對象。一行為者在完成或考慮執行其行為時所采用的判斷標準(好與壞,對與錯,合法與不合法等)是根據符合其標準的前提建立起來的。
令人奇怪的是法官接收到一樁訴訟案件時選擇什么樣的是非標準使他困惑迷惘,而他卻并不因此而定下心來決定做出什么樣的選擇即何等命令。他不必在開庭時公開陳述他做出這樣決定的原因,來自體系的壓力——使他能獨立闡述對本案的看法,上訴的可能性等也許會使他根據合法的前提和事實依據入手做出邏輯推理繼而做出公正的判決。但事實上這幾乎僅僅是人們的愿望而已因為來自外界的壓力諸如新聞媒體的完全相反的見解,議會的評論等往往會使他做出完全相反的判決和命令,這不得不令人感到驚訝。所以從傳統的法律道德和心角度講,法官這樣做很不可能,但事實上又是可能的。即使不可能,這種不可能也不是邏輯意義上的不可能,法庭的裁決往往并不是根據事實進行邏輯推理的結果。
若對前面再深入一步發現:任何一“法官都知道在一案例中,他必須通過法律名義作出判斷,現我們假定這樣一個推理:”如果p成立,q就成立。“”同時設想在一具體案例中,如果某原因使法官不偏袒于結論q成立,常識會為他找到明顯的漏洞,他可以簡單地說他找不到證據證明p成立,因而沒有推理的前提;同時,假如他想以q定義作結論,那么在該案中他就只需說證據表明p是正確的即可。由此可見,從表面上看,雖然推理的形式存在,但由于他做出判決之前,他決定了如何選擇。
提出法理的過程就其特點來講往往純粹是演繹和推理的過程,即使法官先生們經常搞錯甚至歪曲他們發現的事實根據,但他們在以法律規范為準繩,以事實為基礎的原則中,要么進行真正的演繹推理,要么根本沒有推理可言而得出結論仍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我們在哪怕是一個案例中證明通過純粹的演繹推理能讓法官做出令人信服的決定,目的是為了說明演繹推理的可靠性的確存在,而且在現實生活中,演繹推理得出讓人信服的結論的例子不時會有出現,但我們還有疑問,比如這是不是經常發生(實際上并不經常),如果純粹的演繹推理不可有解決問題時,或者由于某些原因,法官或法庭并不采用這種推理方式時,我們又采取什么樣的推理形式呢。
小結:①法庭常會找到各種事實根據,而這些“事實”不論事實上是正確的或錯誤的,從法律角度講都認為真而不假;②我們能把法律條款用“如果p成立,那么q 定義就成立”的命題形式表達出來;③我們還發現,至少有時所能找到的事實根據正是該形式中很清晰的p定義,因而如果我們以法律命題的事實為基礎,以事實為推理的前提,通過演繹推理,我們的確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而該結論所引發的命令相應會使該結論產生實際效力,并且理由十足。
顯示①表現為實際的審判行為,②、③表現為法律推理。
三、法律意義上的“合乎邏輯”與“不合邏輯”
篇(5)
于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規定:“判決書應當寫明判決結果和作出該判決的理由。判決書內容包括:
(一)案由、訴訟請求、爭議事實和理由;
(二)判決認定的事實和理由、適用的法律和理由;
(三)判決結果和訴訟費用的承擔;
(四)上訴期限和上訴的法院。”
較之現行的民事訴訟法,新民訴對判決書內容的修改主要體現在:作出判決結果的理由,以及適用法律的理由之上。然而,如何在判決理由闡述的現狀基礎之上,使以上概括性規定得到具體實踐,涉及的不僅是法官的責任意識、工作的認真態度,其必然關涉到法官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的審判思維以及現行司法體制下法官的角色定位等問題。本文試圖通過對判決理由闡述的現狀進行分析,從審判邏輯角度探尋新民事訴訟法對判決理由闡述的新要求。
一、判決理由闡述的現狀
(一)判決理由的定義:“法官根據當事人各方的主張和抗辯,認定事實和適用相應的法條,進而得出判決結論的推理過程。”
根據以上定義可知,判決理由即法官審理過程中所適用和形成的推理過程。然而,在不同的法系中,由于不同的推理過程的適用,形成了判決書中判決理由闡述的不同風格。
(二)兩大法系判決理由的比較
1、大陸法系
大陸法系國家均以成文法典為法源。即以一定的法律規則為依據,使判決書看起來是從法律事實和法律規則的前提中運用邏輯演繹的方法必然得出的。
2、英美法系
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律系由法院創設,判例即為法源,法院采取“由案件到案件的推理”,斟酌事物本質及合理性,依歸納的方法逐漸建立法律的原則。同時,特別重視事實資料及經驗知識,并且深入討論各種解決可能方法所產生之后果。
“英美法系以上判決風格的形成,除了歸納式的推理的運用之外,判例之法源性、法官選任方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英美法官大部分是從律師中選任,小部分為大學教授或政府高級官員。如此出身背景的法官所作成之判決不會使用簡潔、抽象、機械化的官式語言,而會傾向于表現自己的人格與見解。”
3、我國民事判決書判決理由闡述現狀
(1)無立法上的明確要求
《民事訴訟法》一百三十八條:判決書應當寫明:
(一)案由、訴訟請求、爭議的事實和理由;
(二)判決認定的事實、理由、和適用的法律依據;
(三)判決結果和訴訟費用的負擔;
(四)上訴起期間和上訴的法院。
(2)在我國的司法判決書中,很少有法律理由和法律推理過程的展示,一般首先陳述原被告雙方的訴訟請求、對案件事實的陳述和有關證據,然后,經過一句“本院經審理認為”的過渡,便直接宣告原告或被告的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最后依據某條或幾條法規做出判決。從判決書中展現出的僅僅是簡單地形式三段論推理。
二、形式推理與實質推理
在我們將判決理由定性為推理過程的前提下,可分類為形式推理與實質推理。不同的推理方式可以反映出不同的司法目的和追求,而現行司法實踐中,不同方式的運用也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一)形式推理
“源于形式主義的法律推理理論,在推理方法上以邏輯推理為主導形式,主張一切法律法律問題都可以通過應用明確的、不變的規則而做出決定,因此,一切法律問題的答案都是在人們的意料之中,唯一可用的法律推理方法就是邏輯的演繹三段論。在這種模式中,法律規則是大前提,案件事實是小前提,法官只需通過邏輯的演繹推理便能得出明確的法律判決結果。”
與形式推理向對應的是形式性的司法模式和環境,形式性司法是指堅持法律適用的外觀和法律依據的至上性,拒斥對法律依據背后的實質性理由的探究。
(二)實質推理
“在實質推理要求下,法律推理不只是根據確定的法律規定和案件事實作為前提得出法律結論的邏輯演繹的過程,而是要涉及到對法律規定的選擇,對案件事實的剪裁和對法律結論的合法性、合理性、綜合性進行平衡的過程,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推理前提的合法真實,并通過推理將前提的這一專屬性傳遞給結論。”
與之相對應的司法模式和環境是實質性司法,即其不拘泥于法律依據的外部表現形式,而更傾向于對法律依據背后的實質性理由的探究,并且可以借口實質性理由的正當性而背離法律依據的表面規定。
三、從形式推理到實質推理
(一)形式推理在我國現行司法中的具體運用及其缺陷
在我國民事判決文書中,判決理由的闡述大多以形式推理為其表現形式。
以“衡水子牙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與張晶延等侵犯發明專利權糾紛上訴案”的判決書為例。在案件中,張晶延(以下簡稱“張”)訴稱“衡水子牙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子牙公司”),未經許可在其建造的工程中運用了由張享有發明專利的“預制復合承重墻結構的節點構造施工方法”,侵害了其發明專利。而子牙公司以包括由張擁有發明專利的技術在內的《CL結構構造圖集》現為河北省工程建設標準設計為由,主張該技術屬于已有技術而不屬于侵權。而法院的判決書中,對上訴人子牙公司的主張進行了以下簡單地認定:“子牙公司雖以已有技術進行抗辯,但僅提交一份涉案專利申請日之前實施的《CL結構工程質量驗收標準》,而并非一項完整的現有技術方案。以此主張其不構成侵權的上訴理由,本院不予支持。”隨后,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朝陽興諾公司按照建設部頒發的行業標準設計、施工而實施標準中專利的行為是否構成侵犯專利權問題的函》(一下簡稱“最高法函”)中的相關闡述:“鑒于目前我國標準制定機關尚未建立有關標準中專利信息的公開披露及使用制度的實際情況,專利權人參與了標準的制定或者經其同意,將專利納入國家、行業或者地方標準的,視為專利權人許可他人在實施標準的同時實施該專利,他人的有關實施行為不屬于專利法第十一條所規定的侵犯專利權的行為。”
最后,法官依據以上答復的精神,認為子牙公司的行為不夠成侵權,且判令子牙公司支付使用費。
縱觀以上判決理由的闡述過程,法院對子牙公司“已有技術”的主張不予采納的原因僅僅是機械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三十條的規定:“已有的技術,是指申請日(有優先權的,指優先權日)前在國內外出版物上公開發表、在國內公開適用或者以其他方式為公眾所知的技術”。認為其提交的《CL結構工程質量驗收標準》,并非一項完整的現有技術方案,無法進行對比,卻未對該標準的內容、性質、及將專利納入標準的影響進行分析 。
通過以上案例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形式推理的模式下,判決理由的闡述將產生以下缺陷。
1、無法滿足法律推理的真正要求
法律推理應包含以下兩個因素:
(1)它涉及法律推理實質上的評價性和主觀性。它要考慮到各種裁判結果的社會效果的可接受性,其評價有多種標準,包括正義、常識、公共福利、方便、功利等。
(2)法官做出的判決應當與現有的法律制度必須保持一致性和一貫性。
而在形式推理的適用過程中,要達到以上要求,將會不可避免地遭受以下難題:
(1)“相關性”問題:即在什么法律規則同案件相關的問題上 發生爭論。以上述案件為例,對“已有技術”和“默示許可”的相關規定的選擇及適用理由,并未進行明確的分析和闡述。
(2)法律解釋問題:即法院在法律用語含糊不明而必須在多種解釋中做出選擇的情況。
2、無法保障實質正義的實現。
以《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為例,在不考慮經營者行為對消費者及市場產生的實質影響以及立法的實質目的的情況下,機械適用法條規定,認定經營者將高獎項的產品宣傳成低獎項的產品為虛假宣傳而進行相應制裁,將實質上影響經營者和消費者利益,無法實現法律所追求的真正的正義。
3、無法應對法律漏洞
在形式推理的模式下,法律規定作為推理的前提出現,而當出現法律未規定或規定相矛盾的情況時,法官將無法可依。
(二)實質推理的要求
法律規定、法律事實、推理主體都是包含多種屬性的對立統一體,對于如何從一法律體系中選擇相關的法律規定、如何把客觀事實加工成法律事實,建構一法律理由,如何對眾多的法律理由進行權衡、抉擇,保證做出的判決的合理、有效,不是形式的推理所能解決的問題,其可能是對矛盾的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法律價值權衡的結果,也可能是處于社會政策的考慮,甚至法官的法律信念、判案經驗、道德傾向的影響。
因此,判決理由的闡述不應局限于形式推理的過程,在新《民事訴訟法》的立法要求下,“作出判決的理由”應當具體表現為實質推理的運用和展現。
同時,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民事審判的過程并非僅限于判決書中判決理由所展現出來的形式推理過程。在合議庭筆錄、審判委員會的筆錄中,合議庭、審委會可以表達對案件事實、適用法律規則、不同法律理由及可能判決結果的意見,并相互論辯,最后做出一個多數人認可的判決結果。該過程及實質推理的過程。故判決理由的闡述應更多地包括以上過程的呈現。
實質推理的實現包括對事實認定過程的解釋,其中包括認證規則的適用以及法官自由心證的形成過程;包括法律解釋的過程,體現在多種法律解釋方法的選擇以及其在具體案件中適用的過程;于此同時還需要通過正確運用法律原則、指導性案例及一定的利益衡量彌補法律的漏洞。
在實質推理要求法官更大地發揮其主觀能動性的情況下,法官的裁判仍然受到一定因素的約束。其中包括立法本意、擬制的客觀標準、公平正義和情理、以及公共利益等。
在新《民事訴訟法》對判決理由提出新要求的前提下,上述文章以法律邏輯的視角具體分析了形式推理到實質推理的運用,最后引入哲學詮釋學,試圖跳出原有推理模式從新認識民事裁決的思維過程和判決理由的要求。從形式推理到實質推理,再到詮釋,由于哲學基礎的不同,法官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空間愈加擴大,欲實現的狀況也愈加理想化。判決理由的闡述的新要求,并非只是文字數量上的增加,也非僅僅是理由的細化。對其分析的嘗試旨在探尋在我國現行法律體制下,民事訴訟法關于判決理由的要求究竟能走多遠。參考文獻
[1]亢婷婷;:《民事判決基本模態分析;西南政法大學碩士論文 2008年
篇(6)
“推理公證”是公證思維的特殊形式,它客觀存在于具體的公證實務中。下面就“推理公證”現象,介紹一個實踐中的典型案例:
2005年1月17日,修水籍客運汽車承包人王參國等,從廣東惠州發車運載旅客至修水,途經廣東韶關路段時,客車不幸與其它車輛碰撞,發生車禍,造成乘車的8位旅客不同程度受傷。韶關交警處理事故過程中,將8位受傷旅客送往韶關“鐵路醫院”救治,并作了事故記載。事故第二天,滯留旅客及受傷8位傷員共同乘座修水客車轉送回修水。其中,有4位輕微傷傷員至修水境內時,急著回家過春節,相繼中途下車,未留下聯系地址。另4位傷情較重的傷員即轉入修水大橋鎮、義寧鎮醫院繼續治療,至2005年3月份相繼痊愈出院。2005年4月初,當事人王參國持4位傷員的出院證明到韶關進行事故理賠,被告之要其出示8位傷員治療痊愈的公證證明。而當事人向公證處僅能提供4位較重傷員的痊愈出院的資料,對另外4位輕微傷傷員無法提供出院痊愈材料,人海茫茫,不知他們下落。公證員以“當事人提供什么出什么,自己看到什么出什么”為由,拒絕出具8位傷員痊愈出院的公證。而當事人則再三要求公證證明8位傷員痊愈,可公證員只同意證明4位痊愈,雙方一直爭執不下,為此,公證員將問題提交公證處主任會議研究,修水縣公證處經研究決定:責成公證員對客運車輛駕駛員、售票員和已知出院的4位重傷員及其他知情的車輛股東補充調查,并核實了解其余4位無法查找的輕微傷員當時的傷情及在韶關“鐵路醫院”的治療、檢查記錄。之后,公證員根據當事人提供的材料、調查的證據,綜合推理分析,推定無法查找的4位輕微傷傷員痊愈出院,并制作出具了8位傷員全部痊愈的公證證明法津文書,使當事人9萬余元的車禍損失及時到廣東韶關得到了理賠。
透過上述案例,不難發現,“推理公證”是一種順應社會需要的,體現公證法律價值的實質性公證;是一種公證員運用邏輯思維,進行推理、判斷的職業風險公證。對于“推理公證”的認識,我們不妨作如下幾個方面的探討:
一、推理公證的法理基礎
“推理公證”從理論上分析,它是一種法律上的推理思維;法律推理思維可劃分為形式推理和實質推理。形式推理思維包括歸納推理、演繹推理、類比推理三種不同思維形式;實質推理思維包括辯證推理、辯證邏輯等思維形式。“推理公證”究竟屬于哪一類思維形式呢?首先,“推理公證”表現為執業公證員對已知公證材料的審查,并運用法律職業思維、價值判斷,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性認識過程,因而它屬于法律實質推理的范疇;其次,“推理公證”它又表現為公證員以現有的證據、材料為前提,在當事人舉證不足或舉證困難的情況下,輔以相應的調查核實手段,對已經發生的事情作出事實性判斷和價值評價。它回答的是:過去發生的事件是否客觀存在、合法、公平與正義。因此,“推理公證”的法律推理思維形式應該是:辯證推理和辯證邏輯。
另外,從“推理公證”的法律根據看,法律推理思維離不開法律判斷;而法律判斷是以現行法律為基礎的。因此,“推理公證”也是以現行法律為依托的。這里所講的現行“法律”包括現行的法律原則、法律規范、規章、習慣、政策、道德倫理、公平與正義的法律意識等,它們都是“推理公證”的法律依據。
二、推理公證的證明要求
在司法活動中,按照不同的證據采信制度,有不同的證明標準。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證明須達到法官的確信狀態或者能夠排除一切合理懷疑”;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高度的蓋然性或較高的蓋然性”。公證制度作為一項司法制度,在我國起步較晚,其證據采信規則、證明標準,法律有關規定不是很明確。從公證制度的起源看,它源于大陸法系(即民法法系)的司法制度。大陸法系國家廣泛實行“自由心證”的證據采信規則,其司法活動的證明要求是:“以法律執業者的內心確信”為標準,基本上是依據法律執業者個人的理性思維來判斷。
在“推理公證”中,由于當事人申請的公證事項比較復雜,或存在舉證上的困難,或舉證明顯不足,必須借助執業公證員的輔助調查及法律推理思維活動,才能達到公證的目的。從“推理公證”的結果和過程看,它既類似于民事訴訟的蓋然性(即可能性)證明要求,又類似于大陸法系的“自由心證”制度。所以,“推理公證”的證明要求可以表述為:公證執業人員運用專業知識,按照“自由心證”的規則,對公證事項進行法律推理思維,而得出的較高蓋然性結論。
三、推理公證的法律價值與法律風險
“推理公證”是法律意識、公證觀念發展的產物。在我國公證制度確立初期,人們對公證活動價值的認識是模糊的,一些公證當事人申請辦理公證,尋求的是一種法律上的心理安慰,他們在辦理公證事項的前與后,總是說不清、道不明公證的法律效用與價值。我們且把這類當事人稱之為“模糊公證”當事人。隨著我國公證制度的發展與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公證當事人的法律風險意識、法律價值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些可公證或可不公證的事項,或者沒有法律價值、法律效用的公證,當事人一般是不會辦理的。現在到公證機關辦證的當事人中,辦理“模糊公證”的當事人少了,代之而來的是“風險公證”、“目的公證”當事人。因而對于事實清楚、法律關系簡單明了的事項,如果法律、習慣不是要求應當公證的話,當事人是不會選擇公證的;相反,法律關系復雜,容易引發糾紛;或是舉證不能、事實模糊、易發生法律風險的事項,當事人卻迫切要求尋找公證法律保護,轉嫁法律風險。這就是當前公證當事人的法律價值追求。而“推理公證”正是為了滿足這一法律需求應運而生的。
也許有人認為:從當事人的法律需求看,“推理公證”充滿著法律風險,因怕承擔法律風險,所以不敢或不肯辦理。不錯,“推理公證”存在著一定的法律風險,正因為它有法律上的風險,才體現了它的公證需求價值。試想如果公證機構、公證員,終日固守原來的思維模式不變,無風險的公證社會不需要你辦,而社會需求的公證因有風險你又不敢辦,勢必會使公證的路子越走越窄,公證事業的發展就會徘徊不前。畢竟,公證行業本身就是一個風險行業,公證員承擔的法律風險從公證制度的構建上看,它比法官、律師的執業風險要大得多。因而承擔一定的執業風險是公證制度和公證職業道德對公證員及公證執業機構的基本要求。公證員及公證機構正是利用自身承擔的法律風險為當事人提供有效的公證服務,才顯示出公證本身應有的社會價值。
四、推理公證的適用前提
“推理公證”的有效運用,取決于兩個方面的前提因素:一個是適用的事項條件;二個是公證人員的法律素養。一方面,從公證形式看,“推理公證”一般僅適用于要素式公證,而不適用于定式公證;從公證內容看,“推理公證”適用于當事人對申請事項舉證不足或舉證困難的情況,著重解決公證材料、證據與公證事實之間存在的“內容”與“形式”、“合理”與“合法”之類的矛盾。
另一方面,從公證隊伍執業素質的現狀看,不是所有的公證人員都能夠得心應手地運用“推理公證”,熟練順利地解決公證中的復雜法律問題。因為,“推理公證”是建立在法律執業者的專業思維基礎上的,它要求執業人員有較高的法律素養和法律思維能力。所以,“推理公證”需要一支高素質的公證執業服務隊伍。
五、推理公證對公證活動的影響
篇(7)
【正文】
一、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歷史
計算機先驅思想家萊布尼茲曾這樣不無浪漫地談到推理與計算的關系:“我們要造成這樣一個結果,使所有推理的錯誤都只成為計算的錯誤,這樣,當爭論發生的時候,兩個哲學家同兩個計算家一樣,用不著辯論,只要把筆拿在手里,并且在算盤面前坐下,兩個人面對面地說:讓我們來計算一下吧!”(注:轉引自肖爾茲著:《簡明邏輯史》,張家龍譯,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54頁。)
如果連抽象的哲學推理都能轉變為計算問題來解決,法律推理的定量化也許還要相對簡單一些。盡管理論上的可能性與技術可行性之間依然存在著巨大的鴻溝,但是,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速度確實令人驚嘆。從誕生至今的短短45年內,人工智能從一般問題的研究向特殊領域不斷深入。1956年紐厄爾和西蒙教授的“邏輯理論家”程序,證明了羅素《數學原理》第二章52個定理中的38個定理。塞繆爾的課題組利用對策論和啟發式探索技術開發的具有自學習能力的跳棋程序,在1959年擊敗了其設計者,1962年擊敗了州跳棋冠軍,1997年超級計算機“深藍”使世界頭號國際象棋大師卡斯帕羅夫俯首稱臣。
20世紀6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課題是博弈、難題求解和智能機器人;70年代開始研究自然語言理解和專家系統。1971年費根鮑姆教授等人研制出“化學家系統”之后,“計算機數學家”、“計算機醫生”等系統相繼誕生。在其他領域專家系統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鼓舞下,一些律師提出了研制“法律診斷”系統和律師系統的可能性。(注:SimonChalton,LegalDiagnostics,ComputersandLaw,No.25,August1980.pp.13-15.BryanNiblett,ExpertSystemsforLawyers,ComputersandLaw,No.29,August1981.p.2.)
1970年Buchanan&Headrick發表了《關于人工智能和法律推理若干問題的考察》,一文,拉開了對法律推理進行人工智能研究的序幕。文章認為,理解、模擬法律論證或法律推理,需要在許多知識領域進行艱難的研究。首先要了解如何描述案件、規則和論證等幾種知識類型,即如何描述法律知識,其中處理開放結構的法律概念是主要難題。其次,要了解如何運用各種知識進行推理,包括分別運用規則、判例和假設的推理,以及混合運用規則和判例的推理。再次,要了解審判實踐中法律推理運用的實際過程,如審判程序的運行,規則的適用,事實的辯論等等。最后,如何將它們最終運用于編制能執行法律推理和辯論任務的計算機程序,區別和分析不同的案件,預測并規避對手的辯護策略,建立巧妙的假設等等。(注:Buchanan&Headrick,SomeSpeculationAbout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egalReasoning,23StanfordLawReview(1970).pp.40-62.)法律推理的人工智能研究在這一時期主要沿著兩條途徑前進:一是基于規則模擬歸納推理,70年代初由WalterG.Popp和BernhardSchlink開發了JUDITH律師推理系統。二是模擬法律分析,尋求在模型與以前貯存的基礎數據之間建立實際聯系,并僅依這種關聯的相似性而得出結論。JeffreyMeld-man1977年開發了計算機輔助法律分析系統,它以律師推理為模擬對象,試圖識別與案件事實模型相似的其他案件。考慮到律師分析案件既用歸納推理又用演繹推理,程序對兩者都給予了必要的關注,并且包括了各種水平的分析推理方法。
專家系統在法律中的第一次實際應用,是D.沃特曼和M.皮特森1981年開發的法律判決輔助系統(LDS)。研究者探索將其當作法律適用的實踐工具,對美國民法制度的某個方面進行檢測,運用嚴格責任、相對疏忽和損害賠償等模型,計算出責任案件的賠償價值,并論證了如何模擬法律專家意見的方法論問題。(注:''''ModelsofLegalDecisionmakingReport'''',R-2717-ICJ(1981).)
我國法律專家系統的研制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步。(注:錢學森教授:《論法治系統工程的任務與方法》(《科技管理研究》1981年第4期)、《社會主義和法治學與現代科學技術》(《法制建設》1984年第3期)、《現代科學技術與法和法制建設》(《政法論壇》)1985年第3期)等文章,為我國法律專家系統的研發起了思想解放和理論奠基作用。)1986年由朱華榮、肖開權主持的《量刑綜合平衡與電腦輔助量刑專家系統研究》被確定為國家社科“七五”研究課題,它在建立盜竊罪量刑數學模型方面取得了成果。在法律數據庫開發方面,1993年中山大學學生胡釗、周宗毅、汪宏杰等人合作研制了《LOA律師辦公自動化系統》。(注:楊建廣、駱梅芬編著:《法治系統工程》,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349頁。)1993年武漢大學法學院趙廷光教授主持開發了《實用刑法專家系統》。(注:趙廷光等著:《實用刑法專家系統用戶手冊》,北京新概念軟件研究所1993年版。)它由咨詢檢索系統、輔助定性系統和輔助量刑系統組成,具有檢索刑法知識和對刑事個案進行推理判斷的功能。
專家系統與以往的“通用難題求解”相比具有以下特點:(1)它要解決復雜的實際問題,而不是規則簡單的游戲或數學定理證明問題;(2)它面向更加專門的應用領域,而不是單純的原理性探索;(3)它主要根據具體的問題域,選擇合理的方法來表達和運用特殊的知識,而不強調與問題的特殊性無關的普適性推理和搜索策略。
法律專家系統在法規和判例的輔助檢索方面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解放了律師一部分腦力勞動。但絕大多數專家系統目前只能做法律數據的檢索工作,缺乏應有的推理功能。20世紀90年代以后,人工智能法律系統進入了以知識工程為主要技術手段的開發時期。知識工程是指以知識為處理對象,以能在計算機上表達和運用知識的技術為主要手段,研究知識型系統的設計、構造和維護的一門更加高級的人工智能技術。(注:《中國大百科全書·自動控制與系統工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版,第579頁。)知識工程概念的提出,改變了以往人們認為幾個推理定律再加上強大的計算機就會產生專家功能的信念。以知識工程為技術手段的法律系統研制,如果能在法律知識的獲得、表達和應用等方面獲得突破,將會使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制產生一個質的飛躍。
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發展源于兩種動力。其一是法律實踐自身的要求。隨著社會生活和法律關系的復雜化,法律實踐需要新的思維工具,否則,法律家(律師、檢察官和法官)將無法承受法律文獻日積月累和法律案件不斷增多的重負。其二是人工智能發展的需要。人工智能以模擬人的全部思維活動為目標,但又必須以具體思維活動一城一池的攻克為過程。它需要通過對不同思維領域的征服,來證明知識的每個領域都可以精確描述并制造出類似人類智能的機器。此外,人工智能選擇法律領域尋求突破,還有下述原因:(1)盡管法律推理十分復雜,但它有相對穩定的對象(案件)、相對明確的前提(法律規則、法律事實)及嚴格的程序規則,且須得出確定的判決結論。這為人工智能模擬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2)法律推理特別是抗辯制審判中的司法推理,以明確的規則、理性的標準、充分的辯論,為觀察思維活動的軌跡提供了可以記錄和回放的樣本。(3)法律知識長期的積累、完備的檔案,為模擬法律知識的獲得、表達和應用提供了豐富、準確的資料。(4)法律活動所特有的自我意識、自我批評精神,對法律程序和假設進行檢驗的傳統,為模擬法律推理提供了良好的反思條件。
二、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價值
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制對法學理論和法律實踐的價值和意義,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是方法論啟示。P.Wahlgren說:“人工智能方法的研究可以支持和深化在創造性方法上的法理學反思。這個信仰反映了法理學可以被視為旨在于開發法律分析和法律推理之方法的活動。從法理學的觀點看,這種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揭示方法論的潛在作用,從而有助于開展從法理學觀點所提出的解決方法的討論,而不僅僅是探討與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有關的非常細致的技術方面。”(注:P.Wahlgren,AutomationofLegalReasoning:AStudy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ComputerLawSeries11.KluwerLawandTaxationPublishers.DeventerBoston1992.Chapter7.)在模擬法律推理的過程中,法學家通過與工人智能專家的密切合作,可以從其對法律推理的獨特理解中獲得有關方法論方面的啟示。例如,由于很少有兩個案件完全相似,在判例法實踐中,總有某些不相似的方面需要法律家運用假設來分析已有判例與現實案件的相關性程度。但法學家們在假設的性質問題上常常莫衷一是。然而HYPO的設計者,在無真實判例或真實判例不能充分解釋現實案件的情況下,以假設的反例來反駁對方的觀點,用補充、刪減和改變事實的機械論方法來生成假設。這種用人工智能方法來處理假設的辦法,就使復雜問題變得十分簡單:假設實際上是一個新的論證產生于一個經過修正的老的論證的過程。總之,人工智能方法可以幫助法學家跳出法理學方法的思維定勢,用其他學科的方法來重新審視法學問題,從而為法律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的途徑。
二是提供了思想實驗手段。西蒙認為,盡管我們還不知道思維在頭腦中是怎樣由生理作用完成的,“但我們知道這些處理在數字電子計算機中是由電子作用完成的。給計算機編程序使之思維,已經證明有可能為思維提供機械論解釋”。(注:轉引自童天湘:《人工智能與第N代計算機》,載《哲學研究》1985年第5期。)童天湘先生認為:“通過編制有關思維活動的程序,就會加深對思維活動具體細節的了解,并將這種程序送進計算機運行,檢驗其正確性。這是一種思想實驗,有助于我們研究人腦思維的機理。”(注:轉引自童天湘:《人工智能與第N代計算機》,載《哲學研究》1985年第5期。)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研究的直接目標是使計算機能夠獲取、表達和應用法律知識,軟件工程師為模擬法律推理而編制程序,必須先對人的推理過程作出基于人工智能理論和方法的獨特解釋。人工智能以功能模擬開路,在未搞清法律家的推理結構之前,首先從功能上對法律證成、法律檢索、法律解釋、法律適用等法律推理的要素和活動進行數理分析,將法理學、訴訟法學關于法律推理的研究成果模型化,以實現法律推理知識的機器表達或再現,從而為認識法律推理的過程和規律提供了一種實驗手段。法學家則可以將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推理過程、方法和結論與人類法律推理活動相對照,為法律推理的法理學研究所借鑒。因此,用人工智能方法模擬法律推理,深化了人們對法律推理性質、要素和過程的認識,使法學家得以借助人工智能科學的敏銳透鏡去考察法律推理的微觀機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BryanNiblett教授說:“一個成功的專家系統很可能比其他的途徑對法理學作出更多的(理論)貢獻。”(注:BryanNiblett,ExpertSystemsforLawyers,ComputersandLaw,No.29,August1981.note14,p.3.)
三是輔助司法審判。按照格雷的觀點,法律專家系統首先在英美判例法國家出現的直接原因在于,浩如煙海的判例案卷如果沒有計算機編纂、分類、查詢,這種法律制度簡直就無法運轉了。(注:PamelaN.GrayBrookfield,ArtificialLegalIntelligence,VT:DartmouthPublishingCo.,1997.p.402.)其實不僅是判例法,制定法制度下的律師和法官往往也要為檢索有關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耗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而且由于人腦的知識和記憶能力有限,還存在著檢索不全面、記憶不準確的問題。人工智能法律系統強大的記憶和檢索功能,可以彌補人類智能的某些局限性,幫助律師和法官從事相對簡單的法律檢索工作,從而極大地解放律師和法官的腦力勞動,使其能夠集中精力從事更加復雜的法律推理活動。
四是促進司法公正。司法推理雖有統一的法律標準,但法官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差異個體,所以在執行統一標準時會產生一些差異的結果。司法解釋所具有的建構性、辯證性和創造性的特點,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差異。如果換了鋼鐵之軀的機器,這種由主觀原因所造成的差異性就有可能加以避免。這當然不是說讓計算機完全取代法官,而是說,由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為司法審判提供了相對統一的推理標準和評價標準,從而可以輔助法官取得具有一貫性的判決。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鋼鐵之軀的機器沒有物質欲望和感情生活,可以比人更少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擾。正像計算機錄取增強了高考招生的公正性、電子監視器提高了糾正行車違章的公正性一樣,智能法律系統在庭審中的運用有可能減少某些現象。
五是輔助法律教育和培訓。人工智能法律系統凝聚了法律家的專門知識和法官群體的審判經驗,如果通過軟件系統或計算機網絡實現專家經驗和知識的共享,便可在法律教育和培訓中發揮多方面的作用。例如,(1)在法學院教學中發揮模擬法庭的作用,可以幫助法律專業學生鞏固自己所學知識,并將法律知識應用于模擬的審判實踐,從而較快地提高解決法律實踐問題的能力。(2)幫助新律師和新法官全面掌握法律知識,迅速獲得判案經驗,在審判過程的跟蹤檢測和判決結論的動態校正中增長知識和才干,較快地接近或達到專家水平。(3)可使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律師和法官及時獲得有關法律問題的咨詢建議,彌補因知識結構差異和判案經驗多寡而可能出現的失誤。(4)可以為大眾提供及時的法律咨詢,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法律素質,增強法律意識。
六是輔助立法活動。人工智能法律系統不僅對輔助司法審判有重要的意義,而且對完善立法也具有實用價值。(注:EdwinaL.Rissl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SteppingStonestoaModelofLegalReasoning,TheYaleLawJournal.(Vol.99:1957-1981).)例如,倫敦大學Imperial學院的邏輯程序組將1981年英國國籍法的內容形式化,幫助立法者發現了該法在預見性上存在的一些缺陷和法律漏洞。(注:EdwinaL.Rissl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SteppingStonestoaModelofLegalReasoning,TheYaleLawJournal.(Vol.99:1957-1981).)立法輔助系統如能應用于法律起草和法律草案的審議過程,有可能事先發現一些立法漏洞,避免一個法律內部各種規則之間以及新法律與現有法律制度之間的相互沖突。
三、法理學在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研究中的作用
1.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法理學思想來源
關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統之法理學思想來源的追蹤,不是對法理學與人工智能的聯系作面面俱到的考察,而旨在揭示法理學對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發展所產生的一些直接影響。
第一,法律形式主義為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產生奠定了理論基礎。18-19世紀的法律形式主義強調法律推理的形式方面,認為將法律化成簡單的幾何公式是完全可能的。這種以J·奧斯汀為代表的英國分析法學的傳統,主張“法律推理應該依據客觀事實、明確的規則以及邏輯去解決一切為法律所要求的具體行為。假如法律能如此運作,那么無論誰作裁決,法律推理都會導向同樣的裁決。”(注:(美)史蒂文·J·伯頓著:《法律和法律推理導論》,張志銘、解興權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頁。)換言之,機器只要遵守法律推理的邏輯,也可以得出和法官一樣的判決結果。在分析法學家看來,“所謂‘法治’就是要求結論必須是大前提與小前提邏輯必然結果。”(注:朱景文主編:《對西方法律傳統的挑戰》,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92頁。)如果法官違反三段論推理的邏輯,就會破壞法治。這種機械論的法律推理觀,反映了分析法學要求法官不以個人價值觀干擾法律推理活動的主張。但是,它同時具有忽視法官主觀能動性和法律推理靈活性的僵化的缺陷。所以,自由法學家比埃利希將法律形式主義的邏輯推理說稱為“自動售貨機”理論。然而,從人工智能就是為思維提供機械論解釋的意義上說,法律形式主義對法律推理所作的機械論解釋,恰恰為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開發提供了可能的前提。從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研制的實際過程來看,在其起步階段,人工智能專家正是根據法律形式主義所提供的理論前提,首先選擇三段論演繹推理進行模擬,由WalterG.Popp和BernhardSchlink在20世紀70年代初開發了JUDITH律師推理系統。在這個系統中,作為推理大小前提的法律和事實之間的邏輯關系,被計算機以“如果A和B,那么C”的方式加以描述,使機器法律推理第一次從理論變為現實。
第二,法律現實主義推動智能模擬深入到主體的思維結構領域。法律形式主義忽視了推理主體的社會性。法官是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人,其所從事的法律活動不可能不受到其社會體驗和思維結構的影響。法官在實際的審判實踐中,并不是機械地遵循規則,特別是在遇到復雜案件時,往往需要作出某種價值選擇。而一旦面對價值問題,法律形式主義的邏輯決定論便立刻陷入困境,顯出其僵化性的致命弱點。法律現實主義對其僵化性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霍姆斯法官明確提出“法律的生命并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注:(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鄧正來、姬敬武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478頁。)的格言。這里所謂邏輯,就是指法律形式主義的三段論演繹邏輯;所謂經驗,則包括一定的道德和政治理論、公共政策及直覺知識,甚至法官的偏見。法律現實主義對法官主觀能動性和法律推理靈活性的強調,促使人工智能研究從模擬法律推理的外在邏輯形式進一步轉向探求法官的內在思維結構。人們開始考慮,如果思維結構對法官的推理活動具有定向作用,那么,人工智能法律系統若要達到法官水平,就應該通過建立思維結構模型來設計機器的運行結構。TAXMAN的設計就借鑒了這一思想,法律知識被計算機結構語言以語義網絡的方式組成不同的規則系統,解釋程序、協調程序、說明程序分別對網絡結構中的輸入和輸出信息進行動態結構調整,從而適應了知識整合的需要。大規模知識系統的KBS(KnowledgeBasedSystem)開發也注意了思維結構的整合作用,許多具有內在聯系的小規模KBS子系統,在分別模擬法律推理要素功能(證成、法律查詢、法律解釋、法律適用、法律評價、理由闡述)的基礎上,又通過聯想程序被有機聯系起來,構成了具有法律推理整體功能的概念模型。(注:P.Wahlgren,AutomationofLegalReasoning:AStudy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ComputerLawSeries11.KluwerLawandTaxationPublishers.DeventerBoston1992.Chapter7.)
第三,“開放結構”的法律概念打開了疑難案件法律推理模擬的思路。法律形式主義忽視了疑難案件的存在。疑難案件的特征表現為法律規則和案件之間不存在單一的邏輯對應關系。有時候從一個法律規則可以推出幾種不同的結論,它們往往沒有明顯的對錯之分;有時一個案件面對著幾個相似的法律規則。在這些情況下,形式主義推理說都一籌莫展。但是,法律現實主義在批判法律形式主義時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它否認具有普遍性的一般法律規則的存在,試圖用“行動中的法律”完全代替分析法學“本本中的法律”。這種矯枉過正的做法雖然是使法律推理擺脫機械論束縛所走出的必要一步,然而,法律如果真像現實主義法學所說的那樣僅僅存在于具體判決之中,法律推理如果可以不遵循任何標準或因人而異,那么,受到挑戰的就不僅是法律形式主義,而且還會殃及法治要求實現規則統治之根本原則,并動搖人工智能法律系統存在的基礎。哈特在法律形式主義和法律現實主義的爭論中采取了一種折中立場,他既承認邏輯的局限性又強調其重要性;既拒斥法官完全按自己的預感來隨意判案的見解,又承認直覺的存在。這種折中立場在哈特“開放結構”的法律概念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法律概念既有“意義核心”又有“開放結構”,邏輯推理可以幫助法官發現問題的陽面,而根據社會政策、價值和后果對規則進行解釋則有助于發現問題的陰面。開放結構的法律概念,使基于規則的法律推理模擬在受到概念封閉性的限制而對疑難案件無能為力時,找到了新的立足點。在此基礎上,運用開放結構概念的疑難案件法律推理模型,通過邏輯程序工具和聯想技術而建立起來。Gardner博士就疑難案件提出兩種解決策略:一是將簡易問題從疑難問題中篩選出來,運用基于規則的技術來解決;二是將疑難問題同“開放結構”的法律概念聯系在一起,先用非范例知識如規則、控辯雙方的陳述、常識來獲得初步答案,再運用范例來澄清案件、檢查答案的正確性。
第四,目的法學促進了價值推理的人工智能研究。目的法學是指一種所謂直接實現目的之“后法治”理想。美國法學家諾內特和塞爾茲尼克把法律分為三種類型。他們認為,以法治為標志的自治型法,過分強調手段或程序的正當性,有把手段當作目的的傾向。這說明法治社會并沒有反映人類關于美好社會的最高理想,因為實質正義不是經過人們直接追求而實現的,而是通過追求形式正義而間接獲得的。因此他們提出以回應型法取代自治型法的主張。在回應型法中,“目的為評判既定的做法設立了標準,從而也就開辟了變化的途徑。同時,如果認真地對待目的,它們就能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從而減輕制度屈從的危險。反之,缺少目的既是僵硬的根源,又是機會主義的根源。”(注:(美)諾內特、塞爾茲尼克著:《轉變中的法律與社會》,張志銘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頁。)美國批判法學家昂格爾對形式主義法律推理和目的型法律推理的特點進行了比較,他認為,前者要求使用內容明確、固定的規則,無視社會現實生活中不同價值觀念的沖突,不能適應復雜情況和變化,追求形式正義;后者則要求放松對法律推理標準的嚴格限制,允許使用無固定內容的抽象標準,迫使人們在不同的價值觀念之間做出選擇,追求實質正義。與此相應,佩雷爾曼提出了新修辭學(NewRhetoric)的法律理論。他認為,形式邏輯只是根據演繹法或歸納法對問題加以說明或論證的技術,屬于手段的邏輯;新修辭學要填補形式邏輯的不足,是關于目的的辯證邏輯,可以幫助法官論證其決定和選擇,因而是進行價值判斷的邏輯。他認為,在司法三段論思想支配下,法學的任務是將全部法律系統化并作為闡釋法律的大前提,“明確性、一致性和完備性”就成為對法律的三個要求。而新修辭學的基本思想是價值判斷的多元論,法官必須在某種價值判斷的指示下履行義務,必須考慮哪些價值是“合理的、可接受的、社會上有效的公平的”。這些價值構成了判決的正當理由。(注:沈宗靈著:《現代西方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43-446頁。)制造人工智能法律系統最終需要解決價值推理的模擬問題,否則,就難以實現為判決提供正當理由的要求。為此,P.Wahlgren提出的與人工智能相關的5種知識表達途徑中,明確地包括了以道義為基礎的法律推理模型。(注:P.Wahlgren,AutomationofLegalReasoning:AStudy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ComputerLawSeries11.KluwerLawandTaxationPublishers.DeventerBoston1992.Chapter7.)引入道義邏輯,或者說在機器中采用基于某種道義邏輯的推理程序,強調目的價值,也許是制造智能法律系統的關鍵。不過,即使把道義邏輯硬塞給計算機,鋼鐵之軀的機器沒有生理需要,也很難產生價值觀念和主觀體驗,沒辦法解決主觀選擇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波斯納曾以法律家有七情六欲為由對法律家對法律的機械忠誠表示了強烈懷疑,并辯證地將其視為法律發展的動力之一。只有人才能夠平衡相互沖突的利益,能夠發現對人類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的價值。因此,關于價值推理的人工智能模擬究竟能取得什么成果,恐怕還是個未知數。
2.法理學對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研制的理論指導作用
GoldandSusskind指出:“不爭的事實是,所有的專家系統必須適應一些法理學理論,因為一切法律專家系統都需要提出關于法律和法律推理性質的假設。從更嚴格的意義上說,一切專家系統都必須體現一種結構理論和法律的個性,一種法律規范理論,一種描述法律科學的理論,一種法律推理理論”。(注:GoldandSusskind,ExpertSystemsinLaw:AJurisprudentialandFormalSpecificationApproach,pp.307-309.)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究,不僅需要以法理學關于法律的一般理論為知識基礎,還需要從法理學獲得關于法律推理的完整理論,如法律推理實踐和理論的發展歷史,法律推理的標準、主體、過程、方法等等。人工智能對法律推理的模擬,主要是對法理學關于法律推理的知識進行人工智能方法的描述,建立數學模型并編制計算機應用程序,從而在智能機器上再現人類法律推理功能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工智能專家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如何吸收法理學關于法律推理的研究成果,包括法理學關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究成果。
隨著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研究從低級向高級目標的推進,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對法律推理的微觀機制認識不足已成為人工智能模擬的嚴重障礙。P.Wahlgren指出,“許多人工智能技術在法律領域的開發項目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許多潛在的法理學原則沒有在系統開發的開始階段被遵守或給予有效的注意。”“法理學對法律推理和方法論問題的關注已經有幾百年,而人工智能的誕生只是本世紀50年代中期的事情,這個事實是人工智能通過考察法理學知識來豐富自己的一個有效動機。”(注:P.Wahlgren,AutomationofLegalReasoning:AStudy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ComputerLawSeries11.KluwerLawandTaxationPublishers.DeventerBoston1992.Chapter7.)因此,研究法律推理自動化的目標,“一方面是用人工智能(通過把計算機的應用與分析模型相結合)來支撐法律推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應用法理學理論來解決作為法律推理支撐系統的以及一般的人工智能問題。”(注:P.Wahlgren,AutomationofLegalReasoning:AStudy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ComputerLawSeries11.KluwerLawandTaxationPublishers.DeventerBoston1992.Chapter7.)在前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法律系統充當法律推理研究的思想實驗手段以及輔助司法審判的問題。后一方面,則是法律推理的法律學研究成果直接為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制所應用的問題。例如,20世紀70年代法理學在真實和假設案例的推理和分析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已為幾種人工智能法律裝置借鑒而成為其設計工作的理論基礎。在運用模糊或開放結構概念的法律推理研究方面,以及在法庭辯論和法律解釋的形式化等問題上,法理學的研究成果也已為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究所借鑒。
四、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研究的難點
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究盡管在很短的時間內取得了許多令人振奮的成果,但它的發展也面臨著許多困難。這些困難構成了研究工作需要進一步努力奮斗的目標。
第一,關于法律解釋的模擬。在法理學的諸多研究成果中,法律解釋的研究對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制起著關鍵作用。法律知識表達的核心問題是法律解釋。法律規范在一個法律論點上的效力,是由法律家按忠實原意和適合當時案件的原則通過法律解釋予以確認的,其中包含著人類特有的價值和目的考慮,反映了法律家的知識表達具有主觀能動性。所以,德沃金將解釋過程看作是一種結合了法律知識、時代信息和思維方法而形成的,能夠應變的思維策略。(注:Dworkin,TakingRightsSeriously,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7.p.75.)目前的法律專家系統并未以知識表達為目的來解釋法律,而是將法律整齊地“碼放”在計算機記憶系統中僅供一般檢索之用。然而,在法律知識工程系統中,法律知識必須被解釋,以滿足自動推理對法律知識進行重新建構的需要。麥卡錫說:“在開發智能信息系統的過程中,最關鍵的任務既不是文件的重建也不是專家意見的重建,而是建立有關法律領域的概念模型。”(注:McCarty,Intelligentlegalinformationsystems:problemsandprospects,op.cit.supra,note25,p.126.)建立法律概念模型必須以法律家對某一法律概念的共識為基礎,但不同的法律家對同一法律概念往往有不同的解釋策略。凱爾森甚至說:即使在國內法領域也難以形成一個“能夠用來敘述一定法律共同體的實在法的基本概念”。(注:(奧)凱爾森著:《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盡管如此,法理學還是為法律概念模型的重建提供了一些方法。例如,德沃金認為,法官在“解釋”階段,要通過推理論證,為自己在“前解釋”階段所確定的大多數法官對模糊法律規范的“一致看法”提供“一些總的理由”。獲取這些總的理由的過程分為兩個步驟:首先,從現存的明確法律制度中抽象出一般的法律原則,用自我建立的一般法律理論來證明這種法律原則是其中的一部分,證明現存的明確法律制度是正當的。其次,再以法律原則為依據反向推出具體的法律結論,即用一般法律理論來證明某一法律原則存在的合理性,再用該法律原則來解釋某一法律概念。TAXMAN等系統裝置已吸收了這種方法,法律知識被計算機結構語言以語義網絡的方式組成不同的規則系統,解釋程序使計算機根據案件事實來執行某條法律規則,并在新案件事實輸入時對法律規則作出新的解釋后才加以調用。不過,法律知識表達的進展還依賴于法律解釋研究取得更多的突破。
第二,關于啟發式程序。目前的法律專家系統如果不能與啟發式程序接口,不能運用判斷性知識進行推理,只通過規則反饋來提供簡單解釋,就談不上真正的智能性。啟發式程序要解決智能機器如何模擬法律家推理的直覺性、經驗性以及推理結果的不確定性等問題,即人可以有效地處理錯誤的或不完全的數據,在必要時作出猜測和假設,從而使問題的解決具有靈活性。在這方面,Gardner的混合推理模型,EdwinaL.Rissland運用聯想程序對規則和判例推理的結果作集合處理的思路,以及Massachusetts大學研制的CABARET(基于判例的推理工具),在將啟發式程序應用于系統開發方面都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但是,法律問題往往沒有唯一正確的答案,這是人工智能模擬法律推理的一個難題。選擇哪一個答案,往往取決于法律推理的目的標準和推理主體的立場和價值觀念。但智能機器沒有自己的目的、利益和立場。這似乎從某種程度上劃定了機器法律推理所能解決問題的范圍。
第三,關于法律自然語言理解。在設計基于規則的程序時,設計者必須假定整套規則沒有意義不明和沖突,程序必須消滅這些問題而使規則呈現出更多的一致性。就是說,盡管人們對法律概念的含義可以爭論不休,但輸入機器的法律語言卻不能互相矛盾。機器語言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LDS基于規則來模擬嚴格責任并計算實際損害時,表現出的最大弱點就是不能使用不精確的自然語言進行推理。然而,在實際的法律推理過程中,法律家對某個問題的任何一種回答都可根據上下文關系作多種解釋,而且辯論雙方總是尋求得出不同的結論。因此,智能法律專家系統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于自然語言理解研究工作的突破。牛津大學的一個程序組正在研究法律自然語言的理解問題,但是遇到了重重困難。原因是連法學家們自己目前也還沒有建立起一套大家一致同意的專業術語規范。所以EdwinaL.Rissland認為,常識知識、意圖和信仰類知識的模擬化,以及自然語言理解的模擬問題,迄今為止可能是人工智能面臨的最困難的任務。對于語言模擬來說,像交際短語和短語概括的有限能力可能會在較窄的語境條件下取得成果,完全的功能模擬、一般“解決問題”能力的模擬則距離非常遙遠,而像書面上訴意見的理解則是永遠的終極幻想。(注:EdwinaL.Rissl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SteppingStonestoaModelofLegalReasoning,TheYaleLawJournal.(Vol.99:1957-1981).)
五、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開發策略和應用前景
我們能夠制造出一臺什么樣的機器,可以證明它是人工智能法律系統?從檢驗標準上看,這主要是法律知識在機器中再現的判定問題。根據“圖靈試驗”原理,我們可將該檢驗標準概括如下:設兩間隔開的屋子,一間坐著一位法律家,另一間“坐著”一臺智能機器。一個人(也是法律家)向法律家和機器提出同樣的法律問題,如果提問者不能從二者的回答中區分出誰是法律家、誰是機器,就不能懷疑機器具有法律知識表達的能力。
依“圖靈試驗”制定的智能法律系統檢驗標準,所看重的是功能。只要機器和法律家解決同樣法律問題時所表現出來的功能相同,就不再苛求哪個是鋼鐵結構、哪個是血肉之軀。人工智能立足的基礎,就是相同的功能可以通過不同的結構來實現之功能模擬理論。
從功能模擬的觀點來確定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究與開發策略,可作以下考慮:
第一,擴大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發主體。現有人工法律系統的幼稚,暴露了僅僅依靠計算機和知識工程專家從事系統研發工作的局限性。因此,應該確立以法律家、邏輯學家和計算機專家三結合的研發群體。在系統研發初期,可組成由法學家、邏輯與認知專家、計算機和知識工程專家為主體的課題組,制定系統研發的整體戰略和分階段實施的研發規劃。在系統研發中期,應通過網絡等手段充分吸收初級產品用戶(律師、檢察官、法官)的意見,使研發工作在理論研究與實際應用之間形成反饋,將開發精英與廣大用戶的智慧結合起來,互相啟發、群策群力,推動系統迅速升級。
第二,確定研究與應用相結合、以應用為主導的研發策略。目前國外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實驗室領域,還沒有在司法實踐中加以應用。但是,任何智能系統包括相對簡單的軟件系統,如果不經過用戶的長期使用和反饋,是永遠也不可能走向成熟的。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如果不能將初期研究成果盡快地轉化為產品,我們也難以為后續研究工作提供雄厚的資金支持。因此,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究必須走產研結合的道路,堅持以應用開路,使智能法律系統盡快走出實驗室,同時以研究為先導,促進不斷更新升級。
第三,系統研發目標與初級產品功能定位。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發目標是制造出能夠滿足多用戶(律師、檢察官、法官、立法者、法學家)多種需要的機型。初級產品的定位應考慮到,人的推理功能特別是價值推理的功能遠遠超過機器,但人的記憶功能、檢索速度和準確性又遠不如機器。同時還應該考慮到,我國目前有12萬律師,23萬檢察官和21萬法官,每年1.2萬法學院本科畢業生,他們對法律知識的獲取、表達和應用能力參差不齊。因此,初級產品的標準可適當降低,先研制推理功能薄弱、檢索功能強大的法律專家系統。可與計算機廠商合作生產具有強大數據庫功能的硬件,并確保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判例的網上及時更新;同時編制以案件為引導的高速檢索軟件。系統開發的先期目標應確定為:(1)替律師起草僅供參考的書和辯護詞;(2)替法官起草僅供參考的判決書;(3)為法學院學生提供模擬法庭審判的通用系統軟件,以輔助學生在、辯護和審判等訴訟的不同階段鞏固所學知識、獲得審判經驗。上述軟件旨在提供一個初級平臺,先解決有無和急需,再不斷收集用戶反饋意見,逐步改進完善。
第四,實驗室研發應確定較高的起點或跟蹤戰略。國外以知識工程為主要技術手段的人工智能法律系統開發已經歷了如下發展階段:(1)主要適用于簡單案件的規則推理;(2)運用開放結構概念的推理;(3)運用判例和假設的推理;(4)運用規則和判例的混合推理。我們如確定以簡單案件的規則推理為初級市場產品,那么,實驗室中第二代產品開發就應瞄準運用開放結構概念的推理。同時,跟蹤運用假設的推理及混合推理,吸收國外先進的KBS和HYPO的設計思想,將功能子系統開發與聯想式控制系統結合。HYPO判例法推理智能裝置具有如下功能:(1)評價相關判例;(2)判定何方使用判例更加貼切;(3)分析并區分判例;(4)建立假設并用假設來推理;(5)為一種主張引用各種類型的反例;(6)建立判例的引證概要。HYPO以商業秘密法的判例推理為模擬對象,假設了完全自動化的法律推理過程中全部要素被建立起來的途徑。值得注意的是,HYPO忽略了許多要素的存在,如商業秘密法背后的政策考慮,法律概念應用于實際情況時固有的模糊性,信息是否已被公開,被告是否使用了對方設計的產品,是否簽署了讓與協議,等等。一個系統設計的要素列表無論多長,好律師也總能再多想出一些。同樣,律師對案件的分析,不可能僅限于商業秘密法判例,還可能援引侵權法或專利法的判例,這決定了緣由的多種可能性。Ashley還討論了判例法推理模擬的其他困難:判例并不是概念的肯定的或否定的樣本,因此,要通過要素等簡單的法律術語使模糊的法律規則得到澄清十分困難,法律原則和類推推理之間的關系還不能以令人滿意的方式加以描述。(注:EdwinaL.Rissl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SteppingStonestoaModelofLegalReasoning,TheYaleLawJournal.(Vol.99:1957-1981).)這說明,即使具有較高起點的實驗室基礎研究,也不宜確定過高的目標。因為,智能法律系統的研究不能脫離人工智能的整體發展水平。
第五,人-機系統解決方案。人和機器在解決法律問題時各有所長。人的優點是能作價值推理,使法律問題的解決適應社會的變化發展,從而具有靈活性。機器的長處是記憶和檢索功能強,可以使法律問題的解決具有一貫性。人-機系統解決方案立足于人與機器的功能互補,目的是解放人的腦力勞動,服務于國家的法治建設。該方案的實施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人為主,機器為人收集信息并作初步分析,提供決策參考。律師受理案件后,可以先用機器處理大批數據,并參考機器的和辯護方案,再做更加高級的推理論證工作。法官接觸一個新案件,或新法官剛接觸審判工作,也可以先看看“機器法官”的判決建議或者審判思路,作為參考。法院的監督部門可參照機器法官的判決,對法官的審判活動進行某種監督,如二者的判決結果差別太大,可以審查一下法官的判決理由。這也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司法腐敗。在人-機系統開發的第二階段,會有越來越多的簡單案件的判決與電腦推理結果完全相同,因此,某些簡單案件可以機器為主進行審判,例如,美國小額法庭的一些案件,我國法庭可用簡易程序來審理的一些案件。法官可以作為“產品檢驗員”監督和修訂機器的判決結果。這樣,法官的判案效率將大大提高,法官隊伍也可借此“消腫”,有可能大幅度提高法官薪水,吸引高素質法律人才進入法官隊伍。
篇(8)
司法理性既表現為一種法律適用中的形式理性,同時也包含著實質理性。司法理性,從外部視角看,在形式上體現為司法者運用程序技術進行推理和論證的技能,如關于程序、證據、推理、解釋的技能。司法理性以司法的程序為依托,借助于司法的程序技術得到表達,是在程序中通過程序技術發展起來的。從這一點上看,英國的柯克大法官將其視為“技藝理性”,很恰當地凸顯出司法理性的形式特點。但司法理性并不等同于程序技術,隱含在程序技術背后的則是一種道德視角,是以程序技術為依托和表達形式的由司法職業特有的實踐態度、思維方式、價值取向以及職業經驗等因素綜合構成的、對司法者的判斷和推理產生指引和控制作用的內在視角,是司法者行為選擇的自我調節和自我控制機制,是對各種價值、原則、政策進行綜合平衡和擇優選擇的結果。這種特殊的內在視角是由一系列基本的理念所支撐的,如獨立自主的精神、作為正義守護者的使命感、法律家的思維方式等等。一個充分體現司法理性的司法過程既包含了司法官對法律條文形式上的遵守,又包含了司法官以其睿智解讀所形成的法律條文、法律規范、法律理論的邏輯正當性。換言之,司法官在司法過程中并不以表面化的法律形式為限,更強調對法的實質性內涵的遵從,只不過這種遵從是通過一種正當化的形式所展現出來而已。
司法形式理性是程序性的理性,首先要求法官具有通過程序進行思考,在平等聽取雙方當事人對立意見的前提下進行判斷、在對話和論辯的基礎上形成結論的職業習慣和程序倫理。其次要求法官嚴格遵循邏輯原則謹慎地運用各種法律推理方法來保證司法裁判結論的確定性和妥當性。在我國法學界,形式理性不僅備受關注,而且被賦予很高的地位。在法哲學研究領域,有的學者認為法律形式合理化是“以法治現代化為關鍵性變相的法制現代化”的判定標準之一。③這是因為我國是成文法制國家,司法過程具有強烈的形式主義和程式化色彩,程序正義乃司法的核心價值,司法的實質價值包容于其形式價值之中,并通過形式正義體現出來。但在司法過程中,一個被高度認同的司法裁判除卻形式符合邏輯外,還有該裁判對公平、正義、善良等法律價值的實現程度。單純的形式理性并不是實現公正裁判的充要條件,在司法實踐中也出現了嚴格遵守推理的形式要求,做出的裁決卻背離法律的一般價值要求司法理性是與法官的自主判斷和選擇聯系在一起的,并體現在法律規范與案件事實之間的這種互動關系之中。司法過程實際上是法官能動地運用理性,妥善地將抽象的法律規范與具體的案件事實進行溝通和對接,在具體的個案處理中實現司法實質理性,進而實現司法公正的過程。
司法理性在本質上又是一種實踐理性,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司法理性的存在是基于司法實踐客觀存在的制度性事實,法官面對的是各種活生生的社會現實,他要做的就是運用理性解決這些現實發生的社會矛盾。法官的司法實踐解決的都是活生生的社會問題。其次,法官的司法理性只能通過司法實踐才能得以表現出來。審判當中法官運用的方法更多的是實踐的方法,而非單純的科學方法。再次,司法理性與實踐的作用是反復和循環的。理性的獲取、提升和實現都離不開實踐活動,理性反過來對實踐的方法和方式產生影響,司法實踐對于司法理性來說是決定性的。從法官的角度來看,即使最簡單的案件也絕不是“1+1=2”的過程。法官的經驗在司法理性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法官在處理具體案件時所練就的一些技藝,包括駕馭庭審、參與調查、展開詢問、主持調解、撰寫判決等,在法庭之外是無法達致的。這些技藝因人而異,各有千秋,充分體現了司法理性的實踐性特點。④
二、法律推理中的司法理性
法官在司法過程中通過法律推理來進行論證說理,在多種相互競爭的論據和理由之間進行權衡和取舍并獲得最佳選擇的過程,也是彰顯司法理性的過程。法律推理首先體現了司法形式理性。在我國,“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由法官獨立審判案件”等正是將待決案件事實置于法律規范構成要件之下,以獲得特定判決的一種邏輯思維過程,也就是以法律規范為大前提、案件事實為小前提、最后得出判決結果的推理過程。這一法律推理所反映的基本思維模式就是司法三段論,它是“一種利用演繹推理中的涵攝特點把法律作為大前提,事實作為小前提,法官根據大前提與小前提之間的邏輯涵攝關系進行的推理。”⑤這種演繹推理所體現的司法形式理性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法律本身是人們理性思維的產物,理性思維無法脫離邏輯思維而存在,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成文法國家,法律制度以條文的形式體現出來,要把這些抽象的條文和紛繁復雜的具體案件事實加以對應起來,通過邏輯演繹方式進行形式論證是至為有效的。在法律形式主義看來,司法三段論是以邏輯為基礎而建構起來的,邏輯是司法三段論的重要工具,它對于實現司法裁判的確定性、一致性和可預測性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因此,建立在邏輯基礎之上的司法三段論裁判模式是一種最基本的裁判模式。在此種裁判模式下,法官進行法律推理的過程在嚴格的訴訟程序中展開,是一種嚴密的邏輯思維活動,具有規范性和公開性的特點,體現了形式理性的基本要求。此外,法律推理的邏輯性質還意味著“平等而無偏見地對待每一個社會成員”、“同類案件相同處理”,因此三段論模式在形式上的特點即意味著平等無偏見地實施公開的規則,從而盡力保證了法律規范與司法判決的一致性。這種推理至少從外在形式上告訴人們法官的判決是符合大眾的一般認識規律的,判決給出的結論不是某一位法官的個人認識與選擇的結果,而僅僅是規則,事實以及規則與事實二者勾連起來后邏輯運行的結果。如果把司法三段論看作是一種程式,則形式理性就意味著對這種程式的嚴格恪守,通過合理的推理規則或者規律實現前提到結論的邏輯有效性。法律推理同樣也體現了司法實質理性。在司法實踐中,如果一個案件的事實清楚,爭議不大,同時法律規則對某種利益要求或權利主張的保護是明晰的、確定的,法官可以在確定了利益沖突的事實后,進行權利義務分析,運用三段論式的演繹邏輯推理方法,作出最終的法律決定,這類案件就是所謂的簡單案件。在簡單案件中不存在所謂利益衡量問題,因而法官進行法律推理時不需要進行價值判斷和自由裁量。然而我們知道法律終歸是人制定的,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社會生活是紛繁復雜的,是不可能全部預見的,法制再嚴密,總會是有漏洞的,而且由于法律相對于社會發展的滯后性,這種漏洞是隨處可見的。人類理性的有限性決定了創制完美的制定法注定屬于徒勞。抽象、概括的法律規則不可能與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形成直接的對應關系,規則的普遍性、抽象性、穩定性與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復雜性、變易性的矛盾也不可能依靠立法的方式得到根本的解決。實踐也表明,“無論怎樣精心設計的審判制度,在其中總是廣泛存在著委諸個人自由選擇的自由領域”⑥,這就使得司法過程不可能成為一個機械的純粹邏輯化的適用法律的過程。即使是在嚴格規則主義的約束下,法官的能動作用也不可能徹底排除,而且機械的裁判也并不能很好地實現立法者的意志。沒有法官的自由選擇和裁量,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司法活動。這就要求法官必須在各種社會因素的制約下,對多元的法律意義進行權衡和選擇,并充分考慮他的選擇會有怎樣的后果。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實質推理,它體現了一種司法實質理性,相對于形式理性為基礎的形式法治而言,實質理性代表了一種實質法治觀。
司法實質理性通常出現在法官自由裁量的場合,憑借法官個人對公正、善良的價值觀為指導的司法裁判實現個案中的正義。實質理性實際上代表了個案實質正義實現的理性路徑,法律推理的過程實際上包含著法官對法律規范的選擇和解釋、對案件事實的理解、對具體情境的斟酌、對各種相關因素的綜合考慮,以及在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張力下對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的探求。具體而言,法官所適用的作為推理大前提的法律規范不是法律文本中自在自為的法律條文,而是法官“發現”的結果,是法官針對特定案件事實對相關法條進行理解和解釋的法律規范,這種理解和解釋包含著法官針對該事實的具體的價值判斷,即法律應該是什么的判斷。同樣,法律事實是建立在證據的基礎之上的,法官對案件事實的判斷實際上是對證據的判斷,即對事實應該是什么的判斷。法官不是要恢復已經逝去的客觀事實,而是對由證據建構起來的事實形成一種內心的確信。這就是說,作為法律推理的大小前提往往都有賴于法官的主觀認定。從推理的實際過程來看,法官的推理作為法律與事實的結合,并非是一個由前提到結論的線性推理,而是一種基于經驗的由前提到結論和由結論到前提的雙向結合的實質推理。⑦法律推理更是一種實踐推理活動。法律推理不僅僅是一種思維領域的現象,是法律實踐主體的邏輯思維活動,它還是一種可以實際運用和操作的方法和過程,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在法律適用中,推理的運用就是要建立起待決案件事實與法律規范的某種關聯,并依據這種關聯的“正當性”得出待決案件的具有說服力的結論。在適用法律的作業中,法官對待決案件事實的確認,對所要適用的法律規范的選定,以及對待決案件事實與法律規范關聯性的論證,不是單憑邏輯思維就能解決的。霍姆斯因此說,法律的生命不在邏輯,而在于經驗。作為一種實踐理性,它是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之上,依靠司法者在司法實踐中的不斷學習和探索逐步掌握和積累起來的。因此法律推理所蘊涵的司法實踐理性,是與智慧、審慎、深思熟慮聯系在一起的以司法程序技術為依托的實踐推理能力。另外,法律推理本質上是一種行為選擇,而行為選擇的靈魂則是價值與目標判斷。⑧無論是法律漏洞的填補、規則歧義的消除、抽象規則的具體化還是推理的后果評價,都需要推理主體借助于價值論和目的論評價在多種可替代的規則解釋方案中作出選擇。在同一案件中,由于推理主體的價值與目的偏好的不同,同一規則的適用也完全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因此,法律推理不同于純粹形式的邏輯推理,也不同于與價值無涉的科學推理,法律推理實質上是一定原則提導下的價值判斷與行為選擇。價值判斷與利益權衡使得法律推理不再是一種機械性操作,法律推理主體不是機械地受到法律規范的決定與支配;以價值判斷與利益權衡為核心的行為選擇也不會成為法官的個人專斷,法院也不被認為是純粹的強力機構。法律推理作為一種有目的的實踐活動,正是由于實踐理性的作用,才有可能成為防止司法專橫的手段。
法律推理的這種實踐理性雖然不排除個人價值判斷、個人的利益主張與要求,但它要求法律推理主體應該使個人的主張和意見具有可普遍化的性質,因為只有可普遍化的理由才能為各方所接受,使個人的利益主張具有正當性。作為一種實踐理性活動,法律推理“既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又是一個非常個性化的過程。說它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是指任何行為的選擇都是存在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任何行為最終都必須與他人發生關聯,都必須接受一定的社會評價;說它是一個個性化的過程,是因為行為的選擇最終是由行為者自己做出的,根本上取決于對自身行為目的的認識和把握”。⑨法律推理作為法律職業者實際地處理自身與世界之間關系的活動,它是以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的觀念為范導的,是人類有目的地、能動地處理人與世界之問關系的活動。
三、運用法律推理,促進理性司法
篇(9)
案件鏈接:
涉訴地塊位于上海外灘,介于豫園和十六鋪世博水門之間,占地約4.5萬平方米。上海證大2010年以92.2億元投得該地塊,刷新了當時的“地王”記錄。
2011年11月,上海證大以95.7億元向海之門出售外灘地王項目。截至2011年11月2日,上海海之門房地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由浙江復星、證大房地產、綠城及磐石投資分別直接或間接占有50%、35%、10%及5%。
到了12月29日,SOHO中國公告,通過從證大、綠城和磐石收購股權,從而持有了上海外灘8-1地塊50%的股權。這也意味著,SOHO中國將與復星共同持有外灘地王項目。
在SOHO中國收購之前,復星一直掌握外灘8-1地塊的控股權。但SOHO中國40億元的收購,使得該項目變成了各占半壁江山的局面。
直至2012年5月31日,復星國際宣布正式就上海外灘8-1地塊的權益向有關各方提出民事訴訟,以保障公司在項目上的優先認購權。
2012年11月29日,外灘8-1項目股權紛爭案在上海一中院一審開庭。
一、法律事實的認定
司法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此處的事實不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事實,而是指法律事實,即能夠引起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的事實,是經過法官的篩選后確定的作為判案依據的事實。面對具體的糾紛, 法官的首要任務是進行法律事實的認定,以之作為判案的依據,即尋找所謂的小前提。法律事實是法官依法認定的事實,在這一認定過程中也包括了當事人以及證人等的參與。但是,諸多的事實資料最后卻只能交由法官依法進行“剪裁”(普通法系交由陪審團裁定),由法官享有法律事實認定的獨斷型權力,從而為法律推理的小前提作出法律評價與確認。可見法官在法律事實的認定上具有獨斷性和權威性,雖然這并不表明法官的認定總是準確無誤的。
本案中,對法律事實的認定一直存在爭議。在11月29日的開庭中,有關復星是否有股東優先購買權以及復星的股東資格是否適當成為當日庭審焦點。
復星訴稱,復星與證大五道口的母公司證大早在2010年4月簽署了一份《合作投資協議》,根據這個“母協議”,“未經對方事先書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全部或部分轉讓該協議規定的權利和義務”。復星的律師在法庭上宣稱,SOHO受讓股權的行為沒有得到復星的同意,因此此項交易違反了“頂層協議”的約定。
SOHO中國、證大、綠城對此反駁稱,此次證大、綠城只是把其持有海之門公司股份的控股公司轉讓與SOHO中國,而不是直接出售海之門股權,因此復星不擁有優先認購權。
復星方面則反駁,在該交易中,SOHO為此交易特別設計了這樣的一個交易結構――通過收購目標公司(海之門公司)的上級公司股權,并剝離這些上級公司的資產,使其成為僅擁有目標權益公司的殼公司,其用意是繞開復星在目標公司內的優先認購權。
在合資公司中,復星、證大、綠城、磐石的股份都由下屬公司持有。但是SOHO在收購復興外的50%股權時,并沒有直接收購這些下屬公司持有的股權,而是收購這些下屬公司的再上一級公司股權。表面上看,這種收購似乎是在上一級公司之間進行的,但目的就是為了收購下屬公司的部分權益。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法官對于這一設計如何認定。由于本案的案件事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能像一些典型的事實一樣直接歸類于某一事實范型中。而是可能歸類于某幾個事實范型中,這就需要法官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專業知識以及公平正義觀念作出權威性的認定。《公司法》確實明文規定,在“同等條件下”,其他股東有優先認購權。在庭審中,作為被告一方的證大方面單獨辯稱,在去年的11月份期間,證大就與SOHO中國達成意向交易曾兩次發函給復星,但復星都沒有給予回應,并且證大之所以向復星發函,只是一種交易告示,并不是向復星承認其擁有股東優先權。顯然,《公司法》對優先購買權的行使只進行了原則性規定,實際操作只能由法院具體裁決。
二、法律發現
法官在裁判案件之前必須在錯綜復雜的法律規定中選擇要適用的法律,這就是法律發現。法律事實的認定和法律發現是三段論推理最主要的最基礎的工作,小前提和大前提確定以后才能按照推理規則得出相應的容易為人們接受的結論。法官發現法律首先應從制定法中尋找,這是限制法官自由裁量的第一步。可見法律發現的主要場所是制定法,這有利于保持法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是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但首先在制定法中進行法律發現并不否認在特殊情況下適用其他的法律淵源,,如在出現法律空白時可以適用公平正義觀念、公序良俗、公共政策等。
本案原被告雙方在法律發現上存在重大分歧,原告復星認為應該適用《公司法》第72條的規定,而被告卻不以為然。我國《公司法》第72條規定經股東同意轉讓的股權,在同等條件下,其他股東有優先購買權。兩個以上股東主張行使優先購買權的,協商確定各自的購買比例;協商不成的,按照轉讓時各自的出資比例行使優先購買權。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所謂股東優先購買權,是指股東在同等條件下可以優先的購買其他股東的權利。這種優先購買權是有限責任公司定的一種權利,公司法為了保證有限責任的股東的權利和利益,規定股東可以通過行使優先購買權來實現對公司的控制。這種規定不僅是一種對老股東對公司的貢獻的承認,也是為了在股東之間能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系維護公司當中的人合性。如果認為本案適用《公司法》72條的規定,質言之,如果認為復星沒有行使優先認購權,意味著承認了復星的優先認購權。而如果復星優先認購權的訴求獲得法庭支持,SOHO中國所在的被告一方將陷于被動。
三、法律解釋
法律發現的結果可能是明確的規范也可能是模糊的規范。法律的模糊乃法律三大病灶之一,如果發現的法律是模糊的那就有必要進行法律解釋。法律解釋是法官在處理具體案件中經常用到的一種方法,其目的在于使大前提具有明確性,為處理具體案件提供法律依據。法律解釋的目標不在于找到立法者的原意,而在于為案件找到合法、合理又適合于個案的判決理由。通過法律解釋來明確三段論推理的大前提,這一過程應由法官這一主體作為權威性的解釋主體, 同時法官也必須根據法律進行解釋,而不是任意進行解釋。因此,法律解釋具有獨斷性特征,這有利于建立統一的秩序,增強民眾對法律的信賴,也符合法治社會的要求。法官在進行法律解釋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和原則,即法律解釋的方法。法律解釋的方法主要有文義解釋、歷史解釋、體系解釋、目的解釋等。法治原則要求法律解釋首先要接受法律字面規定的約束,而不能脫離法律的明文規定進行隨意解釋。文義解釋具有客觀性,符合法治的原則和要求,因此在進行法律解釋時首先要考慮進行文義解釋。只有在具有排除文義解釋的理由時,才可能放棄文義解釋。文義解釋的嚴格遵守法律進行解釋這一特征也決定了其具有機械性和僵化性, 在一些情況下需要通過目的解釋、體系解釋等來克服這一缺陷,實現法律解釋的目的。
本案中一個引起廣泛爭議而需要解釋的問題是:復星是否有股東優先購買權。《公司法》第72條規定了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優先購買權。公司法規定的優先購買權對公司原有股東具有普遍性,主要體現在:原有股東對于對外轉讓的股權具有優先購買權;同時主張優先購買權的股東協商不成時按各自出資比例行使權利。公司法沒有規定內部股東之間轉讓的優先購買權問題,但規定“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該條規定給股東優先購買權留下了豐富的設計空間。
股東優先購買權,對于投資者來說具有以下意義:
1、限制外部股東加入。有限責任公司具有“人合性” 的特點,為維護公司股權結構和經營運轉的穩定,投資者對股東對外轉讓股權設定前置程序――經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設定限制條件――其他股東放棄行使優先購買權。只有這兩個條件得到滿足,股東對外轉讓股權才能實現。
2、確保和增強投資者股東地位。除公司法設定的對外轉讓股權的優先購買權外,投資者還可以要求內部股東股權轉讓的優先購買權、對內對外股權轉讓的最優級優先購買權,從而確保和增強自身的股東地位,甚至取得控股法律地位。
根據本案,對于復星來說,實現優先購買權利益最大化方式是,協議取得優于現有股東和未來股東的最優級優先購買權。即未來海之門公司任一股東轉讓股權,無論對內還是對外轉讓,復星都作為第一順序受讓人,復星有權選擇行使協議約定的最優級優先購買權,購買轉讓股權的全部或部分,在復星放棄優先購買權的情況下,其他股東才能行使次級優先購買權。如果復星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則無法協議約定復星的優先購買權。原因在于《公司法》第138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轉讓”,該強制性條款排除了章程的自由約定,投資者沒有股份對外轉讓的優先購買權。因此,就本案而言,對《公司法》的第72條應該作出何種解釋,取決于復星與證大在設立合資公司之初,在“母協議”中究竟是怎么約定的。
四、法律論證與法律推理
法律論證和法律推理是有區別的。法律論證是論證大前提的合理性,目的是解決大前提的缺陷,而法律推理則是根據推理規則推導出結論。司法必須要以法律為準繩,一方面法官也不能隨意選擇法律進行斷案,另一方面在選定了法律規范之后還必須依照一定的推理規則進行。法官在選定了法律之后,要對選擇適用的法律作出合理的論證,為什么用這條法律,而不是其他的,即論證大前提的合理性,屬于外部證成。在認定了法律事實這一小前提,尋找到了法律依據這一大前提,并通過法律解釋和法律論證使大前提具有了明確性和合理性之后,再依據推理規則進行法律推理得出最終結論,屬于內部證成。
法院若依據《公司法》第72條的規定認定復星具有股東優先認購權時,首先必須論證為什么要適用《公司法》第72條的規定。法院若認為證大、綠城轉讓其持有海之門公司股份的控股公司的行為與直接出售海之門股權的行為沒有本質的區別,并進一步從主客觀方面論證SOHO中國受讓股權的行為沒有得到復星的同意,違反了復星與證大、綠城的“母協議”約定,從而為適用《公司法》第72條這一大前提提供了合理性支持。
法院若最終認定SOHO中國的行為侵犯了復星的股東優先認購權,這樣還必須論證證大、綠城轉讓其持有海之門公司股份的控股公司的行為就是直接出售海之門股權的行為。因為不能直接按照推理規則推導出這一結論。這一命題,需要加入一個新的三段論來論證,這個新的三段論即屬于外部證成。這一新的三段論的大前提是新《公司法》第72條第4款規定:“公司章程對于股權轉讓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這表明新《公司法》第72條之規定屬于任意性條款,只有公司章程沒有規定股權轉讓規則的時候才適用。這就為按照推理規則進行法律推理提供了合理的大前提。
篇(10)
法律推定作為分配證明責任以及在無直接證據證明的情況下認定法律事實的手段,在證據法中是一個十分基本的和重要的問題。但我國司法實踐中長期以來強調的是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以及法定證據制度,甚至對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作了不正確的理解,加上演繹邏輯的法律邏輯觀的影響,而長時期地忽視了對法律推定規則的研究和適用,造成了在法律實踐中的許多困惑和處理案件時的模棱兩不可的局面,以至于造成了司法實踐中的許多困難和不公正現象。比如,有許多案件事實雖然明顯為真,但由于得不到演繹證明,但又不得拒絕審判,而不得不作出不予認定的結論,造成了許多實際上的不公正的裁判。在無罪推定問題上的模糊態度,不利于該原則的實施,不利于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保護。由于在非法所得罪問題上運用推定上的不堅決,導致對該罪的打擊不力,無法實現刑法對于該罪的立法宗旨。由于占有不利證據一方拒不提供證據,如果不運用推定,不利于證據的調查、獲取,及時處理案件。如此等等。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逐漸發展起來的非單調邏輯,如缺省推理、模態非單調推理、約束推理、基于理性人假設的推理、基于封閉世界假設的推理和自認知推理,以不完全信息情況下的推理為研究對象,為我們準確分析法律推定和整個法律論證的邏輯特征提供了恰當的工具。本文著重分析法律推定在邏輯認知基礎上的非單調性與其在法律價值上的合理性。推定邏輯性質的準確認識對于更好地發揮推定在訴訟過程中的作用,對整個證據立法和司法技術的進步,實現司法的整體公正性,都將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一、什么是非單調推理
關于推理的單調性和非單調性概念,人工智能科學中是這樣理解的:加進系統的新知識(信念)必須與已有的知識(信念)相一致,不引起矛盾。所以,隨著運行時間的推移,系統內含的知識有增無減,這就是所謂的單調性;反之,如果加進新知識會取消原有的知識,就是非單調性。
非單調邏輯的產生源于單調邏輯的處理能力的有限性。
二、可反駁推定的非單調性與合理性
筆者考察了關于推定(presumption)的諸多定義,認為如下定義是一個較好的定義:“從廣義的角度出發,推定的定義可界定為:在訴訟過程中,在沒有足夠的相反證據時,法律或審判者無須主張者舉證證明而直接認定一具有或然性的事實或結論為真的一種事實認定過程。”推定即假定,是指由法律規定或法律事實審理者決定的對或然性的事實加以認定的訴訟活動和法律規則。推定可分為可反駁的推定與不可反駁的推定。
推定的可反駁性是指,推定被審理者初步采用后,該推定事實對其不利的一方當事人若能證明該推定事實不存在或推定不成立,則推定不能再被采用。主張該推定事實的一方當事人就要另行證明。
案例分析。湖南省衡陽市糧運總公司兩位職工集資建房糾紛案。無房戶某甲得到一個集資名額卻苦于財力不夠無法在限期內支付集資款,有房戶某乙即托人做中找到某甲,愿以自己原先所在單位分得的兩居室舊房(當時正由某乙的兒子居住,某乙住在丈夫所在單位家屬宿舍)的居住權為代價換取集資名額。二人約定:待某乙的兒子搬進集資新房,某甲即搬進某乙兒子現住的舊房。某甲即回絕了多人以數千元購買其集資權的要求,與某乙達成了口頭協議。之后,某乙便以某甲的名義集了資,但在交房前,某乙卻發生婚變,被丈夫逐出家門,自己也成了無房戶。某乙于是否定她與某甲之間的協議,一口咬定集資權系某甲無償相送。法院在審理本案時,面臨兩難境地:采信某乙的主張,明顯于理不合;而采信某甲的主張,又缺乏法定證據的支持。兩級法院的法官對此都心知肚明,但現行證據制度下卻無能為力,只好判某甲敗訴。弄得某甲一家到處喊冤,一直不服。
上述案例中,如果根據缺省推理,即進行推定,則可從無房戶某甲拒絕多人以數千元的價款交換其集資權這一事實,推出甲不會將集資權無償相送。這是一個隱含推理,或者說省略推理。省略的前提是一個概稱句:“在正常情況下,處于某甲這樣地位的人是不會將集資權無償相送的。”依據的是一種類型化特征。按照人工智能理論中的分類層次體系理論,事物可以按其共性分類,使得屬于某類的事物擁有該類共有的典型特性,成為人之常識,除非已知該事物在某特性上異常。例如,人們都會假設隨意的一只鳥會飛,除非已知它不會飛。同樣,我們可以假設,隨意一個人,在自己無房且有人以數千元價款交換集資權的情況下,不會將集資權無償相送。我們可以構造一個缺省推理:若不是某乙以高于數千元的條件交換其集資權,一般情況下某甲不會給予其集資權;既然某甲給予其集資權,那么是某乙以高于數千元的條件交換其集資權。這個條件即是某乙舊房的居住權。由于我國民事訴訟法中尚未明確規定自由心證制度,法官忌用缺省推理。這說明我國民事立法的缺陷,立法對于某甲來說是不公正的。若法官用缺省推理作出有利于某甲的心證,案件就會得到公正的處理,但應允許某乙提出證據反駁。筆者認為上述這類案件如果按照缺省推理的結果來處理,結論的可靠性程度將會大大提高。
三、不可反駁推定的邏輯推理形式的單調性與價值選擇
不可反駁的推定,是指法律不允許提出證據來反駁被推定事實的推定。只要前提事實成立,就必須確認推定事實。如對犯罪能力的年齡的規定。作為不可反駁推定的一種極端情形是,只要基礎事實是真的,即使能證明與推定事實相矛盾的事實,仍然不能這種推定的結果。如我國訴訟法關于法律文書送達的推定。法院以張貼公告、在報紙上刊登公告等方式,通知受送達人在規定的期間到指定的地點領取訴訟文書,自發出公告之日起,經過60日,即視為送達。即使被送達人舉證證明了其未收到公告,也不能改變推定的效力。
筆者認為,下列幾種常見的推定也是不可反駁的推定。
1 非法所得的推定。我國《刑法》第395條非法所得罪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說明來源。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在非法所得罪的推定中,如果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且本人又不能說明其來源,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前提成立,結論不可反駁。
2 舉證妨礙之推定。所謂舉證妨礙,亦稱證明妨礙,是指因一方當事人的行為而致其持有的對證明案件待證事實具有相當證明意義的證據材料拒
不提供、銷毀、毀損至喪失其證明價值的程度而產生相應法律后果的一種事實狀態。而所謂舉證妨礙之推定,是指立法者在立法上明確規定在特定情形下對此行為擬制產生對行為人不利的訴訟法律后果或者授權法官據情判定是否對其行為人產生不利的訴訟后果。
在舉證妨礙推定中,如果占有不利證據,司法機關要求提供而拒不提供的,推定證據的內容對其不利,只要前提成立,結論不可反駁。
3 無罪推定。無罪推定是指如果法律事實的審理者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則推定其無罪。前件成立,后件不可反駁。
下面分析基于無罪推定之推理的邏輯推理形式的單調性。
無罪推定原則在我國刑事訴訟立法中雖有所體現,但并未完整地確立。這其中有政治、法律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原因,但其認識論方面的原因也不容忽視。從我國立法機關對無罪推定原則的態度及學術界對其認識論的分析來看,不完全接受這一原則的主要認識論原因是認為它違反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有學者從邏輯上認為基于無罪推定之推理的邏輯形式是“以無知為據”,更強化了這種認識。
筆者認為,上述這種對無罪推定原則在邏輯上的理解是不準確的。
無罪推定,是以不能證明犯罪為前提,這一點正好說明它是以事實為根據,是實事求是的,而且是建立在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相對性的認識基礎之上的。無罪推定也是一種法律擬制,它不單純是一種認知關系。它是對在法官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情況下的一種包含價值選擇的法律技術處置,而并非像有的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以無知為據”的一種純粹推論關系。如前所述,無罪推定以無罪假定為前提,是在無罪假定基礎上的一種推定,只有法官的有罪確信或認定,才能對無罪假定給予否定。
基于無罪推定的推理之所以是單調的,是因為,只要前提“法律事實的審理者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不改變,則結論“犯罪嫌疑人無罪”的結論不能廢止。
四、不可反駁推定的邏輯認知基礎的非單調性
1 從封閉世界假設和自認知推理看基于無罪推定之推理在認知基礎上的非單調性 下面再從自認知推理來看基于無罪推定之推理的認知基礎的非單調性的問題。自認知推理遵循下列模式:
1)如果陳述x真,那么我將知道。
2)我不知道x是否為真。
3)因此,x不是真的。
在無罪推定問題上,我們假定主體的知識基礎包括:
4)如果某人有犯罪事實,那么法官將會知道。
5)某甲有犯罪事實。
并且在知識基礎里沒有信息允許得出結論某乙有犯罪事實。則可得出:
某乙沒有犯罪事實。
因為法官不知道某乙有犯罪事實。但加上前提
6)某乙有犯罪事實。
很顯然使先前“某乙沒有犯罪事實”的結論成為不可能。
這里的非單調性表現在,關于某犯罪嫌疑人無罪的結論的得出依據了封閉世界假設,封閉世界假設是將不完全的知識庫封閉化,當作完全的來處理。事實上,在封閉的集合里找不到某被告有罪,不等于被告無罪,而是存在有罪和無罪兩種情況。一旦我們證明了被告有罪的事實后,被告無罪的假定性結論將被取消。
2 從約束推理看精神正常推定的認知基礎的非單調性。在刑法中,行為主體即使達到了刑事責任能力的年齡,但如果存在精神障礙,就可能影響其責任能力,從而影響其刑事責任。比如我國刑法典第18條就規定了精神病人的刑事責任問題。第18條第一款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第二款規定:“間歇性的精神病人精神正常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第三款規定:“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篇(11)
法律推理為什么要涉及諸多實質性問題?對此學者們有過許多研究和論述。美國法理學家博登海默列舉了三種情況:(1)法律沒有提供解決爭端的基本準則;(2)法律規范本身相互抵觸或沖突;(3)將一既定法律規范用于某一具體案件時明顯有失公正[1]。深入研究會發現,需要人們在進行法律推理時考慮實質性問題的原因是繁復多樣的。就有關法律的推理而言,在面臨法律漏洞、法律規范含義不清、法律條文相互沖突等情況時,為了確定恰當的推理前提,就需要作關乎內容的實質性分析和推斷。例如,出現“法律漏洞”,即現有法律條文沒有就某一問題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即意味著這一領域出現了法律適用的空白。按照我國刑法規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也不受罰。面對司法實踐中的某些情況,便可能就相關法律條文的內容做出不同的解釋。又如,法律雖經嚴格的立法程序,但因各種原因某些條文的含義仍可能不甚清晰明了,導致人們可以作多種不同的理解或解釋,從而引發紛爭。當要以這樣的法律條文作為推理根據時,就需要對其中的法律概念或規定進行界定、梳理和分析,以證明引用某一條文作為處理本案件之判決依據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再如,有關法律規范相互抵觸或沖突的情況,具體有三種可能:其一,一部法律內的不同規定不一致或相互抵觸;其二,不同法律對同一問題的規定不一致或相互抵觸;其三,將不同法律適用于某一案件可以推出相互沖突的結論。法律規范之間的相互沖突,有些隨著立法制度的健全和立法水平的提高有可能得到解決;有些則不然,由于不同法律的著眼點或立法意圖不盡相同,所以各自的具體規定或由它們推得的結論就可能相互抵觸。倘若針對同一案件的不同判決都能找到法律依據,這時進行法律推理就不能不考慮諸如社會的價值理念和道義原則等實質性問題,據此在不同的法律或法律條文間作出選擇。就根據法律的推理而言,最突出的問題是嚴格按照法律作出的判決結論有時會陷入“合法”與“合理”相悖的窘境之中。也就是說,某一判決結果,從法律角度看是“合法”的,但是從道義、倫理角度看,則不一定“合理”;或者相反,從法律角度看不“合法”,但從道義、倫理角度看,卻有合理性。法律原本是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而制定的,當適用現行法律規定得到的結果與立法者自己認同的公平正義觀相抵觸,或與社會主流價值觀相沖突的時候,人們必定要尋求某種補救辦法,其中之一就是所謂的“衡平”。“衡平”是指在適用法律過程時對某些案件作出有別于一般法律規定的特殊處理,以在“法”與“理”之間求得某種平衡。法國比較法學家勒內•達維德把衡平法稱作是避免在法律和正義之間產生“不能容許的脫節”的一種“矯正劑”和“解脫術”,認為這是任何一個立法制度都不能沒有的[2]。而“衡平”運用之處,必定有對諸如立法意圖、判決效果、社會倫理價值觀等實質性問題的考量和權衡。
影響法律推理的主體因素
由上文所述可見,進行法律推理必然會涉及到對與推理過程相關的諸多實質性問題的考慮,而在考慮這些問題時,人的個體因素就會滲入其間,并影響他的判斷,影響最終的推理結果。在司法實踐中常常出現這樣的情況:面對同樣的案情,當事各方會做出截然相反的判斷,這通常不是因為各方據以推論的邏輯規則不同,或者其中一方粗暴踐踏了邏輯規則,而是因為推理的主體———人受到各種不同因素的制約和影響,使他們對問題形成全然不同的認識或判斷。從推理主體方面分析,影響法律推理的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心智狀況。這里所謂“心智狀況”,既包括非理性層面的心理、情感等因素,也包括理性層面的認知能力、分析方法等。法社會學和分析法學是20世紀初盛行于歐美的兩大學派,他們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人的心理因素和邏輯分析方法對適用法律及法律推理的影響。法社會學主張聯系現實社會生活來理解法律的本質和功能,所以他們注重對法律的社會效果的研究。法社會學派指出,法律規范只提供了維護社會正義、解決個人糾紛的一般指南,它不可能囊括全部司法領域,其實這也就是上文提及的出現“法律漏洞”或法律條文含義不清等情況的深層原因之一。因此法社會學派認為,必須給法官判案以一定范圍的自由裁量權,而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為了做出公正的判決,必須考慮社會流行的道德觀念,研究當時當地的社會經濟條件等,在這一過程中法官的個人直覺和感情因素會起一定的作用。法社會學派所說的這種心理因素對法官判案的影響并不難理解:比如,倘若法官的從眾心理較強,那么社會流行的道德觀念等就會在較大程度上支配他的判斷;反之,法官則可能更傾向于依據法律規范進行獨立的分析思考。分析法學突出了問題的另一方面,他們排斥對法律作心理的、社會的、價值的“形而上”研究,提出,研究法律的任務在于解釋法律體系中的一般概念和原則,從而獲得對法律的更為精細的理解。
因此分析法學強調研究法律內部的形式、結構和語言的重要性。這一學派的一些學者曾運用維特根斯坦提出的語言分析方法,通過解剖法律概念、把它們還原為其基本成分來澄清法律概念的含義。分析法學派提出的對法律概念、形式、結構等的精細理解,對人們理性思維能力具有極強的挑戰性,需要運用各種邏輯或語言分析的理論與方法。分析法學派的問題在于其理論趨向極端,無視人的心理狀態等非理性因素對于理解法律所發生的作用,甚至根本反對做這一領域的研究。第二,價值理念。現實的法律過程,從立法、司法到執法,沒有一個環節能逃脫人的價值理念的“糾纏”。任何法律的制定都有其追求的特定價值目標,都有相應價值理念的支撐,價值理念是統攝法律的“靈魂”。因而對法律條文的解讀,除了要有一定的邏輯或語言分析理論與方法之外,還必須把握其背后蘊含的價值理念,否則,邏輯或語言分析的理論與方法就會成為無本之木。德國法哲學家拉德布魯赫指出:“法律是人類的作品,并且像人類的其他作品一樣,只有從他的理念出發才能理解。”[3]從一定意義上講,法律推理的主體能否領悟某一法律的價值目標,他的價值觀是否與該法律所蘊含的價值理念相契合,是他能否準確理解法律條文、從而確定其推理前提的重要條件。理想的法律制度,是在一項法律確定以后,其適用過程能排除或盡量減少主體因素的影響,從而體現法律的普適性、一致性和公正性。但是,由于種種難以消弭的主客觀原因,在任何一種法律制度下,都會存在法律空隙、法律條文含義不清乃至相互沖突等情況,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因而總是需要適用法律的人從自己的判斷出發去彌補漏洞、廓清含義、做出選擇。人的任何思考和行為都自覺不自覺地受其價值觀的支配,所以主體的價值理念在適用法律及法律推理中的影響是排除不了的。比如,面對相互抵觸的法律條文,不同的判決結論均可找到相應的法律依據,都可以合乎邏輯地推出,那么,究竟是選擇有利于被告的判決還是相反,最終的判決結果必定反映了推理主體對孰是孰非、孰重孰輕的價值判斷。第三,利益關系。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任何價值理念的形成都有其社會經濟根源,因此由價值理念可以進一步看出人的各種利益關系在法律推理中的影響。每個人均是一個利益主體,在社會經濟結構中處于相同或相近地位的人構成一利益集團。不同個體、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有契合之處,也必定存在差異、矛盾甚至沖突,由此產生各種復雜的利益關系,如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個人與集團之間的利益關系、集團與集團之間的利益關系、個人和集團與整個社會的利益關系等等。這些利益關系會影響人們的價值判斷,當然也會影響身處適用法律過程中的人對問題的判斷。#p#分頁標題#e#
利益關系對適用法律過程的影響可能帶來對司法公正的嚴重威脅,因此世界各國都嘗試作出相應的制度安排,切斷利益向司法過程侵蝕的通道,尤其是切斷法官與各種利益關系的瓜葛,以保持其獨立性。但任何“獨立”都是相對的,因為人不可能置身于利益集團之外;即使其個體的利益關系獨立了,也不能保證他對問題的整體判斷不受某一相關利益集團的影響。上文已提及,為了緩解“合法”與“合理”之間的沖突需要求助于“衡平”。在司法實踐中有太多的案例表明,所謂“合理”之“理”,不僅是指立法者認同的公平正義觀或社會主流價值觀,而且還包括社會或多數社會成員的整體利益。“衡平”往往是社會或推理主體內心各種利益關系相互博弈的結果。主體因素的加入對于適用法律而言是一把“雙刃劍”,既有積極意義,如消弭法律空隙,澄清法規含義,在“合法”與“合理”的沖突間保持必要的平衡等;也有負面效應,如影響司法公正,導致司法腐敗,削弱法律的統一性、公正性、權威性等。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是對“人治”的否定,但實行“法治”并不意味著可以無視或否定人的作用。就適用法律和法律推理過程而言,便不能沒有人的參與和運作。如實承認并正視這一現實,與實行“法治”并不矛盾,相反能使我們得到某些重要的認識:其一,提高司法人員的整體素質至關重要,推進“法治”、實現司法公正必須進行不懈的努力;其二,建立一套嚴格、透明的司法制度同樣至關重要,這樣才能保證適用法律過程處于有效的制度規范、約束和監督之中,保證司法人員的個體因素在合乎法律基本精神的框架內發揮作用。
對法律邏輯學研究視角的思考
一門學科的研究視角和方法總是與它的研究對象的特點密切相關。邏輯學是研究推理的學問,推理的特點不同,它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就會有所區別;或者說,對推理特點的認識不同,邏輯學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就會發生相應變化。從上文分析可見,法律推理的特點在于,它既要遵從人類共通的邏輯規則,也要考慮推理過程所涉及的諸多關乎實質內容的問題,而在這一過程中,人的主體因素將滲入其間并產生相應影響。法律推理的這一特點,要求法律邏輯學有其不同于傳統邏輯的研究視角和方法[5]。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邏輯學專注于思維形式結構,特別是“必然推出”之推理模式和規則的研究,刻意排斥探討推理中人的主體因素及其作用。正如蔡曙山先生所言:“邏輯學是從來不關心人的,這來源于邏輯學根深蒂固的觀念:邏輯要為思維立法!因此,邏輯學只有抽去人的因素,它才能適用于一切人!在傳統邏輯和近現代邏輯中,人的因素都被排斥于邏輯學之外。亞里士多德三段論、假言推理、一階邏輯都是與人無關的,因此,它們是適用于一切人的。”[5]這一傾向在弗雷格那里發展到了極致。他在《算術基礎》一書序言中提出了研究數學哲學的三條原則,其中第一條就是:“要把心理學和邏輯學的東西區分開來,把主觀和客觀區分開來。”[6]這種邏輯主義傾向在20世紀不斷遭遇挑戰。與弗雷格同時代的直覺主義學派就提出,數學起源于經驗直覺,是人類心靈的創造性構造,因而他們認為,數學和邏輯不僅不排斥心理因素,相反應肯定心理意向在數學和邏輯中的作用。20世紀40年代,維特根斯坦以語言游戲論取代他早期的邏輯圖像論,提出“語言的意義在于它的應用”,強調語言的意義與語言的使用者和使用者的意向有關。后來奧斯丁發展了維特根斯坦的理論,進而研究語言的使用條件即語境與語言意義的關系,建立起言語行為理論。20世紀70年代,在喬姆斯基的心理主義語義學等理論的影響下,形成了認知科學,促使心理學與邏輯學相互交融。人們在對認知的研究中找到很多證據,表明心理因素在人的推理過程中的作用,如著名的沃森紙牌游戲就生動說明了人的邏輯推理是如何受其心理因素影響的[7]。